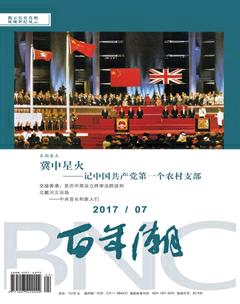交接香港:親歷中英設立終審法院談判
陳佐洱
1994年3月11日,我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是專門處理香港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具體事宜的臨時性外交機構,下設不同的專家小組。自上任到1997年香港回歸前,我擔任過中方14個專家小組組長,主談了包括軍事用地、防務與治安交接、財政預算案編制、政府資產移交、終審法院籌建、公積金制度設立等議題,最終全部與英方達成共識。
我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后,在當年完成軍事用地問題談判以及其他多項談判繼續齊頭并進的情況下,即重點關注和著手準備終審法院問題的談判。
從倫敦樞密院到香港終審法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一章總綱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是中國在“一國兩制”國策下對香港作出的一項重大制度性安排,是在“一國”的前提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體現。
如何為未來香港特區建立史無前例的終審法院及其相關配套制度?如何實現香港司法體制在回歸前后的平穩銜接?這是備受港人和國際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英國管治的150多年里,香港法院的終審權掌握于倫敦的王室咨詢機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這個有上千年歷史的機構專門受理海外領地、王家屬地和英聯邦成員國家終審案件。香港每年有一二十宗案子要上報倫敦樞密院,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法律原則問題是上訴焦點。雖然英國和香港同屬一個法系,但相距兩大洲,歷史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很不相同,加上樞密院的成員大多年事已高,對香港世態民情一知半解,作出的判決往往與香港上訴庭的判決很不相同。盡管如此,終審權始終是在倫敦,而不是在香港。
可是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后,老謀深算的英國卻想在香港易幟前“放下”至關重要的終審權,在香港設立終審法庭,其目的是要把按它設想建立起來的終審機構過渡到未來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方搬起石頭砸了自己腳
1988年2月,英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設立終審法庭的建議大綱,包括架構組成、判決權和訴訟程序等主要內容。中方本著友好合作精神,慎重研究了半年,認為在1997年前提前進行過渡性安排,使未來相關特區終審法院的各項具體安排明朗化,將有助于促進政權的順利平穩過渡,增強港人信心,于是決定接受英方的建議,但是要求通過充分磋商,以使1997年前設立的終審法庭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中方要求。
可是,良好的愿望被包括英國在內的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打碎了。英方代表處奉命,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后單方面中斷與中方的磋商。
直到1990年8月,英方重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為了香港司法體系的平穩銜接,中方代表鄭偉榮不計前嫌,在第一次有關專家小組會議發言中開宗明義聲明:“對于英方提出于1997年前的適當時候設立終審法院的建議,中方原則上不持異議。”
這以后又開了三次專家小組會議,在1991年的第20輪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全體會議上,雙方首席代表以互換發言稿的形式達成了原則協議。雙方同意香港終審法院將由四名常設法官組成,并備有兩份非常設法官名單,其中一份為非常設本地法官,一份為非常設海外法官。將來審案時,審判庭由四名常設法官和一名非常設法官組成,這一名非常設法官可在兩份名單中挑選。雙方同意將繼續保持友好合作,甚至設想在1993年就把終審法院成立起來。
不料,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關于終審法院的原則協議公布不久,港英法律界、立法局和傳媒中的某些人又掀起一股反對浪潮。先是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公開批評指責,后是以“二李”為首的八名議員慫恿立法局通過反對中英協議的動議,個別媒體連篇累牘地為英方在1991年協議中的“讓步”叫屈,對中方堅持按基本法規定設立終審法院的立場橫加攻擊。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嚴正指出,作為港督咨詢機構的港英立法局無權否定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原則協議。
而這時聯合聯絡小組的英代處又卻步了,以“立法局有了動議”為借口,遲遲不再執行中英雙方已經達成的協議。
彭定康想趁“鐵票”在手建終審庭
1994年5月,英方又向中代處交來一份終審法院條例草案建議,發出了希望再續這一議題談判的信號。一旦這份文件獲得中方同意并通過立法程序,港英當局就可以“依法”張羅起終審法庭的事來。
有利于平穩過渡的事中方是樂此不疲的,因為過渡得越平穩,回歸后特區的繁榮穩定就越有保障。所以,如果能夠按照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在“九七”前就設立港英的終審庭,然后過渡到“九七”后成為特區終審法院,中方當然樂見其成,即使英方違約了兩次,仍愿意第三次坐下來磋商。可惜的是,英方提交的終審法院條例草案完全是用英國思維寫成的,如果按此通過港英立法程序并設立了終審庭,那必然與平穩過渡沖突,特區終審法院的設立必然得另起爐灶。
1994年10月,中國外交部的一位官員對外表示:“照目前情況看,香港的終審法院不可能在香港回歸前成立。”此話一出,英方著急了。11月1日,在一個雙方非正式的會晤場合,英方要求澄清,我根據中國外交部關于香港終審法院問題的對外表態口徑說:中方當然希望1991年中英雙方就終審法院達成的原則協議能夠得到執行,在香港回歸前就成立終審法院。這是個大的原則,但怎么成立,那就要具體談了。
英方抓住我這句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很快就送交一份說帖,稱對陳代表的表態感到“鼓舞”,英方專家隨時準備與中方就終審法院問題恢復談判。
中代處對形勢進行了分析,認為英方仍然企圖在香港回歸前就成立一個完全體現英國意志的終審法院,造成既成事實讓中方接受。而港督彭定康特別希望在其可以完全控制的本屆立法局任期內完成條例草案的立法,因為1995年7月底任期將滿的本屆立法局61名議員中,有包括港督本人在內的4名當然議員、18名委任議員,而下一屆立法局的全部議員都將由間接或直接選舉產生。這個口口聲聲自我標榜為“民主斗士”的彭定康竟擔心民主選舉出來的下屆議員不靠譜,一旦失去本屆這種“鐵票”優勢,條例草案可能會通不過。我們將有關情況和研究上報了北京。
北京兩部(國港辦、外交部)肯定了我們的分析,并且下達指示,要中代處盡可能地與英方斡旋,爭取在1996年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成立之后再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將來要“以我為主”來設立香港的終審司法機構。
于是,北京國港辦政務司和中代處的法律專家們把英方提交的條例草案稿再一次從頭到尾琢磨個透,陸陸續續分三批向英方提交了問題單子,要求給予解答,通過提問題單子,引導對方修改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讓條例草案向基本法靠攏。
1995年3月,我們得悉港督彭定康在年初回倫敦述職時已獲得梅杰首相同意,即使未能與中方達成共識,港英也將采取單方面行動,于7月底本屆立法局任期結束以前,強行通過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可能他已得知來年中國全國人大將成立香港特區籌委會的信息,感到了特區籌委會和7月后失去“鐵票”的雙重威脅。
難怪英代處在“耐心”回復一批批問題單子的同時,不停地催促我們召開專家會議。彭定康則氣勢洶洶,在社會公開場合擺出一副強硬架勢,多次高調指責中方正在為終審法院談判“制造障礙”。明明拆掉香港平穩過渡“直通車”軌道的是他,他卻倒打一耙。
為了贏得民心和輿論的支持,經中央同意,我們主動向英方提出了召開專家小組會議的建議。1995年3月24日,中英雙方終于就終審法院問題重開談判,舉行第五次專家小組會議。
會上,我首先強調,終審法院問題之所以拖延至今未解決,確實是受到人為干擾,但責任不在中方。我指出,假如英方要在1997年前就成立終審庭并期待過渡到1997年之后,那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近來英方官員多次公開表示港英立法局無論如何要在某年某月通過該條例草案,言下之意必須按照這個時間表來進行磋商和籌備工作,中方不能接受。為了使香港司法體制與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以實現平穩過渡,也為了給雙方的磋商創造一個良好氛圍,中方再次要求英方承諾,在雙方未就終審法院條例草案的磋商達成共識前,不得采取單方面行動。
接著,我提出七個方面的磋商路向,建議以后專家組會議照此開展工作。
莫把1995錯當1842
會后接受記者采訪時,我公開批評了彭定康在中英時隔三年半重開談判的消息剛一發出時,就散布對談判前途表示悲觀,蓄意把責任往中方身上推的言論。 “奉勸彭定康先生莫把1995錯當成1842,1842年英國可以強迫中國簽下割讓香港的不平等條約,但今天如果還要迫使中方按照你們的時間表來設立所謂的終審庭,這辦不到!”
我的“開炮”,讓站在身旁的英方代表包雅倫表情相當復雜和無奈。
4月27日至28日,第六次專家小組會議在香港舉行。我在發言中回顧了香港終審法院問題的歷史由來和中英雙方談判過程,強調香港未來的終審權不是固有的,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設立終審法院本來是特區成立以后的事,中國政府從實現香港平穩過渡的良好愿望出發,同意1997年前適當時候可以設立,并與英方在1991年就達成了重要原則協議,但港英立法局卻通過所謂“動議”,導致協議執行不下去。1994年,英方雖然向中方提交條例草案建議,但同時又設置時間表,制造了新的障礙,中方無法接受。我再次告誡,為了未來享有終審權的香港特區有自己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司法體制,英方單方面設立的終審庭不可能過渡到1997年7月1日。
經過有理有利有節的堅決斗爭,英方的態度在會內溫和了許多,在會外也減弱了雜音,英代處不僅向我們提交了根據上次專家小組會議中方意見修改過的新條例草案,連包雅倫的發言實際上也都照著我們提出的七個磋商路向來陳述英方觀點。
27日夜晚,中方專家組對英方的新修改稿進行了通宵達旦的研究。英國已經在法官資格、法官產生程序等問題上基本吸收了中方建議,但雙方還存在兩方面的重要分歧:一是香港終審法院的管轄權。雙方均贊同香港終審法院管轄范圍應符合香港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地位,不應包括對國家行為的審理。但對于什么是“國家行為”的具體表述各執一詞,中方主張要與基本法規定的提法相一致,即采用“國防、外交等”的表述,而英方則認為僅應局限于國防、外交兩項。此外,中方堅持終審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并建議設立判后補救機制,使某些錯判或誤判的案件能得到再審的機會。英方對上述兩點均持反對意見。
總的來說,中方堅持香港所以獲得終審權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依據基本法授予的,終審權的內容、履行程序等都應與此相適應;而英方則極力淡化“授權”本質,欲最大限度地擴大地區性終審法院的權力,盡可能減少來自中央的影響。
在次日的專家小組會議上,我首先肯定英方的進步,繼續說理闡明雙方兩三個重要分歧所在。
英方的態度不錯,包雅倫在發言中多次正面評價中方作出的努力,如“中方一再重申執行1991年協議,港人、世人以此知道中國對香港司法制度平穩過渡的承擔”,“中方態度十分務實”等。針對我挑明的分歧,他也有了讓步跡象,例如關于“國家行為”的表述,他表示“已經注意到中方的觀點,會仔細考慮自己所持的立場”等。
第五、第六次專家小組會議召開后,談判形勢和輿論都逐漸向有利于中方的方向轉變。英國政府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據報載,英國外交部傾向于在取得中方同意以前先推遲終審庭的籌備工作,對中方提出的成立特區籌委會后再決定終審法院問題也并不反對。還有英國商界人士認為,如果港英當局不經中方同意一意孤行,將迫使以后特區政府采取“更加極端”的手段處理這一問題。還有輿論引述英國前殖民地羅德西亞(現津巴布韋)1965年在其終審法院支持下單方面宣布獨立的例子,認為中方是吸取了國際經驗,決心不讓香港終審法院成為可以在憲制問題上決定香港命運的司法機構。
基本法草案是這樣通過的
未來香港將享有終審權,是基本法作出的具有石破天驚意義的規定。
這部莊嚴的全國性法律從起草到頒布的全過程都非常嚴肅、縝密,每一章每一條每一款甚至每一字、標點符號都經過了香港和內地起草委員們的深思熟慮,甚至激烈的討論。其中對于“國家行為”的表述是僅僅涵蓋“國防、外交”還是“國防、外交等”,這是個反復多次討論了幾年的老問題,結果誰也不能否認除國防、外交外,的確還有一些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區關系的事務屬于國家行為,這個“等”字不能省略。
基本法的每一條規定和所有附件草案,都是經過全體起草委員在1990年2月16日舉行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經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表決通過的。
記得會議閉幕當晚,全體起草委員和工作人員在北京貴賓樓飯店三層的咖啡座大平臺上聯歡,李后、魯平兩位秘書長興致勃勃地與秘書處工作人員一起合唱表演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末尾高潮《歡樂頌》的片段,皆大歡喜。
鄧小平關于香港問題的最后一次公開講話
1990年2月17日上午,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起草委員和工作人員。我作為草委會秘書處負責人、秘書長的助手,奉命在福建廳外的電梯口迎候中央領導。江澤民總書記先到,我迎送他去福建廳稍事休息,在途中把前一天基本法草案稿通過的情況作了匯報。
不一會兒,小平同志也到了。一進福建廳,江總書記就把這個好消息報告了他,小平同志連聲說:“好,好。”
隨后,中央領導們步向東大廳,接見草委會全體委員和工作人員,小平同志在熱烈的掌聲中發表了即席講話。他說:“你們經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杰作。”
小平同志講話字字千鈞。他剛一開始講,魯平副秘書長就示意我趕緊記下來,我忙掏出兜里常備的筆記本。接見一結束,我就從筆記本上撕下記錄稿送請魯平副秘書長審定,然后召集在場的所有中外記者,高聲朗讀,因為當時的香港記者聽普通話特別是四川口音普通話的水平還不高,所以要與他們一字一句地核對。
中午,我把記錄稿整理了一遍,斟酌了標點符號,經李后秘書長再次審定后送交新華社全文播發。這就是現在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小平同志關于香港問題的最后一次公開講話,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
后發制人,主攻八項主張
1995年5月5日,魯平主任就終審法院談判問題在北京召集國港辦、外交部、中代處有關人員開會,我赴京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魯主任傳達了錢其琛副總理的指示,要求我們對外積極表態,仍努力爭取在香港回歸前成立終審法院,以爭取人心。這個指示是談判進程的重要轉圜,策略從此轉為主動制勝。
5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政務組對外公布了八項組建終審法院的主張,其中除了重申中方專家在以往談判中提出的觀點之外,還提出終審法院應由候任行政長官來負責籌組,即以中方為主、英方協助。這八項主張亮出了中方關于終審法院問題的全部政策,在香港社會引起很大反響。
5月23日,我在香港堅尼地道28號結束中英財政預算案編制的專家小組會議,剛從談判大廳走下來,就看見包雅倫代表站在樓梯口等我,要求緊急約見。我雖有些意外,但還是立即同意了。
我們一起走進雙方共用的一樓休息室。他表示,英方已從傳媒上看到預委會政務組的八項主張,并且進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都能接受,將據此對已送交中方的條例草案再次進行修改,希望這一做法能受到中方的歡迎,使下次專家小組會議取得更好的進展。
我當即向包雅倫表示歡迎。回中代處后,我立即召集有關同事開會研究。中代處原以為預委會的八項主張會引起英方的強烈反對,現在看來,英方的態度也在發生重要轉變,逐漸向協商一致靠攏。大家認為,應該力爭抓住有利時機,在第七次專家會議上推動英方接受中方為主、英方協助的合作模式,由特區政府候任班子來籌組終審法院。若英方接受,我們可以預委會八項主張為基礎,對條例草案進行深入討論,繼續堅持按照基本法措辭表述“國家行為”;而對違憲審查權和判后補救機制兩個問題可持靈活態度,因為即使在終審法院層面放棄這兩個要求,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最高的決定權力,必要時仍能加以保障。
翌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綜合上述意見,向國港辦、外交部上報第七次專家小組會議的上會方案請示。
兩部的批復很快下來了,原則同意所提方案,并指示我們將終審法院的籌組和條例草案立法問題一攬子解決,爭取談成。
與新對手在酒樓里密商
就在專家小組會議召開前夕,英方突然通知,包雅倫代表因故急返倫敦,英方組長臨時由港英行政署署長賀理代替。
這一通知頗費思量,不知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后來很快得知,包雅倫并非因公回國,而是他的兄弟病故,回去料理后事。
新對手賀理是港英的一位資深政務官,從20多歲就來香港做英國政務官,曾經擔任過三位港督的秘書,精明、細致的作風在香港是出了名的。他能馬上進入原則性與靈活性嫻熟運用的外交官角色嗎?拭目以待吧!
5月30日,第七次專家小組會議召開。我按照兩部指示提出了解決香港終審法院問題分歧的一攬子方案。賀理在兩天的會議中,一直小心地烘托著良好氣氛,甚至在外交場合表現得過于禮貌和謙讓,會議結束我倆走出來會見媒體時,他還側身伸出一只手,禮讓我走在前頭,弄得我不得不放慢腳步,等他趕上來,并肩跨出門去。但是,他始終未就是否接受中方的一攬子方案作出明確表態。
31日晚,雙方專家組成員及工作人員在銅鑼灣一家規模不大但菜肴上乘的酒樓共進晚餐。到最后一道清蒸石斑魚上桌時,賀理離開了一會兒,回來時面部表情仍如白天似的讓人捉摸不透。但他湊近我耳邊小聲說,飯后要和我小范圍交談一下。
于是,我們找了個空包間。這時他才顯得有些不加掩飾的激動,但還是“有言在先”,禮貌地聲明以下要說的話“并沒有獲得授權”,需要等到交談后并得到了我的正式意見再報告上級,并說:“當然,您陳代表可能也需要報告中方的上級。”
很顯然,賀理是很會保護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他是在積極試探。但是,這次交談最終完成了談判進程實質性的轉折。
賀理提出五點意見:一是英方可以全部接受籌委會的八項主張;二是條例草案通過后,可以同意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候任班子負責籌組終審法院,英方加以協助;三是可以同意草案中用基本法規定的措辭表述“國家行為”;四是希望中方認可英方在違憲審查權和判決補救機制上的立場;五是若達成以上共識,希望中方公開支持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局,在7月之前通過。
我沒想到英方這么快就讓出了幾大步,賀理這么小心翼翼的港英官員居然在外交談判中顯示出這么大的魄力,背后必大有來頭,看來彭定康對外嘴硬,心里猴急了。如果這就是英方正式立場,那么達成協議已近在眼前。
我不露聲色地回應賀理:“我已清楚聽取了你的五點意見。遺憾的是我們這次專家小組會議對外宣布的工作時間已經結束。”
我思忖了一下,連夜將這重要的信息報告北京,加上北京批復需要的時間,估計一夜加上半天夠了,就用商量的口氣繼續說:“如果剛才你所表述的一切都不變的話,是不是明天6月1日下午兩點半我們再加開半天會議?你在會上發個言,把五點意見作一個正式聲明,我也作個正式回應,這樣雙方就可以記錄在案、立此存照,待下周舉行第八次專家小組會議時再最后敲定。”
可能是出于秘書職業的謹慎,賀理先是把我的話大致又復述了一遍,要我再次確認,等我確認了,他那溫和平靜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點頭同意。
當晚的中代處又是一個無眠之夜,通過電報將最新情況報回北京后,一邊等候指示,一邊預做工作方案。6月1日上午,北京果然及時回復,全部同意賀理所提五點意見,指示我在下午磋商中積極回應。
漢字和英文單詞的推敲較量
6月7日,第八次專家小組會議緊接著召開了。
包雅倫回來了,仍擔任英方組長,賀理坐在他的邊上。
可能包雅倫覺得那么重要的第七次加長會議他缺席了,或者還有些其他想法,會議一開始他講話中的意思似乎覺得那五點一下子全讓給中方有些虧了,職業外交官的做法可能是“化整為零”,一點一點讓步。
我立刻正色提醒他,這可是雙方在過往多次專家會議基礎上又加開了半天會,真誠合作取得的進展,倒退的后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對方一看苗頭不對,趕忙解釋,稱只是為了“修補、完善原有的共識”。
至此,雙方對協議內容已不存在分歧,磋商的重點迅速推進到中英文文本稿上。文稿由英方草擬,中方逐字逐句地與之討論。
有幾處地方反復交換意見仍未取得一致。我奉行的是“堅持原則,適當妥協”策略,為避免在文字糾纏中延誤談判進程,就在得到授權的范圍內,對某些表述采取了靈活態度。例如,文稿第四點原為:“中方同意在中英雙方達成協議后,經協商一致的《終審法院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應馬上進行并盡快在本屆立法會期結束前完成。中方將對此給予全力支持。”我稍作修改為:“中方同意在中英雙方達成協議后,經協商一致的《終審法院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應馬上進行,使之得以在1995年7月底前盡快完成。中方將對此給予全力支持。”既保留了英方希望中方“給予全力支持”的關注,又淡化了港英立法局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協議的影響,避免了可能引起“三腳凳”觀感的社會誤解。又如,第五點原為:“中英雙方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候任班子將根據基本法和并參照《終審法院條例》的規定負責籌組在1997年7月1日成立的終審法院,而英方(包括港英政府有關部門)將參與此過程并提供協助。”我將“和”字刪掉,打消了英方一再想把《終審法院條例》和基本法并列的企圖,以維護基本法在香港的小憲法地位。
英方最終同意了我們對中文稿的全部修改意見,但在英文文本的措辭上還保留一些分歧,例如對于“參照”一詞的英譯,英方接連拒絕我們提出的“with reference to”“taking account of”“having regard to”三個建議,主張使用“consistent with”,最后在確保和中文稿內容一致的基礎上,我們也采納了英方的意見。
經過兩個整天的緊張磋商,6月8日20時,文稿的絕大部分已經修改完成。我和包雅倫商定,簡單用完晚餐后繼續工作,當晚一定把文稿改完,同時我要求中方專家組內部作好文稿核定后立即上報的準備,爭取9日上午獲得批復并確認達成共識的文本,下午由雙方首席代表正式簽署。
五年談判換來19行文字
當晚23時50分,專家小組會議就全部文本達成了共識。回到中代處已是9日凌晨,我們將中英文本全文發回北京。幾年談判爭來論去,歸根結底,成果只濃縮在一張A4紙的寥寥19行文字里。
黎明時收到了兩部批示同意的復電。
6月9日上午,我和包雅倫在二層談判大廳正式對協議文稿作了最后確認。
會議結束,我走出談判樓對等候的記者們說:“很高興告訴大家,長達五年之久的設立香港終審法院問題,經過中英雙方協商,已經達成共識,并將在今天下午由聯合聯絡小組雙方首席代表簽署正式協議。這是一個完全按照基本法規定建立的終審法院,一個獨立完整的、史無前例的司法體系必定會在1997年7月1日的香港特區出現,它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有力保證。當務之急,是雙方都必須面對特區籌委會和特區政府候任班子即將在明年產生的事實。由特區候任班子負責籌組特區終審法院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重要體現。歡迎英方參與和協助,在辦成這件大事的過程里將有英方的一份貢獻。中方同意盡快完成立法程序。”
當日下午,趙稷華大使和戴維斯大使簽署了關于香港終審法院問題的正式協議。
談出了“以我為主”的感覺
1995年5月31日,我曾給魯平主任寫過一封信,其中一段內容是:“一旦中英就關于終審法院問題達成新的共識,意義很大。一是在我主動進取下,終于全部完成了1991年兩國政府首腦新聞公報中要求加快工作進程的兩件事(軍事用地、終審法院)。二是開創了以我為主、迫英居次的合作先例,香港過渡時期的交接工作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三是又一次消除了港人及國際社會對中方及香港未來的疑慮,增強了信心。”
6月9日協議簽署并對外公布后,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普遍認為香港司法體系在回歸前后的連續性有了保障,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法律真空,對于香港具有里程碑意義。英國幾乎所有的傳媒都對此熱議,一些媒體批評英方對中方讓步太多,也有比較持中的評價,如《金融時報》12日社論認為:“英方已經認識到,今后在諸如建立香港終審法院這樣的重大問題上,已經不能像以前在選舉問題上那樣單方面處理。英國大膽、單獨采取行動的日子已經過去,今后協作將占上風,中方將不可避免地發揮支配作用。”
其實,英國的傳媒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始終注視著香港問題的進展,進入90年代后對政權交接、平穩過渡的一是一非加以充分報道和評論,茲事體大,關系到英國的政治、經濟、外交,乃至海內外千家萬戶的國民。
9月29日,中英雙方舉行了香港終審法院問題第九次專家小組會議。中英雙方在協議確定的框架下,就法官選任、法院選址、一般職員任用等具體事項進行了友好協商,終審法院各項準備工作終于有條不紊地展開了。會后,我對記者們說:“現在距離香港回歸只有641天,還有很多有關政權交接的事宜要完成,希望在終審法院問題上的合作,以及所確立的中方為主、英方協助的模式,能夠為雙方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提供榜樣,使得香港能夠順利實現平穩過渡。” 最后,我吟誦了毛澤東在紅軍長征中所作的《憶秦娥·婁山關》,寄望未來:“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編輯 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