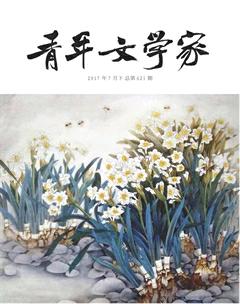眾語喧嘩下的世俗詩意
曹文婷++劉昕華
摘 要:進入新世紀后,不少詩人企圖通過親和民間的寫作立場來重回大眾視野。指涉現實的及物題材擴充了詩歌的容量,口語化的語言使詩歌不再為精英知識分子所獨享,向敘事文學借鑒的手法也讓詩歌在還原真實生活的同時,具有了更為沉靜悠遠的情思。世俗化的詩意使詩歌重煥生機,但若向其過度傾斜,也會讓詩歌因為詩意的缺失而走向末路。
關鍵詞:新世紀詩歌;世俗化;藝術向度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1-0-02
自1999年“盤峰會議”始,新世紀詩歌已經走過了十七年的歲月。盡管樂觀的評論家們始終認為新世紀“是新詩發展的最好時期”,但至少從目前來看,在人文科學遭遇極度漠視的當下,新世紀詩歌恐怕也未能完成突圍的重任,它的現狀大抵如謝冕所言——“奇跡并未發生”[1]。然而,市場經濟又并非單薄的它在,在消費文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詩歌這個往日如“繆斯”般不可褻玩的存在,如今也已走下神壇,逐漸向世俗傾斜,橫溢出世俗化的詩意。透過題材的及物化、語言的大眾化以及敘事的世俗化三個向度,我們也許可以對表面上熱鬧非凡的新世紀詩歌整體走向做一個粗淺的總結。
一、指涉現實的及物題材
詩歌曾是文學金字塔的頂端,精英知識分子為維護詩歌的健康和純粹,在選取入詩意象時,對瑣屑的日常生活是嗤之以鼻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的純詩意識、俄國形式主義以及羅蘭·巴特“不及物”主張等詩歌美學觀點引入中國后,更強化了絕大多數詩人的這種意識。他們認為,盡管采取親近社會現實及時代語境的姿態來寫作詩歌,可能在短期內會吸引外界的關注,但說到底因這些“非”詩因素引發的詩歌會損害詩歌的健康純粹,這樣的詩歌無法長期立足于詩壇,反而會使詩人遭人詬病。聯想到這一點,凡是愛惜自身詩歌名譽的詩人就都絕然不會貿然前往了。因此,與社會層面相關,勾連時代語境的題材和事物就如同瘟疫一般,讓當時致力于青春期寫作、純詩寫作、神話寫作等的詩人群體們避之不及,這在一定程度上將詩歌置于了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20世紀90年代以降,不少詩人發現了這一問題,并開始通過對“此在”世界的觸碰來對抗此前因為“不及物”寫作而導致詩歌陷入的神秘與虛無境地。新世紀詩歌延續了這一傳統,一方面,詩人將個人情感與日常生活體驗緊緊結合,在瑣屑事物中來建構自己的詩歌美學。如王小妮的《一個人輕易改變了一座城》:“吃半碟土豆已經飽了。/送走一個兒子/人已經老了。”日常生活中帶有情感的觸動,語言簡約卻飽含深重;“打工詩人”鄭小瓊粗糲地描繪著底層勞苦大眾的生活,工廠的流水線、冰冷的車間、猙獰的機器……潛藏在工業生產時代的反人性特質被無情揭露。另一方面,進入21世紀后,國家遭遇了一系列事故,“非典”、冰災、地震……災難接連發生。所謂“家國不幸詩家幸”,太多觸目驚心的現實題材,讓詩人避無所避。如汶川大地震之后朵漁的《今夜,寫詩是輕浮的……》,拋卻無謂的煽情,朵漁直率的語言及清醒的反思彰顯出死亡的沉重,顯示出了新時期詩人應有的承擔意識。
“及物”的詩歌題材可以延展詩歌的廣度和深度,但把這種“及物”視作詩歌創作的唯一籌碼,不加節制不經剪裁地直接搬入詩歌中,最終只能導致詩性的淪落和泯滅。詩人榮榮的著名詩作《魚頭豆腐湯》,其詩歌主體是一道菜的描繪,雖然詩人認為自己這樣“隨手寫下”的詩歌是“不急功近利,不空,不無病呻吟,不虛情假意”的[2],但不可否認的是,企圖通過對世俗生活的詩意化的包裝來闡發詩意的做法,得到的只能是對人生膚淺的詮釋與注解。詩歌可以“及物”,但這種“及物”也應有度,一旦“及物”流于泛濫,就容易折射出作者把控能力的孱弱和詩歌精神的萎靡。
二、貼近草根的大眾語言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句話對于詩歌來說則更甚。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新世紀詩歌口語化的趨勢已呈彌漫之勢。有論者認為,新世紀詩歌口語化的態勢是由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詩人”和90年代以韓東、于堅等為代表的“民間詩人”推動的。這兩次浪潮所針對的詩歌現象不同——前者劍指晦澀難懂的朦朧詩,后者則是對‘知識分子詩人的詩學觀念進行反撥,但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詩歌走向民間、走向大眾。
與詩歌文學金字塔的形象相對應,由精英知識分子寫作的詩歌,其語言也應是相當精煉凝重的。詩歌語言的這種特性一直以來維護了詩歌的高潔純粹,進入新世紀后卻越來越成為一道的枷鎖,它阻礙了詩歌與世俗大眾間的正常交流,將詩歌圈禁為知識分子的專利,使詩歌萎縮為一種“小眾”的藝術,這顯然與現代藝術反叛權威,迎合大眾的潮流相悖。口語并非專屬于庸常大眾,也并非不能表達出深刻的玄思。事實上,真正的表達奇才,即使面對最尋常的生活,也能準確抓住生命要義。口語所具有的直白、粗糙的特性,恰好能軟化此前被意識形態鉗固住的詩歌生硬的寫作模式,給詩歌注入幽默、輕松、人間化的成份,充盈詩歌的質感,從而使現代詩歌重獲生機。
口語化的語言拓展了詩歌的接受面,但過于口語化的詩歌也可能造就垃圾。詩人趙麗華有很多這方面的詩歌,隨意摘錄兩首:
“詩人們相約/去北京西郊找桃子/問我去不去/我說要是研討/我就不去了/但摘桃子好玩/遠勝過摘花”
——《摘桃子》
“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后/不沖刷/便池的人”
——《我堅決不能容忍》
在她的作品中,我們沒有感受到任何為人稱道的詩意,去除分行之后,甚至無從將其所謂“詩歌”與傳統散文區分開來。極端的口語化降低了詩歌寫作的門檻,但稀疏的詩意也使詩歌失去了應有深刻涵義。口語化擴充了當代詩歌對現代生活的容納度,但物極必反,不加節制地濫造口語詩歌,也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三、重回人間的敘事詩學
中國古典漢語詩歌一直都是秉承“詩緣情”、“詩言志”的詩學傳統,抒情性長久以來都是詩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表達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詩歌的這種抒情性卻大為降溫,究其根本,大致可有兩個原因:一是,現代都市生活的快節奏擠壓了人們的精神空間,社會整體心理浮躁;一是,在相對太平的世俗年代,物質條件相當富足,多發感慨也顯得略微矯情。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詩歌的抒情美學被逐漸擱置,這種傾向在后朦朧詩中就略顯端倪。在他們的詩中,詩人的情感態度和立場都異常淡漠,讓人感覺不到一絲溫度。進入新世紀后,隨著詩歌與現實社會交匯點的增多,詩人不再滿足于往日的冷抒情,而是借鑒敘事文學的手法,加重了對世俗生活的描繪,使詩歌獲得更切合時代的大容量。
在孫文波看來,詩歌的“敘事性”主要在于展現生活準確的細節,以獲得更“清晰、直接和生動”的圖景[3]。而這種更“清晰、直接和生動”的效果,也使詩歌具有了更直接的溫情。如馬永波的《幸福的蒸汽》,“她還是像在老家的縣城那樣習慣早起/或者當外面黑暗一片的時候/就能聽見她在廚房里忙碌的響動/往常冰冷的廚房也慢慢熱了起來/不久玻璃上就滿是蒸汽/這些白色的香噴噴的精靈/消散,只是升高,升高……”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準確描寫,盡可能地保證了畫面的清晰、生動,依靠這些澄清透明的世俗片段,既還原了真實的生活,也使作者在其中寄寓的情感變得沉靜而悠遠。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的敘事并不是全番鋪陳純粹事實,詩人的敘事應當只是在局部強化細節并滲入感情,通過此類細節的真實讓詩歌獲得更為直接的感染力,因此這種敘事仍是一種詩性敘事。大多數打工詩歌、底層詩歌企圖以流水賬式平鋪直敘的記錄來呈現真實的底層人民生活,這樣的試驗只能因為詩性的缺失而走向失敗。謝湘南的《一起工傷事故的調查報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詩中詳盡寫明了傷者姓名、年齡、受傷原因、傷況等,展現出底層打工者們處境之艱辛。但是,過于連貫的線形思維方式驅走了詩歌固有的凝練,也有悖于詩歌精美的品性,這都使得詩歌失去了應有的審美妙趣,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結語:
新世紀后,網絡的出現及普及大大推動了詩歌世俗化的進程。橫溢的世俗詩意使得人人都能參與到寫詩這一場“狂歡”中來,新世紀詩歌一度呈現出熱鬧非凡的景觀。但我們同樣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詩歌的世俗化不應是一劑猛藥,適量適時的“還俗”才能使詩歌重獲新生。
參考文獻:
[1]謝冕.奇跡并未發生——新世紀詩歌觀感[J].理論與創作,2012(4).
[2]榮榮.讓詩歌擁有一顆平常心[J].詩刊,2003(6).
[3]孫文波.語言形式的命名[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