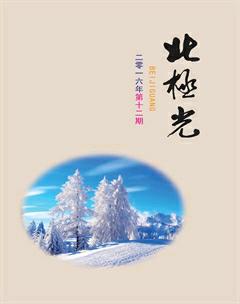納蘭性德和倉央嘉措詩詞中佛學色彩研究
趙芳芳
摘要:生于大清富貴之家卻厭惡官場的險惡,愛妻亡故后飽受佛學思想的影響,痛苦煎熬的人生經歷使得納蘭性德對佛教感悟透徹深刻,佛學修養對納蘭性德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生于寧瑪派紅教的家庭之中,自小受到寧瑪派教義的熏陶,后卻不得已成為了格魯派黃教的首領,黃教束縛人性的戒律使得倉央嘉措受到禁錮,孤獨痛苦,他并不反對佛教,只是在黃教的戒規下反抗,他的佛學修養也在他的詩歌中有著很深的影響痕跡。兩人都與佛學有著不解的淵源,他們的作品也滲透著佛學的思想。
關鍵詞:關鍵詞:納蘭性德;倉央嘉措;佛學色彩
納蘭性德和佛教之間有剪不斷的緣分。首先是納蘭家族內開放的學習風氣,納蘭明珠雖為滿族貴胄但他不像其他滿清弟子那樣只知習武弄棒,而是對漢文化有極大的興趣,這深深影響了納蘭性德,在納蘭性德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很多的漢文化,使得納蘭性德自小就有一種漢文人情懷。而清朝對佛教的政策幾乎完全是繼承明代的,佛教成為了統治階級思想統治和精神統治的支柱之一,受到統治者的支持和保護,滿族貴胄早在關外時期就有了崇佛活動,康熙皇帝雖然自幼潛心誦讀孔孟儒家經典,尤其受到了程朱理學家傳統哲理的很深影響,不好仙佛,清圣祖雖然多次表達了厭惡佛教及佛教徒的想法,可是他也充分認識到佛教是統治人民的有力工具,因而對佛教也持保護態度,康熙皇帝在位期間六次下江南,多次東巡,幾乎每次都要參禮佛寺,接見僧人,題寫碑文、匾額等,這樣納蘭就有可能接觸并了解到佛教。其次,種種痛苦和不幸使得納蘭性德對佛教有了體悟和依賴。愛妻亡故,侍衛生活的束縛,官場的險惡,現實和理想的沖突,這些現實的痛苦使得納蘭無法排解,愛妻亡故后納蘭在雙林禪院為其守靈期間開始對佛教產生了不解之緣,納蘭性德在精神上開始依賴佛教。再次,悲天憫人,“諸法無我”的佛教對天性淳樸的納蘭性德具有極大的內在吸引力,他對佛教極其的虔誠,在他的詩中有表現出來,“凈消塵土禮金經”是說納蘭抱著一顆虔誠之心整理那些蒙塵的佛經。納蘭性德與佛教的不解之緣就此展開。
納蘭性德高度重視佛教,充分肯定佛教,讀了不少的佛教書籍,他在《淥水亭雜識》中這樣寫道:“人世事,釋典無不言之”,這里的“釋典”需要言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人世事”,由此可見,納蘭性德所讀的“釋典”絕非是一兩部,而是很多部。正因為讀了不少的佛教書籍,納蘭性德才會了解熟悉很多的佛教事物,納蘭還與僧人交往,不過,佛教思想對納蘭性德詩詞創作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整體的,并不是每一篇都是明確和直接的。
作為藏族人民根深蒂固的信仰的佛教,而倉央嘉措又是六世達賴喇嘛活佛,那么他對佛教的研習自然就不在少數。倉央嘉措自小就出生在一個信仰紅教的家庭之中,自小就受到寧瑪派教義的熏陶,八歲的時候又到巴桑寺受教,在巴桑寺受教七年之后,終于被認定為活佛,受戒于五世班禪,認五世班禪為老師,后在布達拉宮內舉行坐床儀式,接下來就一直在布達拉宮內接受經師的傳教,研習了很多的佛教典籍,諸如薩迦、格魯、寧瑪等各種有成就的經藏、密咒、教規等等無所不學。倉央嘉措還參加宗教活動。倉央嘉措自小就侵染在佛教的氛圍中,從沒有離開過佛教的影響范圍,由此可知,倉央嘉措的佛法修為應當不淺。倉央嘉措既是轉世的活佛六世達賴,更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的詩歌反映了他的心境,他在詩歌中表現出的反叛指的是扼殺自由的格魯派森嚴的戒律合束縛人性的禁欲主義,并不是整個佛教,因為他自小受其熏陶的紅教寧瑪派是可以享受愛情結婚生子的,而他人住布達拉宮后便成為傀儡,被禁錮了起來。
倉央嘉措是18世紀青藏高原上謎一樣的人物,一方面是因為他作為六世達賴活佛,卻生性逍遙,多次被拉藏汗說是假活佛,但西藏人民認為他是“迷失的菩提”,他對此事更是無所謂,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詩歌,從字面上理解,他的詩歌很容易被認為是“情歌”,可是他是活佛,他的詩歌真的只是“情歌”嗎?他能擺脫活佛的身份束縛嗎?現今學術界內對倉央嘉措詩歌的解讀無外乎有三種看法,一種是情詩,還有就是政治詩和宗教詩,我不能說誰對誰錯,但我比較認同政治詩和宗教詩的說法,倉央嘉措再怎么叛逆,灑脫風流,但是他擺脫不了活佛的身份,擺脫不了從小受到的佛教的熏陶,一個人的外在是表象,是擺脫不了內在的,內在的品質是不會受外在壞境的束縛而受到質的變化的,倉央嘉措就是如此。從原來的藏文來看,倉央嘉措所寫的“情”歌其實與情無關,班丹先生在他的文章《瑣議倉央嘉措情歌篇名、幾首道歌譯文及其他》中這樣說到:“佛教前宏期“Mgur”和“glu”的含義相同。對于富于宗教內容的“glu”有時叫做“Mgur”,有時叫做“glu”,但無敬語之意。而佛教后宏期,“Mgur”和“glu”的含義有區別,“Mgur”仿佛成了glu的敬語,漸漸地民間流傳的glu叫做glu魯,而稱活佛僧人所賦glu為Mgur(古爾)。既然如此,倉央嘉措和米拉日巴都是佛門弟子,為何把《倉央嘉措古爾魯》譯成《倉央嘉措情歌》,而把《米拉日巴古爾魯》譯成《米拉日巴道歌》。”從倉央嘉措詩歌的內容上來看,他的每一首詩幾乎都可以從宗教上來解讀,都是弘揚佛理的道歌。作為西藏紅教格魯派的領袖活佛,倉央嘉措佛理入詩是順其自然的,“在其詩中因果法則;緣起性空;生命無常;覺悟解脫才是永恒;真與善是佛法追求的道德與是非;佛法是真理是永恒的;真理的標準是自心;涅槃是絕對真理;明心見性是真與善;真理是人與生俱來的意識……這些佛教講的真理都體現在倉央嘉措的詩作中。”倉央嘉措的很多詩作表面上描繪的是兒女情長之類的,實際上通過晦澀的描寫倉央嘉措的處境,用代指、譬喻或者暗示的表現手法,隱晦的表達了佛教中的某些觀念和倉央嘉措本人的佛學體悟。
總之,納蘭性德和倉央嘉措都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他們都對佛學有著自己的見解和想法,均反應在各自的詩詞創作中了。
(作者單位:西藏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