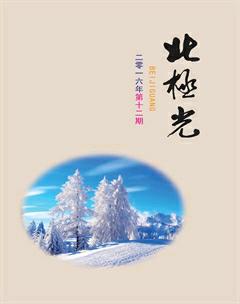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完善路徑
摘要: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自建立以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協商動力不足、現有法律規范約束不夠等問題。應該在充分了解我國工資集體協商特點的基礎上,改良協商模式,完善協商法規,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關鍵詞:工資集體協商;法律規定;完善
一、問題的提出: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實施中存在的矛盾
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工資主要由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協同調節,完全依賴任何一方的調節方式均難以有效保障勞動者權益。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可以彌補市場調節機制的先天不足,成為改善勞動者福利,緩解勞資矛盾的制度選擇。
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在借鑒西方集體談判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于2000年在立法中正式確立。近年來,工資集體協商的發展規模逐年提升,覆蓋面逐步擴大,在保障維護勞資和諧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的成績不容否認。但由于建立的時間較晚,我國工資集體協商缺少必要的理論基礎,在十幾年的推進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矛盾現象,如:工資集體協商的形式化現象嚴重,勞動者參與的比例不高,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偏低,“重簽訂,輕協商;重文本,輕履行”等等。
這說明現有制度在設計上存在缺陷,尤其是相關法律規定過于粗糙,導致實施效果不夠理想。因此,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二、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工資集體協商既有模式的動力不足
第一,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是以合作為導向的政府主導模式。由于勞資關系的自治化程度不高,長期以來沒有形成良好的談判傳統、成熟的談判技巧,這種“自上而下”模式的好處是政府作為工資集體協商的主力,能迅速提高協商的覆蓋率,適當緩和勞資沖突;但最大問題是制度本身的動力不足,易造成工資集體協商形式化。協商主體對政府產生過度依賴,不利于培養勞資雙方的自主意識,消減了勞資雙方主動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的積極性,并且容易使協商偏離法制軌道。
第二,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主要在企業層面展開,結構單一。從現行立法來看,法律規范主要涉及企業一級的工資協商,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的立法與實踐均處于起步階段。協商結構過于單一不利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因為僅憑借企業一級分散的集體協商未必足以與資方相抗衡,同時也不能充分滿足中小企業和集群性產業等企業類型的需要,不利于行業的整體發展和穩定。
(二)我國工資集體協商法律規范的約束不夠
首先,現有立法層級相對較低,影響法律效果發揮。目前,調整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規范如《集體合同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屬于部委規章,立法層級較低。部分地方政府出臺的工資集體協商規范,往往以“指導意見”或“工作通知”形式出現,實踐中很難成為規范工資集體協商的有力手段。
其次,現有立法的強制性不夠。如:《勞動法》、《工會法》中關于勞資雙方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規定多為任意性規范,使工資集體協商強制性大打折扣。在資強勞弱的背景下,工資協商權實際上并未公平的分配給雙方,與勞動者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并未成為法定條件下用人單位必須履行的義務。
最后,現有立法規定過于原則,導致可操作性不強。工資集體協商是一項復雜的制度,其中涉及協商代表產生、內容選擇和程序規范等一系列具體問題。而現有立法對協商主體在協商過程中的權利義務、協商不果如何處理、政府參與工資集體協商的界限等問題往往只做了宣示性的規定,立法規范不夠細化,導致實踐中工資集體協商的可操作性不強。
三、完善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路徑
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要遵循我國集體協商機制在市場運行中的客觀規律,重點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
(一)改良協商模式,形成中國特色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政府主導型的工資集體協商模式仍然適應我國現階段的實際隋況,但應對其進行完善、改良:
第一,進一步明確政府在工資集體協商中的作用,讓其逐步從協商的具體事務中退出來,充當服務者、監督者的角色。政府可以成為工資集體協商的主要力量,但其起作用不應單純依賴于行政命令,而應在勞資雙方自由協商的前提下適度的發揮協調監督作用。政府的工作重心應放在促進工資集體協商外部環境構建、制定和健全法律保障體系和強化處理勞資關系的服務能力等方面。
第二,大力發展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如果只是單一在企業層面展開協商對話,那么企業工會很可能因為對行政方的天然依賴,使集體協商的效果大打折扣。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在協商層次、覆蓋范圍、提升合同質量等方面都有著獨特優勢,不僅能夠擴大工資集體協商的覆蓋范圍,改變目前勞動者維權“原子化”的狀態,而且有利于工資集體協商內容更具針對性,避免協商內容的單一化,提升工資集體協商協議的執行效果。
(二)完善立法,增加工資集體協商可操作性
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要有法律的“保駕護航”。
第一,加快修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規范中關于工資集體協商的規定,適時出臺《集體合同法》、《工資支付條例》等法律規范,提升工資集體協商法律制度的效力等級。
第二,增強工資集體協商的強制力。將法律條文中的“可以”改為“應當”,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不論是否建立工會,只要符合法定條件,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應當成為單位的法定義務,使工資集體協商由過去的選擇性規定變為強制性規定。
第三,細化工資集體協商的各項法律規定,提升制度的可操作性。進一步明確工資集體協商的程序定;重點解決二次協商的程序、效力;明確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的主體、程序和合同生效等規定。
(三)完善配套措施,提高工資集體協商質量
工資集體協商的完善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提高工資集體協商質量,還要注意相關配套措施的完善。
第一,加強輿論引導,減少協商阻力。利用網絡等媒介,宣傳工資集體協商對于構建和諧穩定勞動關系、實現勞資雙贏的重要意義;還可以通過培樹典型,經驗總結等方式進行推廣交流,擴大社會影響力。
第二,提升協商水平,提高協商質量。政府和工會應通過各種方式培養協商主體的協商技巧,強化協商主體的知識能力,提高協商質量。各相關部門應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及時處理工資集體協商中的問題,確保協商結果的實現。
作者簡介:
張琳(1977.12-),女,漢族,陜西西安人,現為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講師。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