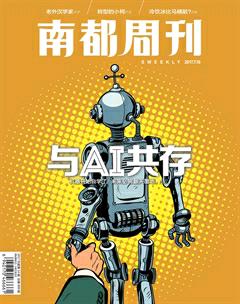是椰子殺人多, 還是鯊魚殺人多?
July

《我是布萊克》在戛納引發(fā)的爭議無非兩點:金棕櫚從熱門《托尼·厄德曼》鼻子底下溜走,被老邁的黑馬攬住,引起噓聲一片。然則80歲的老導(dǎo)演肯·洛奇,幾十年如一日聚焦底層人民,冷靜自持的鏡頭和不帶煽動性的悲憫,并不太容易被求新求變的世界笑納。
然而,當(dāng)你靜靜看完這部電影,只想默默起身脫帽致敬。
這部電影像歐茨的小說,創(chuàng)作者對主人公飽含深情,卻從不施予半點希望,有的只是樸實、悲哀和宿命。就連那句“豈不知屈辱的可怕,但更無奈地知道生活還要這樣繼續(xù)”,都仿佛是布萊克生活的注解。
故事很簡單,鰥夫布萊克因心臟病無法繼續(xù)工作,在與福利部門的拉鋸戰(zhàn)中,屢屢受挫,求告無門,走投無路。在就業(yè)中心,他遇到了因為配房政策而從倫敦趕出來的單親媽媽。兩個過得像鬼火的人,擁擠在一起取暖。
老木匠變成新時代的文盲和廢人,被國家棄若敝屣,但布萊克始終保持著自己的體面,循規(guī)蹈矩、文明謙和、良善助人,跟凱蒂一家愉快相處,敞開胸懷跟年輕人溝通,獲得微薄的快樂,生活還有那么點余裕和退路。如果說底層人物身上有光,是因為他們活得令自己尊重。
然而這一點尊嚴(yán),在單親媽媽凱蒂那里得到了反襯。跟布萊克不同,她還年輕,有滿腔的抱負(fù)和伸出手就可行的計劃。但螻蟻掉進(jìn)了夾縫,眼看抬頭有光,卻怎么也夠不著。人生如寄,倉促安身,詩和遠(yuǎn)方都是奢侈品,抵不過眼前的饑餓,抵不過孩子們嗷嗷待脯的嘴,抵不過擦浴室時突然掉下來摔碎的瓷磚——任何一點打擊,都像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她在超市偷竊衛(wèi)生巾還情有可原,在救濟(jì)站打開罐頭抓起來吃得滿口殘汁,已經(jīng)失去體面,最終迫于生計淪為流鶯,就是徹底的慘敗。
人物和周身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人物互動的關(guān)系,在影片內(nèi)里形成強(qiáng)大張力,表面上不徐不疾的節(jié)奏卻充滿焦慮感,一根皮筋繃到快斷裂。
這場劍拔弩張的對峙中,沒有一個人顯露了絕對意義上的惡。冷漠刻薄的公職人員,是末端執(zhí)行的棋子。哪怕是其中有一位女公務(wù)員,不忍心看布萊克像皮球一樣被人呵來斥去,心懷憐憫地勸解他“我見過多少像你一樣的好人,因為不配合而最終淪落街頭”,但那也是用其軟肋戳其軟肋,換了個方式讓他下跪。
溫和中的殘酷更殘酷,一個有良知的螺絲釘無法撬動腐朽的大機(jī)器,見多了痛苦的泛濫成災(zāi),也就鈍感了。
忿郁,最先擲向了繁文縟節(jié)和所謂的官僚主義,可它們只是餌雷,隱藏在背后的社會體制和吃人制度,種種偽善、腐爛、壓榨、不公,才更深巨、更嚴(yán)酷,更“不可說”。縱然有過一小爐火,但對真正貧寒的人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他的寒冷太過巨大,他的世界就是冰窟。


電影里有一個隱喻,布萊克問凱蒂的孩子:“是椰子殺人多,還是鯊魚殺人多?”掉在樹上的椰子,看上去無害無棱角,實際上比舔著血盆大口的鯊魚更可怕。直接的殺戮尚可反抗斗爭,揮霍生命的血性,但無人預(yù)知何時走到人生的路口,就被一個椰子砸死了。
任何一樁看得心酸、心冷、心寒的故事,并非全因為事情本身的悲慘,而是在潛意識里,作為旁觀者懷有的唇亡齒寒、兔死狐悲的心情。最怕好人沒有好報,不是因為天不開眼,而是因為呼天不應(yīng)的人禍。你不知道,哪天你會是下一個布萊克,哪天你也會被椰子掉下來砸得頭破血流。
他不是懶人,不是小偷,不是乞丐盜賊;他不是一串社保號碼,不是屏幕上一段數(shù)據(jù);他按時納稅,一分不少,為此深感自豪;他不向權(quán)貴卑躬屈膝,誠心對待鄰里,盡自己所能伸出援手,他不接受更不尋求施舍。他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搖尾乞憐的狗。他活得有尊嚴(yán)、體面、文明,但他的死,卻像是一種報應(yīng)。
極其簡約極其冷酷,就像抽過來的一記耳光,扇在“被福利化”的底層生活的嘴臉上。電影里流淌的率真之氣、從容之力、硬朗之骨、赤子之心都令人尊敬。唯一的欣慰就是,一直到死,布萊克都沒有低頭。凱蒂在葬禮上念出了他來不及申訴的信:我,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個公民,無所奢求,無可妥協(x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