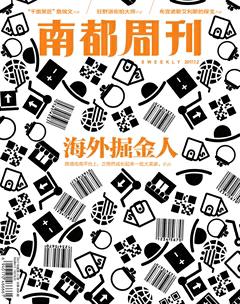威尼斯餐館的意大利面課程
端午過后的傍晚,我在臺北家中烹著西紅柿海鮮意大利面,想起那年夏末在威尼斯一家餐館,曾目睹一堂生動的“意大利面初級課程”。
那家小館坐落在美哉圣母廣場附近,是我的意大利烹飪老師最喜愛的威尼斯館子之一。老師交待了,要么幾天前就訂位,要不在小館傍晚一開門那當兒過去碰碰運氣。那天算我們走運,趕至小館時,見靠門口柜臺邊有張小桌還空著,留著花白絡腮胡的掌柜說明,這桌因坐起來不是那么舒服,一般不給訂位,我們若不介意,可以入座。我們哪敢嫌棄,立刻點頭。
小館沒有正式菜單,只有手寫影印的薄紙一張,說明本日菜式;柜臺上擺了好幾種開胃冷菜,任由店家當場隨意搭配的什錦開胃菜是該店招牌。我們不多想,點了一份。
從我們坐下到點完菜,每隔一會兒,就有新客人上門,凡是沒訂位的,一律遭到婉拒,有兩對美國夫婦卻怎么也不死心,癡癡地守在門邊,這一下可好,愛排隊的日本觀光客也跟進,形成了八九人的隊伍。
掌柜大叔嘆了一口氣,走到門邊,以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說,“各位,別排了,你們沒看見我們已經沒法接待新客人了?”日本人聞言,靜靜離去。
有4位美國人則堅持在門前邊聊邊等,我雖不想竊聽別人談話,但他們侃侃而談,我不想聽都不成。這兩對夫婦彼此并不認識,只是湊巧同時經過小館,見里頭人多,猜想一定好吃,決定就地等座。身材健壯、金發的那對來自俄亥俄州,年長的另一對則是明尼蘇達人。
掌柜替我們送酒過來,見到此景,忍不住嘟嘟嚷嚷,“美國人,干嘛不去麥當勞,那不是你們發明的?”我的意大利文雖差,這兩句話卻給我聽懂了,趕緊翻譯給約柏聽,兩人一頓好笑。
有道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就在我們享用過美味的前菜,等候面食上桌時,隔壁桌空了出來,美國人有位子了。他們4位七嘴八舌一陣子,終于點好酒、菜,聲浪這才漸漸小下來。
過了一會兒,我見到女服務員走到掌柜身旁,面有難色,低聲說了什么,他聞言雙眼圓睜,大聲說:“只能給面包,不能給干酪。”
服務員回到美國人的桌旁,用流利的英語解釋,“老板很樂意多給面包,但是干酪不能給。”掌柜這時也走過去,鄭重宣示:“先生女士,面包是沒問題的,要吃多少都行,可我絕不能給你們干酪。”
他比手劃腳,繼續以其意式英語說:“你們這一盤面有大蝦加貽貝,要吃的是海鮮的清甜,干酪這一撒,什么味道都給蓋住了。只有在美國,才會有人吃大蝦加干酪,真想這樣吃,請回美國再吃。”
在旁好奇窺看的我,聽見掌柜如此唱作俱佳地“教導”兼“搶白”,禁不住像聽了歌劇詠嘆調似的輕聲叫好。掌柜言畢,向四個美國人微微頷首、轉身,經過我桌旁,淘氣地對我眨眨眼。想來他聽到我的喝彩,我恐怕喊得太大聲了。
其實,我也犯過和4位美國人一樣的“錯誤”。多年前初接觸意大利菜時,同樣以為凡是意大利面就得加干酪。后來結交意大利友人,并至佛羅倫薩上烹飪課,這才了解意大利人吃面食有個通則—魚或蝦貝菜肴多半不加干酪,以免香濃的干酪奪味。可當我學會這一點時,已不知用干酪破壞了多少盤海鮮意大利面。
坦白說,我挺欽佩這位威尼斯掌柜,他堅持原則,不怕得罪客人。從他身上,我仿佛看見意大利人對美食的那股執著且不妥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