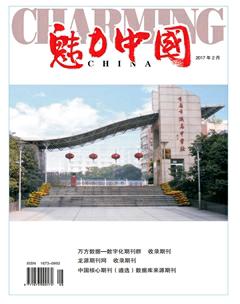從笙的改良看我國民族樂器的發展
張現增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樂器。作為中國古老的一種民間吹奏樂器,深浸著豐富笙文化特色的華夏藝術,并以其獨特的音色和韻味深受人們的喜愛。隨著民族文化的發展,已經由民間形態向專業形態演變,開始步入現代教學之列。
一、笙的結構
(一)笙的構成
笙在我國古代樂器分類中,笙為匏類樂器。笙的構造比較復雜。它是由笙斗、吹嘴、笙苗(又稱笙管)、笙角、簧片和腰箍等部件組成的。笙斗圓形,笙斗和吹嘴銅制,焊接后合為一體。笙管上端有長方形或亞鈴形出音孔,下開圓形按音孔,下端與笙角相接。笙角為紅木或黃柏木制錐狀體,插人笙斗部分鑲簧片。簧片響銅制,長方形,其根部與簧片板連接,經過抹綠(用五音石磨出銅綠涂抹簧片,彌合簧縫,并可防銹)和朱蠟(用蜂蠟、松香,朱砂或銀朱配制)點音(又稱點簧,置于簧片尖端,可調整音高)而成。笙管依發音高低而長短有別,中下部用腰箍固定。右留缺口可容手指按音。
(二)笙的種類
隋唐時期的笙有19、17和13簧多種;后來又流行一種17簧義管笙,這種笙在17簧以外另備兩支“義管”供轉調時替換用。后來19簧笙也失傳了。
北宋景德三年(1006),宮廷樂工單仲辛制作19簧笙,此后19簧笙在宮廷和民間又得到了普遍的應用。
笙管多為竹制,現為銅質。明、清以來,流行的笙多為17簧、14簧(方笙)、13簧和10簧。現在民間使用的笙有13簧、14簧、15簧、17簧等多種,但以14簧、17簧最為流行。
二、笙在國外的傳播
我國的笙對西洋樂器的發展,曾經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笙最早就通過“絲綢之路”傳到波斯,1777年法國傳教士阿米奧又將笙傳到歐洲。
1780年,僑居俄國的丹麥管風琴制造家柯斯尼克,首先仿照我國笙的簧片原理,制造出管風琴的簧片拉手,自此管風琴才開始使用音色柔和悅耳的自由簧。
18世紀末,俄國科學院院士雅·什太林,曾撰文稱贊笙是“最受歡迎的中國管風琴”。以后,又促進了其他自由簧樂器的產生。1810年,法國樂器制造家格列尼葉制成了風琴;1821年,德國布希曼發明了口琴,次年又發明了手風琴。
我國的笙、竽在盛唐之時東傳日本,在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里,現存我國唐時制作的吳竹笙、竽各兩支,假斑竹笙、竽各一支,皆為17管,其排列方法均呈馬蹄形,唯彎曲的吹嘴特別長,斗上都有油漆彩繪的人物或風景畫。古籍中所說竽為多管,而正倉院所存的唐俗樂使用的竽,則與笙同為17管。
三、笙在樂隊中的作用
笙是吹管樂器,但又是通過銅質簧片的振動而發音的,因此具有簧、管混合音色,高音清脆、透明,中、低音優美、豐滿,柔和,易與其他樂器的音響融合。
笙的音色與簫、笛、管比起來,缺乏個性,音質也較為浮泛,穿透力較差,深度和力度不夠,但它卻是一個很好的伴奏樂器和合奏樂器。笙的簧、管雙重音色及自身的和聲配置,使笙的音響具有很強的協調性。在管弦樂隊中,笙是最理想的“溶合劑”,它可以與吹、拉、彈三組樂器結合得很好。
在河北吹歌、山東吹樂和遼南鼓吹等民間吹管樂隊中,笙也能起到調和樂隊音色的作用。在齊奏中能豐富樂隊的音響效果,使之統一、和諧而豐滿。笙在江南絲竹、常州絲弦、福建南音、山西八套和西安鼓樂中,也是不可缺少的配奏樂器。還用于昆曲、越劇等地方戲曲音樂伴奏。笙在民族管弦樂隊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有時要用到高音、中音和低音三種笙。在中西混合樂隊里,笙也能收到良好效果。
四、從笙的改革看我國民族樂器的發展
笙的改革,主要是以增加簧數擴展音域為目的。為適應樂隊的需要,能夠自由轉調,演奏家們研制出了加鍵笙。目前樂隊中使用的高、中、低鍵笙系列確實為樂隊的建設解決了很大的問題,豐富了樂隊的音響,演奏員不再為缺音少調而苦惱。但是也帶來另外一個問題:許多改良笙無法演奏的笙技巧和樂曲。而民族樂器向來是以它的個性突出為特點的。在演奏時,尤其是笙的獨奏技巧,如何在音樂作品中仍得以展現,傳統的名作如何去繼承、發揚?新創作的作品如何保持笙原有的風格和特色,這些問題困惑笙演奏家們,一臺晚會至少要準備兩只笙,一只用于獨奏,一只用于合奏,用于樂隊的加鍵笙不能演奏民族風格濃郁的傳統樂曲,一些獨特的技巧被削弱了,而用于獨奏的笙又因為音域窄、半音不全而無法適應樂隊的需求;再者加鍵笙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由于音位排列和持笙方法的改變,拿到一個加鍵笙后,除了口型不變外,其他的都要從頭學起,給演奏者帶來了額外的負擔。
我國樂器的改革,多是圍繞在解決笙、笛等民族樂器在樂隊中的轉調的矛盾問題,五六十年代隨著樂隊規范發展、作品現代化、演奏欣賞要求的提高等現實情況,許多演奏家、笙制作家將原來的傳統笙不斷改進,在原十七苗十三簧笙的基礎上研制出了十七簧帶有半音的改良笙,隨后相繼出現了二十一簧、二十一簧、二十四簧、三十六簧等園笙等,后為了解決民族樂器缺少低音的實際情況,又出現了三十六簧方笙及中音排笙、中音抱笙、次中音抱笙、低音排笙、低音抱笙和鍵盤排笙等。
許多民族樂器在解決了轉調難的基本問題以后,卻失去了它原有的本質的特色——“音色”,如笛子在加了鍵、打了空后,不僅音色改變,許多傳統笛中的抹音、滑音等技巧也隨之失去,如果笛子改革后的而使其原有的音色改變,那么也就失去了它改革的意義,必然會遭到非議。又有一些樂器改革后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比如;琵琶采用十二平均律品位后,一是對于聽慣了中國傳統五度相聲律的民眾的耳朵來說,無疑存在一個不適應的問題,二是因其中某些品位間距變小了,有礙于某些演奏技巧的發揮。但隨著大多數演奏者對此類改革的接受,以及它在民族樂隊里所發揮的作用,又充分證實了它改革成功的一面。
我國民族樂器改革如何在既要考慮不失去它原有的民族特色,即它的本質音色和音樂表現力,又能借鑒一些西方的科學方法,使之更加完善、更具有時代性,是改革者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我國笙的改良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由牟善平、翁鎮發等研制的37簧圓斗笙,在形制、持笙方法、音位排列等方面等保持了傳統的基礎上將音域擴展的,而在加鍵方面,為不影響傳統技法的發揮,并防止過多的漏氣和指法運用上的不方便,只在中音區加鍵。在完整的三個八度中(g-g3),即解決了合奏中“缺音少調”的問題,又不影響傳統的演奏技法。這種改良笙因為其表現力強、便于攜帶、易學等優點,已經在教學中得到廣泛應用。
總之,笙——這一古老而優秀的我國傳統樂器,但愿它科學、合理地在實踐中不斷改良和完善,使之更趨于完美,更能適應我國民族音樂的需要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