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的繆斯女神
薛玉鳳
在新近出版的全本《馬克·吐溫自傳》(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Volume 1—3, 2010—2015)中,互文是一個明顯特征,引用、參考、暗示、模仿、重寫等多種互文性手法,都被吐溫運用得出神入化。其中一個重要的互文作品,是他早逝的大女兒蘇西(Susy Clemens, 1872—1896)13歲時為他所作的傳記,即“蘇西的傳記”(Susy s Biography)。在《馬克·吐溫自傳》的前兩卷中,吐溫在27天的口述自傳中共57次引用“蘇西的傳記”,最短的只有一句話,最長的達1000多詞,總共長達14704詞,幾乎是蘇西作品的全部內容。那么吐溫為何在自傳中大篇幅地使用這種被評論家認為“毫無益處”的“剪貼法”呢?除懷念早逝的女兒外,“蘇西的傳記”其實是吐溫的靈感源泉。它就像引子,源源不斷地引出吐溫對早逝女兒的痛苦回憶,對過去美好時光的留戀,對家庭逸聞趣事的回顧,以及對自身經歷的補充與說明等。吐溫的自傳在與“蘇西的傳記”的對話與交流中“不斷地刪減、增加、變形、改寫自身,從而生成新的意義、新的文本”,新文本對老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西是吐溫最重要的繆斯女神,無論她生前還是死后,都帶給父親無限的創作靈感。
“蘇西的傳記”作為引子,或線索,或靈感的作用,一開始就顯而易見,吐溫在引用女兒文本的基礎上,“增加”了許多內容。蘇西記載的一些事,使吐溫想起與之相關的更多來龍去脈,這是吐溫自傳對“蘇西的傳記”最常見的增加形式。“蘇西的傳記”第二段結尾兩句看似平淡無奇的話,卻勾起吐溫關于過去的許多美好往事,父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的那段幸福日子呼之欲出。蘇西說父親講的故事總能逗人開心,她和妹妹克拉拉常坐在父親椅子兩邊的扶手上,聽他講述墻上畫里的故事。這使吐溫回憶起當時自己如何絞盡腦汁、費盡心機給孩子們編故事,遠非蘇西描述得那么簡單輕松,因為小蘇西和妹妹要求十分苛刻,是“非常挑剔難纏的聽眾”,父女隔空對話的意味濃烈。作為作家與演說家,編講故事是吐溫的長項,也是培養女兒們文學素養的良機。潤物細無聲,蘇西的文學功底與父親的這種文學熏陶可謂密不可分。
吐溫自傳對“蘇西的傳記”的另一種“增加”方式,是補足蘇西所不知的事實真相。蘇西只知父親經常心不在焉,無法對付生活中的簡單事件,卻不知因為他的心不在焉,曾釀成大禍:導致他唯一的兒子蘭登生病死亡,并因此導致傷心欲絕的孩子母親也差點兒喪命。心不在焉,情緒變化無常,生活能力低下,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作家吐溫也逃不出這個魔咒。他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在現實世界中卻經常處于半睡眠、半意識狀態,疏于觀察,更不善于行動。吐溫補充的一個有趣事例,是他50歲時突發奇想,與朋友一起學一種9英尺高(約2.7米)的老式自行車。朋友很快掌握騎車藝術,而吐溫卻在自行車廠派來的一個認真嚴肅的德國小伙子一天兩次、連續三周的精心培訓下,仍無法馴服那個怪獸,只要稍微分心,就會從高高的自行車上狠狠地摔下來。教練最后不得不“恭維”吐溫,說他從未見過任何人像吐溫那樣,有那么多從自行車上摔下來的不同方式。這些事蘇西無從得知,卻都從一個側面,說明吐溫心不在焉、拙于行動的性格特質。
新文本對老文本的另一種 “增加”形式,是“蘇西的傳記”記載的有些事,讓吐溫浮想聯翩,想起自己親身經歷的另一件事,兩件事關聯不大。在“蘇西的傳記”開頭兩小段的引文中間,吐溫插入長長五段看似不相干的內容,痛斥評論家人云亦云,缺乏真知灼見,對他惡意中傷,多年來竟無人為他平反昭雪。吐溫甚至認為“文學、音樂和戲劇評論,是所有行業中最丟臉的一項工作,毫無真正的價值可言——至少沒有太大價值”。他接著引用“蘇西的傳記”第二段:“很多人形容過爸爸的外表,但都相當荒謬”,接著她不帶偏見、不偏不倚地描述父親,而不像那些評論家一樣鸚鵡學舌。吐溫的用意因此一目了然,一方面指責批評家缺乏新意,一方面“強調”“蘇西的傳記”的真實性與史料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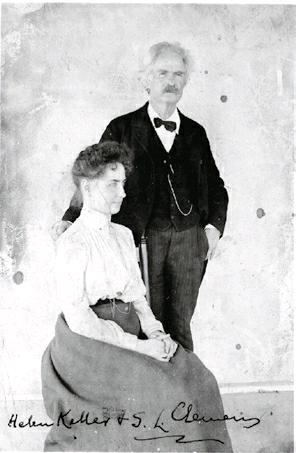
“天呢,我不禁浮想聯翩,塵封許久的記憶從墳墓中跳了出來,變得鮮活生動!”這是吐溫在1906年3月7日的口述開始對“蘇西的傳記”的回應,老文本對新文本的啟發作用顯而易見。在短短三四行的引文中,蘇西提到自己與母親為妹妹克拉拉買了幾本德語書作為生日禮物,這句話勾起吐溫很久以前見到《紐約論壇報》編輯約翰·海的故事,兩個故事之間唯一的共同點是外語書。吐溫用近一頁篇幅,講了約翰·海無意中借給一對母女一本黃色法國小說的故事,故事以約翰·海的勸告告終:“聽我一句勸,自己沒看過的書千萬別借出去”,令人啼笑皆非。吐溫最敏感的是語言與書籍,這件事之所以給他留下深刻印象,說明他對自己作家與演講家雙重文化身份的認同。
“蘇西的傳記”與吐溫自傳的另一種關聯形式,是吐溫糾正“蘇西的傳記”記載的不正確內容,擴展與之相關的故事信息,可謂對蘇西寫作的刪減、變形、深化與改寫。“蘇西的傳記”中的半頁報警器故事,引發吐溫講述另一件三四頁長的報警器故事,是吐溫對女兒文本的有意深化與改寫,淋漓盡致地揭示傳主別具一格的性格特質。蘇西講述父親所做的報警器實驗,證明有著作家大腦的父親,如何理解不了一些最簡單的日常事務。在這段引文后,吐溫詳細論證女兒老早就發現的這些弱點,如何困擾他一輩子。吐溫討厭復雜事物,像報警器這樣連孩童都理解的東西,卻是他無論如何都理解不了的大難題,而這困惑很快會變為憤怒,成為他控制不了的壞脾氣。蘇西故事中的吐溫無論如何也搞不清報警器到底怎樣才算正常,而吐溫講述的是昂貴的報警器唯一真正發揮作用的故事。而那真正的作用,卻絕非一般人所理解的趕跑竊賊,而是驗證吐溫對竊賊的推斷完全正確。這些歪理讓吐溫的妻子莉薇無可奈何,也讓讀者一次次忍俊不禁,笑破肚皮,大概也就是吐溫這樣的大幽默作家,才會想出這么些與眾不同的邏輯。“蘇西的傳記”與吐溫自傳相互映襯,相互補充,同時塑造了一個個性獨特、不食人間煙火的吐溫形象。
誠實的小傳記作家蘇西毫不留情地揭露父親的缺點,吐溫自己更是如此。蘇西在傳記一開始就提到父親脾氣不好,說話難聽,粗話不斷,吐溫于是對自己動輒發怒的壞脾氣用形象的實例做了更多補充說明。刮胡子時的咆哮、吼叫、咒罵,連向窗外扔三件襯衣的滑稽場面,吐溫以為只有自己知道,最后卻發現房門沒關好,自己的壞脾氣被妻子抓個正著,而這是吐溫最不愿看到的。結婚十年來,他一直以為自己的壞脾氣掩飾得很好,不想這次前功盡棄。于是他像做錯事的孩子,沮喪、膽怯、焦慮,一切都展現得惟妙惟肖。酗酒、抽煙、罵人,吐溫的一些壞習慣讓妻子為他操碎了心。
蘇西寫作時只是個孩子,很多聽來的故事難免會有誤差,糾錯也就成了吐溫自傳的部分內容。吐溫與妻子第二次見面是在第一次見面后的第五天,而不是蘇西說的第二年8月;給孩子們帶來無窮樂趣的小鴨子是吐溫買來的,而不是上帝送給她們的;《有片幸福的土地》是吐溫從黑人說唱秀買來逗大家開心的,而不是他自己創作的,等等,閱讀與引用蘇西的傳記,吐溫面前仿佛過電影一般,往事歷歷在目。在1906年情人節那天的口述自傳中,吐溫再次糾正“蘇西的傳記”給人的錯誤印象,詳述自己并不輕松的婚戀經歷。這天開頭的引文只有一句話:“不久爸爸回到東部,爸爸和媽媽結婚了。”緊接著是吐溫對女兒的回應:“聽起來輕松順利,毫無障礙,可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實際的情形遠沒有這么一帆風順。”蘇西對父母婚戀故事的了解,大多從母親莉薇片言只語的介紹中獲得,不可能很完整,而求婚的艱辛歷程,只有吐溫自己心知肚明。在接下來的三四頁自傳中,吐溫回顧那段甜蜜又揪心的歲月:經過三四次求婚的失敗,吐溫心灰意冷,后因一次意外的馬車事故贏得莉薇的芳心,卻又因擔保人對他的差評,差點過不了老岳父那關。好在婚后幾十年的幸福生活,是對吐溫當時艱苦卓絕的求婚努力的最好回報。莉薇不只是吐溫心心相印的愛人,也是他的編輯、校對,甚至他的監護人,處理他無法對付的所有生活瑣事與麻煩,典型的賢妻良母與賢內助。失去莉薇,晚年的吐溫仿佛失去了左膀右臂,痛徹心扉。
“蘇西的傳記”也像記事本一樣,記錄吐溫那段生活的點點滴滴,比如友人寫給吐溫50歲的慶生詩與賀辭,若不是蘇西的記載,也許早已遺失。白發蒼蒼的老父親吐溫21年后看到女兒記載的這些珍貴的陳年往事,感慨萬千,老淚縱橫。他不由得與早逝的愛女隔空對話,或同意女兒的觀點,或糾正謬誤,或補充不足,或借題發揮,滿滿的都是對愛女的思念與不舍。作為忠實的歷史記錄者,蘇西對父親的缺點直言不諱,有時甚至用詞尖刻,會時不時刺痛吐溫的自尊心,但他多么希望女兒把他的缺點都記下來,因為它們都成了吐溫晚年的至寶。他感嘆道:“哦,蘇西,你這個可愛的小傳記家,你的溫柔、仁慈與寬厚使你的老父親為之心碎!”白發人祭奠黑發人的場景令人唏噓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