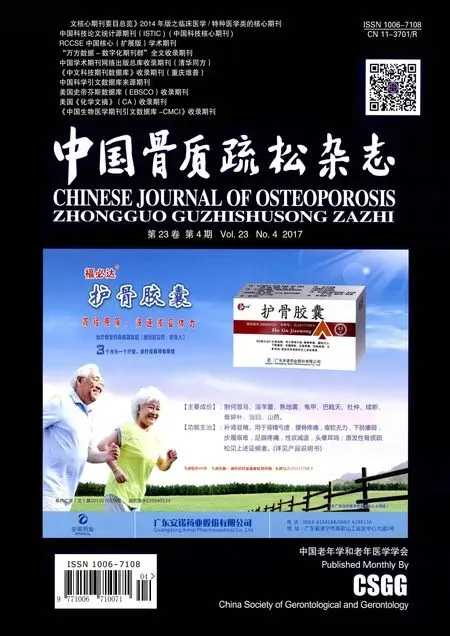唑來膦酸對女性骨質(zhì)疏松癥的療效及其對骨標(biāo)志物的影響
孔瑞娜 高潔 張菊 吉連梅 徐美娟 徐霞 張?zhí)m玲 趙東寶
第二軍醫(yī)大學(xué)附屬長海醫(yī)院風(fēng)濕免疫科,上海 200433
骨質(zhì)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一種以骨量下降,骨微結(jié)構(gòu)損壞,導(dǎo)致骨脆性增加,易發(fā)生骨折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骨質(zhì)疏松癥分為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2大類。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癥主要包括絕經(jīng)后骨質(zhì)疏松癥(Ⅰ型)、老年骨質(zhì)疏松癥(Ⅱ型)。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癥指由任何影響骨代謝的疾病和(或)藥物導(dǎo)致的骨質(zhì)疏松。骨質(zhì)疏松的嚴(yán)重后果是發(fā)生骨質(zhì)疏松性骨折(脆性骨折),從而導(dǎo)致患者病殘率和死亡率增加。如發(fā)生髖部骨折后1年之內(nèi),死于各種并發(fā)癥者達20%,而存活者中約50%致殘。2003年至2006年一次全國性大規(guī)模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顯示50歲以上女性骨質(zhì)疏松癥總患病率為20.7%。北京等地區(qū)50歲以上婦女脊椎骨折的患病率為15%,髖部骨折率為229/10萬。女性一生發(fā)生骨質(zhì)疏松性骨折的危險性(40%)高于乳腺癌、子宮內(nèi)膜癌和卵巢癌的總和。因此骨質(zhì)疏松的預(yù)防和治療顯得尤為重要。
唑來膦酸(zoledronic acid)作為第三代雙膦酸鹽類抗骨質(zhì)疏松藥物,已被廣泛用于治療不同類型的骨質(zhì)疏松癥,而有關(guān)其對不同類型骨質(zhì)疏松臨床療效方面的比較,報道較少。本研究通過觀察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女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應(yīng)用唑來膦酸治療后骨密度和骨代謝標(biāo)志物的變化,評價該藥物對不同病因的女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的臨床療效和骨代謝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2年4月至2016年7月在長海醫(yī)院風(fēng)濕免疫科行唑來膦酸治療的有完整隨訪資料的女性O(shè)P患者119例,根據(jù)病情分成A、B兩組,A組(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66例,年齡52~87歲,平均69.8±9.6歲;其中陳舊性骨折患者22例。B組(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53例,年齡51~82歲,平均66.1±8.4歲;其中陳性舊骨折患者19例,同時伴發(fā)類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9例、風(fēng)濕性多肌痛6例、干燥綜合征6例、強直性脊柱炎4例、糖皮質(zhì)激素性骨質(zhì)疏松癥5例、乳腺癌術(shù)后7例、子宮切除術(shù)后8例、甲狀腺功能減退癥5例、炎癥性腸病3例。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發(fā)病年齡高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P<0.05),兩組患者在陳舊性骨折史、血鈣、血磷、BUN、Cr、腰椎和髖部骨密度值、骨代謝指標(biāo)等方面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予告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病例納入標(biāo)準(zhǔn):參照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推薦的骨質(zhì)疏松診斷標(biāo)準(zhǔn),雙能X線骨密度儀(DXA)檢測骨密度T值≤-2.5及/或發(fā)生脆性骨折的女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病例排除標(biāo)準(zhǔn):嚴(yán)重的血液系統(tǒng)疾病、骨髓增生性疾病(如多發(fā)性骨髓瘤)和惡性腫瘤轉(zhuǎn)移者;嚴(yán)重腎功能不全患者(肌酐清除率<35 mL/min);低鈣血癥未糾正患者。
1.2 研究方法
材料:唑來膦酸注射液(密固達,北京諾華制藥有限公司, 規(guī)格5 mg/100 mL);碳酸鈣 D3片(鈣爾奇D,美國惠氏制藥有限公司,規(guī)格為元素鈣600 mg+維生素D 125IU/片);骨化三醇膠丸(羅蓋全,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規(guī)格0.25 μg/丸); 雙能 X線骨密度儀(DXA)(Lunar Prodigy Advance,GE公司,美國);骨代謝標(biāo)志物試劑盒為德國羅氏診斷公司提供。
治療方法: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的治療方案相同, 在聯(lián)合骨化三醇0.25 μg/日和碳酸鈣 D31片/日連續(xù)治療1年的基礎(chǔ)上,均給予唑來膦酸5 mg靜脈滴注,時間大于30 min,1次/年,唑來膦酸使用前給予生理鹽水500 mL靜滴,以及地塞米松2.5 mg靜推預(yù)防抗過敏;使用后給予生理鹽水100 mL靜滴,洛索洛芬鈉60 mg 3/日 口服治療1天;用藥前及用藥后囑患者多飲水以促進藥物排泄、減少腎臟毒性的發(fā)生。12個月后進行相關(guān)指標(biāo)的測定并進行比較。
1.3 觀察及評價指標(biāo)
1.3.1骨密度測定:采用雙能X線骨密度儀測定治療前和治療1年后兩組患者腰椎L1-4和左髖部(股骨頸、大粗隆、股骨干)的骨密度值。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只有35例患者進行了髖部骨密度檢測。
1.3.2骨代謝標(biāo)志物水平的檢測:采用德國羅氏診斷公司提供的骨代謝檢測試劑盒,應(yīng)用電化學(xué)發(fā)光免疫分析技術(shù)檢測兩組患者治療前和治療1年后的血清骨代謝指標(biāo)總I型膠原氨基端延長肽(P1NP)、甲狀旁腺素(PTH)、25羥基維生素D、β-膠原降解產(chǎn)物測定(β-CTX)、骨鈣素N端中分子片段(N-MID)的水平,以肝素抗凝真空采血管取患者空腹外周靜脈血5 mL,所有血樣標(biāo)本送我院檢驗科進行檢測分析。
1.3.3血鈣、血磷、尿素氮(BUN)、肌酐(Cr)測定:分別于治療前和治療1年后檢測,所有血樣標(biāo)本送我院檢驗科進行檢測分析。
1.3.4觀察患者不良反應(yīng):主要包括發(fā)熱、骨關(guān)節(jié)疼痛、肌肉軟組織疼痛等流感樣癥狀,惡心、嘔吐、乏力及心律失常等癥狀。
1.3.5觀察新發(fā)骨折情況:于治療前和治療后1年行胸腰椎正側(cè)位X線檢查,判斷有無新椎體骨折。
1.4 統(tǒng)計學(xué)處理
2 結(jié)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骨密度值比較
與治療前比較,治療1年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腰椎和髖部骨密度值均明顯增加(P<0.05或0.01),見表1;治療1年后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腰椎(L2、L3、L4、L1-4)、髖部大粗隆和全髖骨密度值均明顯增加(P<0.05或0.01),腰椎L1、股骨頸和股骨干骨密度值無明顯變化(P>0.05),見表2。治療1年后兩組間腰椎和髖部骨密度值均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3。

表1 A組患者治療前、后骨密度值的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group

表2 B組患者治療前、后骨密度值的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group
2.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骨代謝標(biāo)志物水平的比較
與治療前比較,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治療1年后P1NP、β-CTX、N-MID水平均明顯下降(P<0.01),25羥基維生素D水平明顯升高(P<0.01),PTH水平無明顯變化(P>0.05),見表4。與治療前比較,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治療1年后P1NP、β-CTX、N-MID 水平均明顯下降(P<0.01),25羥基維生素D、PTH水平無明顯變化(P>0.05),見表5。治療1年后,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N-MID水平明顯低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P<0.01),兩組之間P1NP、β-CTX、25羥基維生素D、PTH水平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6。

表3 A、B兩組患者治療1年后骨密度值的比較Table 3 Comparison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fter 1-yea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表4 A組治療前、后骨代謝標(biāo)志物水平的比較Table 4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of bone metabolism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group

表5 B組治療前、后骨代謝水平的比較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indicator of bone metalism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in group

表6 A、B兩組患者治療1年后骨代謝標(biāo)志物水平的比較Table 6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of bone metabolism after 1-yea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2.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鈣、血磷、BUN、Cr水平比較
與治療前比較,兩組患者治療1年后血鈣、血磷、BUN、Cr水平均無明顯變化(P>0.05)。治療1年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患者血磷水平明顯高于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P<0.05),兩組之間血鈣、BUN、Cr水平無明顯差異(P>0.05)。
2.4 兩組患者輸注唑來磷酸后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情況
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2例發(fā)熱(3%),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3例發(fā)熱(5.7%);兩組間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無統(tǒng)計學(xué)差異(P>0.05)。以上不良反應(yīng)均在藥物使用后3d內(nèi)出現(xiàn),癥狀出現(xiàn)2~3 d后消失,未見不適癥狀反復(fù)出現(xiàn)的患者。治療期間所有患者未出現(xiàn)下頜骨壞死、腎衰竭、惡性心律失常、休克等嚴(yán)重并發(fā)癥。
2.5 兩組新發(fā)骨折情況研究期間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均無新發(fā)骨折。
3 討論
無論是原發(fā)性還是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均表現(xiàn)為骨量減少,骨密度下降,易發(fā)生骨折。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中,絕經(jīng)后OP的發(fā)生機制主要是以絕經(jīng)后婦女的雌激素分泌明顯減少而引起的骨吸收大于骨形成的高轉(zhuǎn)換型的OP;老年性O(shè)P又稱退行性O(shè)P,它是生理衰老在骨骼方面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一般認(rèn)為老年性O(shè)P發(fā)生的細胞學(xué)基礎(chǔ)是由于破骨細胞的吸收增加及成骨細胞功能的衰減,為低轉(zhuǎn)換型的OP[2-3]。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發(fā)病機制主要是通過產(chǎn)生大量炎性細胞因子抑制成骨細胞活性,增強破骨細胞功能而參與骨質(zhì)重建,最終導(dǎo)致骨吸收大于骨形成,而使骨量丟失[4]。
所以不論是原發(fā)性還是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針對破骨細胞活性增強這一骨質(zhì)疏松發(fā)生的關(guān)鍵機制,雙膦酸鹽類無疑是目前循證醫(yī)學(xué)研究最全面、臨床應(yīng)用最廣泛的抗骨重吸收類藥物[5-6]。其中唑來膦酸是經(jīng)靜脈應(yīng)用的第3代雙磷酸鹽,研究顯示其防治骨質(zhì)疏松療效顯著。
對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國外多項研究均表明唑來膦酸能顯著提高絕經(jīng)后女性腰椎和髖部骨密度[7]。一項超過7700名患者參加的唑來膦酸治療絕經(jīng)后骨質(zhì)疏松及其骨折研究表明,5 mg唑來膦酸每年1次連續(xù)治療3年后,與安慰劑比較,能降低70%腰椎骨折和40%髖部骨折,特別是首次髖部骨折后應(yīng)用唑來膦酸可以降低再發(fā)骨折風(fēng)險和死亡率[8]。本研究顯示唑來膦酸治療1年能顯著提高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女性患者腰椎及髖部的骨量,降低新發(fā)骨折風(fēng)險,這與國外相關(guān)研究結(jié)論一致。雙膦酸鹽對不同原因所致的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治療也有較多報道[9]。但關(guān)于唑來膦酸治療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療效比較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報道。本研究是原創(chuàng)性工作,結(jié)合骨密度和骨標(biāo)志物評價指標(biāo),比較了唑來膦酸治療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的臨床療效差別,為進一步深入研究二者的治療作用機制提供臨床依據(jù)。本研究結(jié)果表明,對于繼發(fā)于類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風(fēng)濕性多肌痛、干燥綜合征、強直性脊柱炎、乳腺癌術(shù)后、子宮切除術(shù)后、炎癥性腸病等疾病,及長期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的女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經(jīng)唑來膦酸5 mg治療1年后,腰椎和髖部平均骨密度也顯著提高,與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比較無明顯差異。所以,唑來膦酸對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女性患者具有同樣的抗骨質(zhì)疏松效果。進一步分析兩組各部位骨密度變化,我們發(fā)現(xiàn)對于繼發(fā)性女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相比髖部骨密度,唑來膦酸更能明顯改善其腰椎骨密度。提示我們應(yīng)用唑來膦酸抗骨質(zhì)疏松對于降低腰椎骨折風(fēng)險的作用更為確定。
BMD是診斷原發(fā)性O(shè)P的“金標(biāo)準(zhǔn)”[10]。但骨密度在治療后短期內(nèi)難以得到改善,而骨代謝標(biāo)志物常能在短期內(nèi)反映治療效果。所以骨轉(zhuǎn)換指標(biāo)被認(rèn)為是應(yīng)用抑制骨吸收藥物雙膦酸鹽治療OP患者最佳的短期監(jiān)測標(biāo)志物。骨代謝標(biāo)志物中,β-CTX作為I型膠原蛋白的羧基端降解產(chǎn)物,在破骨細胞吸收骨基質(zhì)的過程中釋放入血循環(huán),是較好的反映骨吸收活躍程度的檢測指標(biāo);P1NP是骨形成標(biāo)志物,反映了新合成的I型膠原蛋白的變化;N-MID是骨基質(zhì)中含量最豐富的一種特異性非膠原蛋白,由成骨細胞合成分泌,反應(yīng)成骨細胞活性。有研究證實,應(yīng)用抑制骨吸收藥物6個月即能明顯影響骨轉(zhuǎn)換指標(biāo),β-CTX、P1NP、N-MID會顯著下降[11-14]。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不同原因所致的女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應(yīng)用唑來膦酸抗骨質(zhì)疏松治療后骨代謝標(biāo)志物的變化情況。顯示唑來膦酸治療1年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P1NP、β-CTX、N-MID水平均明顯下降;治療后繼發(fā)性性骨質(zhì)疏松組N-MID水平低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P1NP、β-CTX水平無明顯差異。β-CTX水平下降提示唑來膦酸作為骨吸收抑制劑,在治療后較長時間內(nèi),藥物作用穩(wěn)定,能夠有效抑制破骨細胞的活性,減少骨吸收,降低骨轉(zhuǎn)化。P1NP、N-MID水平較治療前降低,提示唑來膦酸除抑制破骨細胞、降低骨吸收標(biāo)志物水平外,可同時抑制成骨細胞活性,即全面抑制骨代謝指標(biāo)。唑來膦酸抑制骨吸收作用在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之間無明顯差異,而在抑制骨形成指標(biāo)方面對兩組患者的影響程度可能存在差異。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治療前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和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N-MID水平無差異,接受治療后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N-MID水平明顯低于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這可能與不同原因骨質(zhì)疏松發(fā)病機制中成骨細胞活性不同有關(guān)。
本研究應(yīng)用唑來膦酸治療1年后顯示,原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25羥基維生素D水平較治療前明顯升高,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組25羥基維生素D水平較治療前無明顯差異,治療后兩組比較無明顯差異。而兩組無論是治療前后比較或治療后兩組間比較,PTH水平均無明顯變化。25羥基維生素D水平變化考慮可能與維生素D在原發(fā)性O(shè)P發(fā)病機制中起更重要的作用有關(guān)[15-16],維生素D缺乏在原發(fā)性O(shè)P中表現(xiàn)更明顯。而PTH信號通路主要與鈣吸收相關(guān),只是間接參與了骨質(zhì)疏松發(fā)病[17]。本研究在治療前無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甲旁亢情況,在唑來膦酸治療過程中兩組都加強了補充鈣劑和活性維生素D3,所以治療后兩組的25羥基維生素D和PTH水平無明顯變化。
本研究患者總體耐受性良好,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明顯低于國內(nèi)外報道[18-19],未出現(xiàn)嚴(yán)重并發(fā)癥,表明唑來膦酸作為抗骨質(zhì)疏松藥物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而且與本研究加強用藥前的預(yù)防措施、強調(diào)水化、預(yù)防抗過敏藥物應(yīng)用有關(guān)。隨訪一年未發(fā)現(xiàn)新發(fā)骨折,也提示唑來膦酸降低骨折風(fēng)險療效顯著。
總之,5 mg唑來膦酸治療不同原因所致的女性骨質(zhì)疏松,能夠顯著增加腰椎及髖部骨密度,降低骨代謝標(biāo)志物的水平,顯著降低骨折風(fēng)險,且總體耐受性較好。相對于其它雙膦酸鹽的給藥形式,唑來膦酸每年1次靜脈注射給藥方式和無上消化道副作用等優(yōu)勢,特別是對于伴有多種疾病且服藥種類較多的繼發(fā)性骨質(zhì)疏松患者,更容易被接受,依從性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