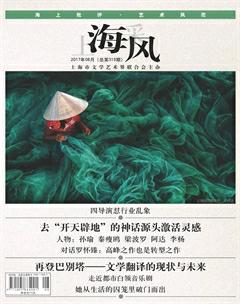做自己認為值得的事
王萌萌
當然,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一襲黑衣、兩鬢微斑的李楊導演,說這句話時有那么一瞬斂了臉上的微笑,雙眸射出略有些凌厲的精光,隨即又恢復笑容補充道,我認為自己是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受邀參加第二十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他住在毗鄰淮海路的花園飯店,對鬧中取靜的寬敞花園和原法國俱樂部改建的巴洛克風格的裙樓很滿意。適逢悶熱潮濕的梅雨季,但他并不抱怨連續降雨使出行不便,稍有閑暇便想去看老房子。
采訪的前一晚,筆者有幸與李楊共進晚餐,席上有重量級劇作家沙葉新,陪伴在側的李楊自始至終恭敬有禮、照顧入微,并且顧及到席間每個人的感受,言行處處分寸得當令人舒服。若非如此接觸,誰能想到這位國內影壇上頗為“另類”的導演,行事待人卻如此隨和低調。
為圓“導演夢”退學出國
生于1959年的李楊,父母都是陜西省話劇院的演員。看著大人們排戲,孩子自然會模仿,與小伙伴游戲的內容之一就是學著大人們的樣子過家家般演戲。耳濡目染,他早早就立下做演員的志向。
文革期間,父親因年輕時曾加入國民黨而遭受批斗、被迫害致死。母親雖然因為曾經參加抗戰而幸免于難,卻也因為不愿與父親離婚而被降職降薪,家中生活一落千丈,身為長子的李楊13歲就承擔起家庭責任,想辦法去掙錢并照顧兩個弟弟。眼看著身邊的人互相檢舉、揭發、批斗,最熟悉甚至最親近的人彼此背棄、施暴……令他年輕的心早早就看見人性的無常與丑陋,并因此產生了長久的思索。1977年恢復高考,對人與人之間的斗爭深懷厭惡的他為了遠離人群,報考了自己并不擅長的地質學專業,卻因11分之差而落榜。1978年,他同時考上了陜西省話劇院和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在稱國家話劇院)。不愿回傷心地面對關于父親的慘痛回憶的他,選擇了去北京學習和發展。
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幾年,起初各個領域包括文化藝術界都百廢待興,并沒有太多好戲可演。后來為了增加表演經驗,也為了生存,他也和不少話劇演員一樣去外面接一些影視表演的活。但在此過程中他開始對導演的工作產生興趣,并且受了第五代導演早期代表作諸如《一個與八個》《黃土地》等影片和一些外國經典電影的影響,逐漸將目標轉移到做導演上。
1985年,26歲的李楊考入北京廣播學院導演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兩年之后,他居然退學了。在那個年代,大學生屬于國家干部編制,罕有人會中途退學,他的舉動在當時著實屬驚人之舉。如今談起緣由,他說當年的女朋友要去德國留學,而他又想走出國門,去電影和藝術發展比較先進的地方學習體驗。那時國家規定,大學畢業生五年內不能出國,想到畢業后再等五年,自己已經三十多歲,為了不虛耗時光,也為了愛情,他做了去德國留學的決定。
帶著湊來的400美金來到德國,李楊最先進入德國西柏林自由大學學習藝術史,之后又轉入慕尼黑大學,修戲劇文學專業。最終1995年在科隆影視傳媒藝術學院電影導演系,獲視聽傳媒學碩士學位。對于自己8年期間三次轉變專業方向,李楊笑稱自己“不安分”。但得益于德國高度人性化和相對自由的教育制度,學生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和情況轉換就讀的專業和學校,大學之間彼此承認過去的學分,他因此能最終比較理想地完成導演專業的學習。
在德國留學期間,李楊為了生活和學費打過各種工,起初是餐廳跑堂、商場銷售之類,語言過關之后就開始做演員,還曾經在對華廣播的電臺做過播音員。通過從事這些工作,使他對德國社會的各個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德國人紀律性強、嚴謹務實、理性重邏輯等特質也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他感覺到自己從前的認知崩塌又重建,看問題和思考的方式都改變了。
親身見證柏林墻倒塌,親眼看見長期處于物資匱乏中的東柏林人在柏林墻開放后因吃得太猛而噎住、一邊干嘔一邊流淚的情景,使得他心中對人性、對生命生出更多悲憫和反思。
處女作《盲井》獲獎無數,讓王寶強脫穎而出
在德國考電影學院期間,李楊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云南瀘沽湖的報道,他意識到那里有適合拍成紀錄片的素材,便自費前往拍攝。完成了記錄摩梭族走婚制的《婦女王國》之后,他又拍攝了記錄哈尼族喜慶葬禮的《歡樂的絕唱》。憶起當時情景,他感慨說那次拍攝過程中,哈尼族“向死而生”的生死觀對他觸動很大。這兩部拍攝于當時云南最偏遠地區、少數民族風情濃郁、又引人深思的紀錄片都出售給了德國電視臺。此后他又為紀念抗戰50周年創作了紀錄片《痕》。
然而僅僅拍攝紀錄片并不能令李楊滿足,他的“導演夢”是拍攝自己的故事片,證明自己有做導演的能力。
在德國完成學業之后,他迫切地想要將所學得以施展,可當時國內電影業不景氣,街頭到處充斥著播放港臺片甚至色情片的錄像廳。電影拍攝都是由各大電影廠進行,個人連拍攝許可證都難以申請。他每年回國來考察,又總是失望,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國內也有所謂“地下電影”,在部分小眾影迷之中頗受歡迎。于是他決定自己攢錢拍一部真心想做的電影,先不考慮之后的放映發行問題。
為了積攢拍片的成本,李楊在德國花三年時間用各種方法賺錢。2000年,他先幫黃建新導演做了一回副導演,以此熟悉了國內拍攝影片的流程。2001年他正式搬回國內,深感國內的變化遠超他的想象,一邊調整適應,一邊尋找合適的拍攝題材。
劉慶邦的短篇小說《神木》觸發了他的創作興趣。小說原著講述的是兩個生活在礦區的閑人,靠騙人去礦上謀害發礦難財的故事。故事的人物簡單、場景和矛盾沖突集中,而反應與表達的內容卻令人極度震撼,他意識到這能改編并拍攝成一個絕佳的小成本電影。于是他先向劉慶邦買下了小說的電影版權,并試著自己寫劇本。然而他發覺由于自己對社會底層和礦工生活不了解,導致在創作過程中最鮮活、最有質感和沖擊力的部分不斷喪失。他又請劉慶邦幫忙安排,前往礦區下生活。他從北京火車站出發,坐慢車,從河北到內蒙古再到寧夏,回到陜西,之后又轉道河南,每到一站就下車去小煤窯探訪。最后,總算寫出了理想的劇本,其中每一個戲劇化的故事,都是由真實的案例在背后支撐。
說起這部處女作《盲井》,筆者還記得第一次看是大學期間在宿舍里放的盜版DVD。彼時同宿舍的室友也都在看片或者看劇,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感動得流淚,而筆者則自始至終沉默著,時刻感覺眼睛被刺痛著、心被拉扯著,看完之后心情沉重久久無法釋懷。那時只覺得,故事片竟然還能這么拍,鏡頭絲毫不修飾、不回避,直擊最骯臟、最混亂、最丑陋之處,似乎隔著屏幕都能聞見空氣中彌漫的煤粉味,那么粗糲又那么有力量,淳樸天真的男孩與窮兇極惡卻又偽裝成好人的騙子之間的對比與互動,以及影片最后男孩離開時不再懵懂和清透的眼神,叫人難受至極卻又無法言說。
而李楊說,藝術創作一定要找到與內容最適合的表現方式,因此這部電影他選擇用“偽紀錄片”的手法拍攝。由于成本的限制和拍攝手法的需要,劇組需要駐扎在一個條件艱苦又危險的小煤礦里。有一回,劇組在井下連續工作了二十個小時,上來兩個小時之后煤洞就塌方了。拍攝至中途,劇組發生變故,制片主任攜款潛逃并且煽動了部分演職人員退出。李楊身兼數職,帶領留下的人在艱難的境況中完成了影片的拍攝。
值得一提的是,《盲井》是王寶強首部作為主演的電影,此前他只是一名在北影廠門口等待做群眾演員的北漂少年。最初在選演員時,副導演曾經帶來不少接受過表演訓練的城市孩子給李楊看,李楊覺得這些孩子既沒有農村孩子的淳樸,又因為刻意訓練,而有了表演的“模式”。他請副導演找回一百多個來自農村的孩子,不給他們試鏡,而是與他們聊天,觀察他們最自然的狀態,最后選中了形象最接近角色需求、又因做過群眾演員對鏡頭沒有陌生感的王寶強。他說我從來不教王寶強表演,因為不需要他表演,他只要理解了角色和劇情,做最真實的自己就可以。當拍攝遭遇困境、團隊人心惶惶之時,李楊曾經對王寶強說,我不能保證你堅持下去一定能得到什么,但作為演員這是你的責任。王寶強堅持到了最后,他在片中毫無表演痕跡的本色出演,讓元鳳鳴這個角色活靈活現深入人心,這是他的電影處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盲井》獲得了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第5屆法國杜維爾亞洲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最佳影評人、最受觀眾歡迎等五項大獎;第2屆美國紐約崔貝卡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2003年荷蘭海岸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和文學大獎等三十余個國際獎項。在法國《電影》雜志評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困境中的堅守與不得已的妥協
“盲和瞎不一樣,瞎是生理上的疾病,而盲是一種視而不見,一種道德上的失明。”李楊曾經這樣解釋他的“盲”系列作品。他的鏡頭始終對焦在社會底層,法律意識的嚴重缺失、人如草芥的生存狀態、赤裸裸的毫無道德底線的金錢交易等,都是他關注和表現的重點。
李楊拍攝的第二部電影《盲山》,講述的是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到關中農村,兩年里受盡虐待不斷掙扎逃跑最終被公安機關解救的故事。與此前的《盲井》不同,《盲山》沒有文學作品作為改編基礎,劇本要靠李楊獨立完成。2006年年初,他專程到成都金堂、中江,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采訪被解救的被拐婦女的生存狀態。對每個被拐婦女來說,回憶那段噩夢般的經歷都很痛苦,就像把結痂的傷口重新撕開一樣。可李楊為了創作,不得不進行這種殘忍的采訪,甚至還需要誘發對方講出具體細節,因為不了解細節就無法創作劇本,那段時間他內心充滿負罪感。向來頭沾了枕頭就能睡著的他,每晚都需要泡澡放松甚至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他比喻自己就像一個戰地記者,拿著相機看著拍攝對象被敵人打傷、打殘,但從職業角度他不能去救人,而是要拍攝。有可能他放下機器時拍攝對象已經死了,但這本身就是兩難的境況。而經過這些采訪,他也堅定了要完成這部電影的信念,覺得自己身上有了一種責任,不論承受多少委屈和艱難,都要把這些故事講述給世人看。
將拍攝地選擇家鄉關中鄉下,一是為了語言溝通方便,也因為當地原本就有買女人的現象。除了女主角和幾位主要的配角之外,男主角和絕大多數演員都是當地的農民。影片中有個角色叫鄭小蘭,在女主角白雪梅寧死不從的時候,她抱了孩子來勸慰,說你看我也是被賣到這里的,還不是這樣了。先把身體保住才是,不然怎么逃?這個演鄭小蘭的女人,現實生活中真是四五年前從四川一個縣城被騙嫁到那個村里的,才20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李楊是拍攝時才知道她的情況,見她天天來劇組看,就叫她演戲。她的丈夫不同意,打她。她就告訴丈夫說你再打我,我就跟劇組走。丈夫不敢再打,后來李楊叫她的丈夫也來串個角色,連她抱的孩子也給一份錢。在拍攝地的村子里,人們視買賣婦女為正常之事,配合拍攝絲毫沒有心理障礙,而專業演員全部向農民靠攏,使影片的鏡頭呈現出最符合真實的效果。
為了拍攝這部《盲山》,李楊抵押了房子,但他覺得為了拍好電影這么做是值得的,真正令他難受的是迫于現實壓力而妥協。《盲山》于2007年入圍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并奪得羅馬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可為了能在國內公映,讓國內觀眾看到這部影片。李楊不得不另外制作了國內公映版。國外版的結局是:白雪梅在大山里的“丈夫”黃德貴知道白父要帶她逃跑,跟白父起了爭執,為了救父親,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黃德貴,然后畫面黑屏。國內公映版的結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親走了,他覺得這個結尾不是不可以,但國外版的處理方式更符合他個人的想法。
“盲”系列的第三部,也就是收官之作《盲道》,于2016年完成,經過一年多的送審、修改之后,今年將會全國上映。這部由李楊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講述的是流浪街頭的留守兒童和落魄的街頭音樂家之間互相救贖的故事。為了創作劇本,李楊采訪了許多流浪的孩子,請他們吃飯,引導他們講自己流浪的經歷。此次拍攝期間依然困境重重,投資人中途撤資,使得李楊不得不“砸鍋賣鐵”,在拍攝后期,幾乎“彈盡糧絕”的時候,幸好得到了幾位主創和好友的鼎力相助才完成拍攝。然而一年多的反復審查和修改,使得不少他認為重要的鏡頭被剪掉,在他看來使得影片的表現力減弱很多,但他只好“表示理解”。整個采訪過程中,每當說起那些不得已的妥協,都是他臉上神情最為無奈和難受之時。
“劍客”本色
從2003年至今,十四年時間拍攝三部影片,李楊在當今國內影壇上或許看似有些低產,但是從影片的題材、質量和社會影響來看,他絕對稱得上是立意高、水準高、責任感與使命感高的導演。或許有人會不解,曾經在德國進行了十多年電影方面的學習,熟諳各種技巧、手段的導演,作品竟然如此寫實與樸素?然而精心地打磨一部作品、扎實地講好一個故事,已經成了如今國內電影導演稀缺的品質。當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大熱之際,李楊和他的作品或許能給業內人士帶來一些思考。
最討厭刻意拔高的李楊卻不愿意被人稱為什么“文藝片大師”,他說電影從來不分“文藝”和“商業”,只分“小眾”與“大眾”,而每部電影都具有商品的屬性。他說接下來他將會轉換方向,創作拍攝一些商業性強的電影,賺錢之后就又能去做自己最想拍的電影了。在過去十年之間,除了籌備和拍攝第三部影片《盲道》之外,他還做了不少編劇和影視后期的工作,例如參與《山楂樹之戀》《智取威虎山》的編劇,或許這些都是他為執導商業大片做的預熱,但他說自己對于底層和弱勢的關注永不改變。
前不久,李楊在微博上的一次轉發引起一場風波,遭到轉發文章中提到的某位當紅女星粉絲瘋狂的嘲諷和攻擊。他回應說,自己的轉發不針對任何演員進行批評和評論。演員的演技好壞自有公論,而中國影視界弄虛作假的現象只會傷害中國電影和電影人。談起這件事,他只覺得可笑和可悲。國內影視界目前膚淺、低俗、粗制濫造、唯利是圖的種種不良現象,才令他心痛和心憂。他想對有志于做導演的年輕人說,觀察生活、體驗生活,加強自身的修養、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然后堅守內心的追求,拍自己真正想拍的東西。
自嘲在日常生活很無趣的他,業余時間愛閱讀、逛博物館、聽音樂會,旅行一定要去遠離喧囂、接近自然的地方。他說自然的廣闊能讓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也能指引人抵達內心的平靜與美好。
“其實有時候,批評不是壞事,是為了能讓在乎的事物變得更好,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嘛。”采訪進入尾聲的時候,李楊語氣鄭重地這樣說,又補充道:“我是個有正義感的人,看見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就要說出來,就想去改變,這個恐怕一輩子都改不了。”
“所以你自稱劍客?”筆者問,他笑著點頭。
“對惡的無視和縱容就是幫兇?”筆者又問,他又點頭,但這次沒笑。
此前采訪的兩個多小時里,他多次說起過三個詞,分別是“常識”“真實”和“意義”。從1987年退學出國學電影到如今完成了“盲”系列三部曲,收獲了不少成績也經歷了太多坎坷磨礪的他,眼下追求的是更平和、更自在的心境。說起過往的悲欣得失,他語氣超然,有種“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意味。
最后他說:“我個人對物質要求很低,能吃飽穿暖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好,最重要的是為自己生活,做值得的事,這樣不一定能舒服,也許要受苦,但心里是安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