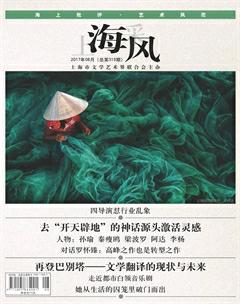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
陸壽鈞
謝晉的經典影片之一《舞臺姐妹》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經典臺詞——“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這部影片劇本的執筆者王林谷,是我們上影的一位老同志,1946年,他27歲時就進入地下黨領導的昆侖影業公司,任制片主任、藝委會秘書,參與了經典影片《烏鴉與麻雀》劇本的創作。建國后,歷任上海市電影局藝術處副處長、天馬電影制片廠副廠長、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學部主任、副廠長等職。我卻很少聽到人家叫他“主任”(廠長),大多數人都親熱地叫他“老王”,他也樂意大家叫他“老王”。
雖然我于1963年從上海電影專科學校畢業后,就被分配到天馬電影制片廠工作,但我與老王在“文革”前與“文革”中的十余年中從未有過接觸。“文革”前,我們不僅在兩個不同的部門工作,而且在輩分、資歷、職務上,都有很大差距,我根本沒有機會接近他,也從未想到要去接近他。“文革”中,他被打翻在地,一直關在“牛棚”,我也經歷了“烙餅”般的翻來覆去,更沒有機會和必要接觸。與老王相識是在“文革”后,他出任了上影文學部的副主任,我剛被正式調入文學部當編輯,由于多種原因,難被任何人善待,更難說看好,純屬“小三子”,日子很不好過。一次,老王要去四川開拓稿源,需帶兩個助手,一個選中了巴金先生的女婿祝鴻生,那是理所當然的,巴老是四川人,祝鴻生去會有好多關系可以便于開展工作。另一個,老王卻選了我,那是讓我至今都不能理解的。以后熟了,我也沒有問過他為什么。此行,讓上影在四川的組稿中打開了局面,以后幾年,祝鴻生和我,在四川為上影組成了不少好劇本,扶植成了不少中青年作者。我心中十分明白,這些成績的取得,不僅功在老王,而且他還有恩于我。在我做出成績后,他卻沒有在任何場合標榜過自己曾是我的“伯樂”。以后,老王升任文學部主任、文學副廠長,當上了局級干部(海燕、天馬兩廠合并成的上海電影制片廠屬局級事業單位),但在我的心目中,他還是原來的那個老王。有一次我去三角街老民居他的住處討論劇本,不巧撞見他正在痰盂上大解,彼此都很尷尬。此時我才知道,他家至此都還未有衛生設備,與當時的上海底層市民過著一樣的生活。
老王離休前,再次入川,帶我去重慶開拓稿源。在此行中我才知道,他出生在浙江寧波的一個貧困人家,11歲起就到上海工廠、商行當學徒、練習生。抗戰爆發后,他隨商行西遷重慶,開始業余創作,發表了不少鼓勵抗日斗志的散文和小說,加入了中國藝術劇社,開始從藝。他在重慶度過了八年,這段時間奠定了他的人生之路,是他一生所難忘的。我們在重慶組稿的間隙中,他帶我去看他當時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常會呆視良久。我們住在黨校的招待所里,傍晚散步時,他常會向我談些上影老人們的事,說到曾兩度主演過他所編劇本《烏鴉與麻雀》和《舞臺姐妹》的上官云珠的一生時,感嘆萬分。我提議他退下來后可為上官云珠寫部傳記,他卻愿意為我提供素材,讓我來寫。結果達成了一起合作、由我執筆的約定,于是就有了《上官云珠生死錄》這本書,也算我協助他完成了一個心愿。
他離休后,我常去看他。后來,我當了文學部的領導,仍常去看他,沒少吃過師母汪老師燒的可口的上海家常菜。在老王的心目中,我還仍然是以前的“大陸”。我們一起談人生、談創作,無話不說,我消除了他的一絲寂寞,也從他那兒得到了不少教益。我感到,老王的內心深處還是想自己搞劇本創作的,可他解放后一直從事的是創作上的行政工作,一直在為他人“作嫁衣”,除了《舞臺姐妹》外,只寫過《神龕記》《一條河的故事》《有一家旅館》《時代的聲音》等幾個劇本,我不知是否有始有終地都成了電影?1981年,他根據于伶的原著改編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七月流火》,總算拍成了電影。在一次我們文學部的聚餐會上,老王的老友謝晉,三杯酒一下肚,話開始多了起來。他指著老王說:你真可惜了!假如你不當官的話,完全可以再多寫幾個好劇本的……讓老王很尷尬,好像他就想當官似的。幸好老局長張駿祥出來說了句公正話:謝晉你胡說什么?!林谷同志做行政工作,是服從組織的安排!這工作總要有懂行的人去做的嘛!老王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一笑了之。但他心中明白:謝晉是在為他這個老友可惜,并無他意。老局長是感同身受,有感而發,他自己不也處在同樣的情況下?
老朋友還是老朋友,老王離休后,謝晉立即邀請他合作一部長篇電視連續劇劇本的創作,拍成電視劇后,卻至今都未能公映,可見,謝晉也不是萬能的。其間,我根據于本正廠長的指示,曾邀他寫過周璇的傳記電影劇本。這個劇本由他來寫是有不少優勢的,然而,他仍然十分認真,不但采訪了不少人,而且還在于廠長的幫助下,通過北京的電影資料館,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報刊上登載的有關周璇的文章全部復印了一份,足足有四百多篇。他寫出的《周璇悲歌》上下集電影劇本,是我所看到的有關周璇的作品中把周璇寫得最真實的一部。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沒能拍成。對此,老王顯得格外的平靜,他干了幾十年劇本工作,太理解其中的原委了。后來,當我得知老王得了癌癥后,曾想協助他整理成一集后爭取投拍。我想了三條理由去與領導陳說:一是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中國電影誕生九十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拍這樣一部三四十年代著名影星的傳記影片正合時宜;二是我們正在營建電影景點基地,好多戲可集中在我們的景點中拍攝,不會花太多的錢;三是也算為老王做一件好事。領導很支持我的想法,讓我去同老王商量。老王聽后欣然一笑,說自己的身體怕再也握不起筆來,他委托我全權處理。最后,他告訴我,據他所知,中央電視臺正在籌拍周璇的電視連續劇,根據影視的關系,拍了電視,就很難再拍電影了。我聽后百感交集,老王在工作上一直是十分認真的,上影出品的不少好影片的劇本,都滲透著他的心血。由于他手中有權,所以處世也特別認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而據我的觀察,他對自己更認真。就在他生命走向盡頭時,仍然對自己、對別人、對廠里是那樣的認真。我雖然安慰了他,顯得信心百倍,但最終還是應了老王的預料。以后見到老王或與他通話時,我真怕他問起此事,可他卻始終只字不提。我曾在謝晉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領導交給我的任務一是協助他組織劇本,二是宣傳謝晉,有可能為他寫個傳記。此時老王雖已離休,卻仍然全力支持我去做好此項工作。我們相約,有可能的話,一起為謝晉寫個傳記。老王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其中有件事特別讓我感動:“文革”開始時的一個星期天,謝晉約了老王一起躲在市郊七寶鎮的一家羊肉館里小酌,他告訴老王,據他得到的消息,次日他將被隔離審查了,他兩個弱智兒子自他被揪出后,在里弄里常被頑童們當作小牛鬼蛇神欺侮,甚至被塞進垃圾箱,以后可怎么辦呢?老王明白謝晉是在“托孤”。他忙答應謝晉,只要他仍有一份自由,他會盡力去協助照顧的。這天,謝晉找了一個公園,與兩個弱智兒子盡心地在草地上踢了一陣足球……謝晉生前,不愿意寫自傳,也不樂意別人去寫他的傳記。我也感到很難寫好他的傳記。所以,我與老王的這個約定也未能實現……
1995年春節前的一天,上午10時光景,我正整理行裝準備回老家去陪年邁的父母過春節時,突然接到老王的一個電話,話筒中傳來他顫顫抖抖的聲音:“我是老王,我知道你要回鄉下過節的,先向你拜個早年吧……”我一聽,來不及有任何思索,立即搶過話頭說道:“不,不,應該我向您拜年,我來,我馬上來看您!”放下話筒,丟下沒有整理好的行裝,我一下沖出了門外……
那天,我來到了老王家,見他正依在床頭看電視。人已骨瘦如柴,說話也十分吃力,卻還為他夫人給我泡茶慢了而發火。師母告訴我,他不能進食,脾氣越來越倔。我鼻子一酸,我知道老王是為了無力對我這個老下級熱情而發急。師母又向我“告狀”:老王聽說廠里經濟困難,不肯進大醫院,不肯用貴重的藥……我忍著淚水。老王又發火了:“你胡說什么?我不明白我的病情嗎?大醫院進了也白進,貴重藥用了也白用,為國家省著點不好嗎?”我的淚水再也忍不住地嘩嘩直淌……我忙給他捧上帶去的一束鮮花,有他喜歡的白丁香和紅玫瑰。我說:“老王,真不好意思,讓您先打電話來了……來不及備什么禮物,給您送上些您喜歡的花吧!”他高興地笑了:“我喜歡你早已做出了牌子,逢年過節從不給領導送禮拜年,只回老家陪父母。今天你能來,還送我喜歡的花,我……”我有意說:“不喜歡我了?”我倆都會意地笑了起來……
我早明白老王將不久于人世,我在回家鄉的路上,一直在想要給他寫篇文章,趕在他走前給他一點安慰,可由于種種顧忌,雖沖動地在大年初一就動了筆,最終還只是開了個頭。但我仍然認為:人走了,送再大的花圈,說再多的好話,已無多大意思,真有情,就趕在前。那天,我在老王家深深地感受到了一個認真的人在老而無權無力時的孤獨。為此,我更敬重認真的人,并將終生告誡自己,要雪中送炭,而無須錦上添花。
春節回滬后,我給老王打過一個電話,他說他的病情有了些好轉,能吃點流汁了。我高興了一陣,卻想不到沒過幾天,他就病危被送入了醫院。他仍然不肯進局級離休干部的定點大醫院,只愿住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地段醫院中,我明白他的意思:一是不愿再去多花國家的錢;二是不忍讓家人多花精力和時間在路上來回。我去看過他兩次:一次是與文學部的兩位老同事去的,老王鼻中插著輸氧管,手臂上扎著輸液管,我們相對無言。另一次,聽說他不行了,是陪兩位老廠長去的,老王掙扎著說出來三句話,一是問:“夏公走了?”他指的是夏衍的逝世。夏公病重,上影代表赴京去看望時,夏公也曾問起過老王。老王明白這回他將隨夏公而去了。二是問起上影的現任領導。三是“謝謝老領導的關心”。老廠長徐桑楚聽至此,眼圈一紅地說道:“我們是50年的老朋友了……”(此話當時我聽過算了,現在想來,老王逝世于1995年,50年前是1945年,可能當時他們都是聽從黨的指示回上海工作的)。兩位老戰友的生離死別之情,讓我非常感動。臨別時,我挨在老王耳邊說了聲“保重!”他吐詞不清地說道:“我沒有完成任務……”這是我聽到他最后對我說的一句話,這句話也只有我能聽懂,那是指寫周璇劇本和謝晉傳記的事。他到了生病的最后時刻,還如此自責,讓我更為感動。
老王臨終前問起上影現任領導,其實問的是吳貽弓,他似乎有什么話要對他說,又不便讓我轉告。此事,多年來我一直不敢向外提及,主要是怕有損老王的形象,似乎到了這地步還在乎現任領導來不來看他。最后,我實在忍不住了,在一次文聯委員在外地學習期間,一天早上正好與吳貽弓一起吃早餐,就對他說了此事。吳貽弓聽后久久沒有說話,似乎深深地觸動了什么,但他還是坦率地告訴了我這樣一件事:他在執導影片《姐姐》時,是以受盡艱難的紅四方面軍女戰士在風沙中繼續勇敢地前進作為結尾的,寓意非常清楚:雖然受盡磨難,前途未卜,但她們仍然不失理想,堅持前進……在送審時,時任副廠長的老王認為“光明面”還表現不夠,一定要打著紅旗前進。雖然吳貽弓認為這種表現太直露、公式化,但他也只能作此改動。影片公映后,確實有不少觀眾提出了這樣的意見,讓吳貽弓難以說清……我聽后,恍然大悟,心靈頓時為此一震,老王啊,他在臨走前,可能就為此事想對吳貽弓說點什么……
人與人的關系,歷來是人們關注和議論的重點之一。我與老王的關系,并非如有些人想的那么“俗”,我從未去巴結過他,只在他臨行前送來過他一束他喜歡的鮮花。更非如有些人想的那么“深”。人與人的關系除了帶有道德和政治層面的色彩之外,更多的關系是建立在想認認真真地為社會做些事上的。但人與人的關系又難避免受道德和政治層面的影響,經歷豐富和復雜的老王,勢必對此深有體會,他在《舞臺姐妹》中寫下的“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的經典臺詞,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但這恰恰是老王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