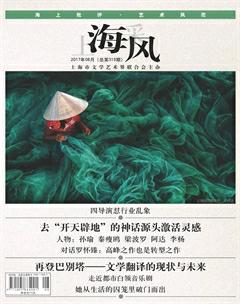牛人愛騎行
柯玲
騎行和劃船一樣,是很多牛村居民、牛津學子喜愛的一種出行和運動方式。牛津的自行車比汽車多,當然并非牛人不用或買不起汽車,而是因為大學城里除了觀光巴士和公交,很多路段都是限行私車的。同時也與大學的規定有關。大學只為大一新生提供一年的住宿,之后就要自尋住處。本科生的住處離牛津市中心不可超過6英里,研究生不超過25英里。這個距離無論去哪里都能騎車到達。牛津公交車服務系統非常齊全,但畢竟價格不便宜(6英里內來回大概要2.40英鎊,約合人民幣24元)。市中心的停車位很緊張,一般學院也只能提供有限的教員停車位,所以老師中的大多數也都是選擇將車停在牛津市郊的泊車點,在那里換乘公交來校。牛津街游人如織,但交通一直順暢,騎行為主自然少見擁堵。
牛津人稱騎自行車叫“賽客靈”(cycling)發音和鈴聲一樣清脆。更有趣的是人們說賽客靈時大多神采飛揚。可見,牛村騎車不僅很常見而且是件比較開心的事情,所以連語言中心的兩位年屆花甲的女士克麗絲和安曼達都是騎行上班族。克麗絲是語言中心的總管,她待人熱情,處事仗義,性格開朗,辦事高效。克麗絲明眸善睞,金發齊耳,雙肩背包,騎行時一副颯爽英姿!安曼達是英語口語老師,牛津畢業,牛津任教已38年。安曼達興趣廣泛,愛好雜多,足跡遍布全球。課上與學生聊起愛好,第一就是“賽客靈”,滿面紅光地說自己每天騎車來上課。語言中心主任鮑勃同時也是在現代語言中心工作,每日穿梭來往都用自行車。中文教授田海來自自行車王國荷蘭,簡直就是一位專業“賽客”。我曾跟田教授開玩笑說,“您是穿行于滄海桑田之間的一位牛津騎士!”還有我英國房東的兩個女兒,她們坐公交去學校非常方便,可小姐妹倆堅持每天騎車。記得一個大雪天的早晨,房東一邊給倆小天使戴頭盔,一邊試圖勸她們坐公交。小姐倆一起說“No,我們喜歡賽客靈!”風雪中母女吻別,我看了真很擔心:“雪天路滑,您還是應該勸止的!”房東笑著說:“沒辦法喲!她們喜歡!路滑應該還可以,好在下雪天自行車道會被優先清掃,你看,黃線上沒有雪的,說明已經被人掃過了。”嚄!沒想到牛人愛騎車,交通規則也這么呵護騎車!
但對于牛村的自行車道,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在快車道的邊沿,有一條十來公分寬的黃線就是所謂的自行車道,與快車道之間毫無間隔,這就是所謂的專用騎行道,只不過告訴你這里可以騎而已!英國的自行車資格很老,但有些缺陷顯而易見。牛津的自行車大多沒有腳撐。照理牛人不笨,為何要省略這個小而重要的部件?騎到終點車們不是倚墻靠壁就是席地而臥。不過牛人的行車安全意識很強,除了騎行有專線,車燈、車鈴、安全帽都是上路必備的。而且,牛人鉆研精神也表現在騎行中,靠近露天市場旁邊是牛津騎行協會,定期活動雷打不動,每次討論都有主題有難題,關于部件的、修理的、騎技的、文化的等等,牛人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對待騎行。我甚至覺得牛村的牛人輩出,或許與他們喜歡騎行有關。
騎行,不僅是一種出行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騎行方式甚至會影響到人的思維方式。自行車速度雖沒有汽車那么快,但該行該止同樣需要掌控有度。車轱轆轉啊轉,拖出往事一串串。高中的學校有一輛“公車”就是自行車——司務長每天騎著它去采購伙食。放學了吃好晚飯天還很亮,晚自修鈴聲未響,為數不多的住校生無所事事,就纏著司務長教學車。騎自行車不難,難的是上下車。只要你的腿夠長,上去就能騎車,不夠長也沒有關系,可以“別大杠”,就是一只腳從大杠下面伸過去踩腳踏。司務長是個大光頭,眼睛特別大,脾氣特別壞,但人不壞。他罵罵咧咧地將我們這些“細殺頭的”扶上車,推著我們走幾步就松手不管了。歪歪扭扭,抖抖豁豁中沿著操場拼命踩腳踏,一圈又一圈,直到司務長大吼“好了,死下來啊!也讓旁人騎騎!”司務長不會講解動作,上車容易下車難,下不來只好又騎一圈,但禁不住司務長的大吼大罵,最后只好橫下心來,眼睛一閉,縱身跳車。結果人摔倒在地上車還要向前跑一段才倒地。下一位同學已經摩拳擦掌受驚若寵地待命了。司務長對摔倒者不屑一顧,氣咻咻地去扶起他的坐騎,站到車頭前,兩腿將前輪一夾,倒抓車把,乜斜雙眼,雙手用力一扳,邊罵道:“倒頭車子就被你們這幫細殺頭的糟蹋死了!快死上來啊!”就這樣痛并快樂著學會了車,騎上單車,耳旁風馳電掣長驅直入的爽快感至今難忘!
說實在的,至今還十分感激司務長,畢業時我們到食堂去找他,司務長正忙,只背對著我們揮揮手,大聲道:“走吧走吧!快滾!沒工夫睬你們!煩死了!”我們知道他的表達方式,這就算是告別了。
在自行車稀缺的年代,我們能學會騎車殊為不易,而且“鄉村騎士”騎技更高一籌,因為鄉間泥路騎行的難度系數要比寬敞平整的柏油馬路高N倍。且說兩點——
一是“蹦缺子”,老家蘇北大平原,農田星羅棋布,土路顛簸不平就算了,更有阡陌交通,路上缺口很多。“缺口”是水放進放出的地方,老家稱“缺子”,尤其到插秧季,缺子有專人負責。缺子有大有小,大缺子會有一尺來寬,上面有時會擔一兩塊小木板,相當于一座微型橋;小缺子寬度往往在20公分左右。蹦大缺子,得對準小木板,毫不猶豫地沖過去,略有偏差就會馬失前蹄掉進缺子;過小缺子更要全神貫注,凌空時必須抬起臀部,提起龍頭,從缺子上“蹦”過去。如果不抬屁股就會被顛得生疼;如果不提龍頭前輪就有可能卡在缺子上;如果被卡的同時你又一腳踩進了缺子,同樣也會人仰馬翻。別小瞧這小小缺口,蹦缺子需要沉著冷靜的心理素質,要有藐視困難的氣勢,要有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更要有克服困難的技術,缺任何一樣都難以完成。
二是“沖橋”。老家位于里下河地區,河網密布,溝渠繁多。以至于三四歲時父母就要把我們扔進河里學游水。老家有多少橋?估計難以數計,我曾經統計過一次,從以前的工作單位到父母家,全程大約13公里,總共19座橋。所謂“橋”有很多形式,有繩橋有木橋有水泥橋,拱橋難度系數太低姑且不論,繩和板都有一根、兩根,一塊、兩塊之分。繩橋自行車無法過去的,一根繩過河雙手抓繩,雙腿盤繩,然后雙手向前挪。一上一下的兩根繩手腳都有了著落,過河就容易得多了,弟弟妹妹們當年有一段時間上下學就是這樣每天往返四趟。最酷的是我們的鄰居長輩,他們可以扛車過橋,也可以挑著一百多斤糧食過繩橋——面向對岸,凝神定氣,然后一手抓繩子,一手扶扁擔,雙腳踩繩,腳掌與繩子同向,一步一步腳踏實繩。圍觀者都屏住呼吸直到他們平穩上岸。自行車要挑戰的是板橋。一塊板的木橋不僅很窄,木板有時還上下震蕩,所以,這種小橋我一般都是老老實實,下車推行。問題是有些木板的寬度不夠你和自行車并行,這時就要將車扛在肩上過橋。扛車過橋跟女生挎包的動作差不多,其實不難的只是需要一把力氣:將大杠扛在肩上,一手抓車把,保持方向,一手握斜杠,三個點著力將車固定在空中就可以過橋了。有小毛頭力氣不夠,路過的大人看到了也會主動幫忙扛一下。兩塊板的橋面寬至少有70公分,車行軌跡不過是一條線而已,一塊板足矣。技高者一條直線過橋,次者小波浪蛇形,只要“蛇”不進入中間的縫隙(被卡),騎車過橋還是比較容易的。因此,騎車過橋的軌跡其實也是一段心理曲線:需要一鼓作氣,鎮定者過橋,保持直行。小河過橋容易,屏住呼吸幾秒鐘就沖過去了。難的是大河過橋,長橋臥波,難免有“路上不遇橋上遇”行人的時刻,腿長者會在中途停下交會,一腳撐地,過后再騎;苦的是腿短者從看見對面有人就開始車走蛇形了,勉勉強強與來人插肩而過,一路慌不擇路倉惶逃逸,抵達實地方松口氣。
若保險起見,所有的橋都應該推車而行,所有的缺子也可以下來搬過去,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偏偏喜歡冒險騎行。反思一下,秀車技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幾乎沒有觀眾。原因恐怕有四:一是速度的魅力,二是掌控的快感,三是喜歡冒險,挑戰自己,四是提升車技,發展自己。過橋和蹦缺子是農村騎行人難得的練車機會。會蹦缺子敢沖橋,天下道路奈我何!記得上高中時父親送我去開學,坐在后座上手里還能拿本小人書看看。坐墊是母親親手縫的,又厚又軟特抗震。父親車技絕對沒話說,但您難以想象我家最早的那輛自行車是沒有剎車沒有擋泥板的二手貨。父親要用右腳伸到前叉頭與車輪之間將車剎住,父親的“腳剎”比任何剎車都精準而又溫和,龍頭更是壓得穩穩。過橋或蹦缺子時,只輕聲提醒我“寶寶抓緊不動啊!”然后,還沒有感覺到,已經順利通過。就是這樣,父親一路騎行,依次將我們四人送出小村,送上中學,甚至送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