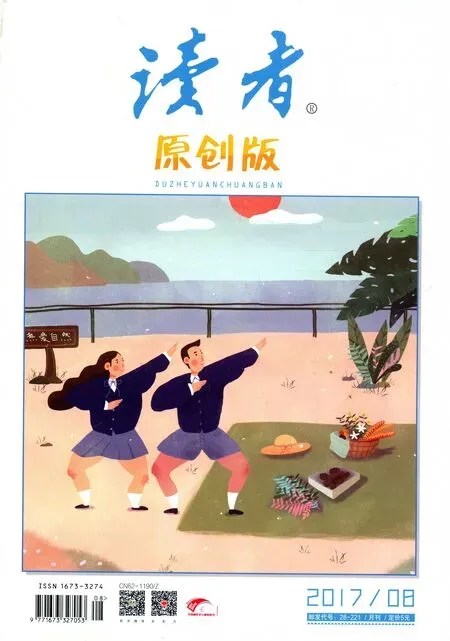語言的孤獨
文|米 周
語言的孤獨
文|米 周

一
一位同事的女朋友是日本人,有一次一起聊天,她說她最喜歡的日本作家是Murakami Haruki。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把話題轉到了別的上面。直到有一天我去逛書店,看見書架上正在銷售Murakami Haruki的《1Q84》,我才恍然大悟:她最愛的作家是村上春樹。第二天上班,我急匆匆地跑去找那位同事,興高采烈地讓他幫我轉告他的女朋友,我最愛的日本作家也是那位Murakami Haruki先生。然而,我的這位同事顯然不能理解我找到語言之橋的那種快樂。
在《圣經》里,人們說不同的語言是從建造巴別塔開始的。在那之前,所有人都說著同樣的語言。直到大洪水過后,人們打算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高塔。這觸怒了上帝,于是上帝讓人們說不同的語言,彼此無法交流,也就不能繼續(xù)建造巴別塔。寫出這個故事的人一定和我一樣,感受過語言的孤獨。語言的孤獨就像個魔咒,而這個魔咒有著不同的層次,層次越高越孤獨,而且越難治愈。
最初級的語言孤獨,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里,根本不會說或者只會說一點點當?shù)氐恼Z言。這時候產生的語言孤獨,和語言關系不大,更像是一種純粹的孤獨。比如當我到波蘭旅行,我不會講波蘭語,而波蘭人又不怎么講英語,所以基本沒法和當?shù)厝私涣鳌4蜷_電視,所有的節(jié)目我都看不懂;坐在餐館里,所有的菜譜我一個字都不認識—我一下子變成了一個“文盲”。這種孤獨感其實比較好克服。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有時候甚至還有些樂趣在里面,因為當語言不通帶來麻煩的時候,你需要動腦筋想辦法。比如想去火車站不知道該怎樣講,就模仿火車進站的聲音;想吃牛肉不知道怎樣講,就在頭上比畫出兩個犄角。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做錯了事,也可以賺取同情,得到理解。
二
第二階段的語言孤獨藏在文學作品里。這時候,就沒那么好玩了。
我剛剛看過三島由紀夫的《春雪》。雖然我被里面美妙的愛戀所打動,但仍然覺得,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和川端康成這些日本作家,雖然行文流暢,但有時讓我覺得不過就是堆砌辭藻罷了。作品有時似乎銜接得并不是很好,少了一些穿針引線的東西。直到前兩天,我在豆瓣網上看到一位旅居日本的網友寫的一段話,他說“夏天結束了”在日語里面并不僅僅表示夏天終結的意思,更有可能是在說“戀愛結束了”“童貞失去了”“女孩子月經初潮了”,或者說“一切全都完了”。看到這里,我猛然想到《春雪》。我把書又找了出來,翻到小說開始不久,清顯帶著本多和兩位暹羅的王子去父親位于海邊的行宮度假。其間三島由紀夫寫到了清顯對聰子的思念與誤會,也寫到了兩位王子對情人的思念。章節(jié)結束時,末尾一段赫然寫了五個字:夏天結束了。
原來,三島由紀夫很早就埋下了草蛇灰線,預示了清顯與聰子的愛情悲劇,甚至在此一箭雙雕,順帶連兩位王子的命運也一并做了交代。只可惜我讀的是中文譯本,自己又不懂日文,讀到“夏天結束了”,就當真以為只是說夏天結束而已。
這不禁讓我想到,《春雪》這本書中,到底還有多少被譯者抹殺(當然有時并非譯者的錯)的細膩心思,不得被我所見?而我讀過的所有譯文中,又有多少是我真正領略到了文學作品的趣味,而不是僅僅讀了一個故事呢?
第二階段的語言孤獨,閱讀譯文的讀者無疑能感受得到,然而更大的孤獨感應該來自作者。我的美國同事得知我出過幾本書,都說要看。但得知只有中文版本的時候,他們的態(tài)度便由些許的敬佩轉為了一種調侃—“哦,所以你才敢告訴我們吧?”“我可是有朋友懂中文,你不要騙我們啊。”每當這時候,我更同情的是那些生來就只能用小語種寫作的作家。我熟悉的作家大都來自英美,除此之外,也有法語、西班牙語、日語、德語這些大語種的作家。對于斯瓦希里語、僧伽羅語、阿爾巴尼亞語,我似乎想不出使用這些語言的文學家。有些語言甚至都沒有專門的譯者,比如我讀過的一本冰島詩集,是中文譯者參照著英譯本翻譯過來的;而那個英譯本,又是英國譯者根據瑞典語譯本翻譯過來的。一首詩被倒了三次手,才從作者到讀者,如果作者知道這件事,估計會抑郁而死。
三
語言孤獨的第三階段,出現(xiàn)在當你了解一門語言之后。
上大學那會兒,我在法國,由于有語言環(huán)境,我的法語一度突飛猛進。我曾經覺得,我的法語如此之好,以至于我好像窺探了身邊所有法國人的秘密。然而一門外語,無論你說得多么好,它總是會在某個時刻給你出一道難題,明確地告訴你,它并不屬于你。
我在讀大學時參加了一個戲劇社,每周上課的時候,老師都要讓同學們即興表演話劇,我是這門課上唯一的外國人。有一次,我們在表演一個類似于法院宣判的場景,我的角色是法官。被告人是一個年輕的寡婦,殺了酗酒家暴的丈夫,因而必須被判刑。根據劇情設定,我要在宣判之后對寡婦說一句類似“實在抱歉,我也無能為力”的話。
那句臺詞是“Je suis impuissant”,而我當時因為緊張,一時間忘了這句臺詞,便臨時想了一句“Je peux rien faire”。對我這個外國人來說,這兩句話表達的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表演結束之后,老師總結說,在臺上最好不要輕易改臺詞,比如“Je suis impuissant”的話外音是“我不想判你刑,但法律如此規(guī)定,我也無能為力”,但如果改成了“Je peux rien faire”,就有些敷衍的意思,好像在對人家說:“我什么都做不了,就這樣吧。”
我當時坐在臺下,心里無比委屈—我怎么能知道這兩句話在法語里會有這么微小的差別呢?我是外國人啊!但我的心情沒辦法和任何人說,因為不會有人懂我的。
這種事情發(fā)生的次數(shù)多了,就會讓你覺得有一種孤獨感。那門戲劇課,我后來再也沒有敢隨意發(fā)揮過,每次都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記住每句臺詞,也因為如此,我覺得它不再有趣,那個學期之后再也沒有去過。
四
語言孤獨的最后一層,是當你在外面轉了一圈,體會了所有的語言孤獨之后,回到家鄉(xiāng),說著自己的母語,卻忽然因為想不到某種表達方式,而被卡住的時候。
我在美國工作,周圍的同事都是美國人,我最長一段沒講中文的時間,差不多有兩個月。到后來,不知道是不是我腦子里面主管語言的部分感受到我的母語快要丟失的壓力,我會在說著英文的時候忽然蹦出中文詞語。我當時說得非常流暢,以至于自己并沒有反應過來,但是我的同事提醒我,說最近我總是講一些奇奇怪怪他們聽不懂的詞語,我才察覺到。
這種情況反過來更可怕:你明明知道你說的英文是什么,卻想不到對應的中文。
我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在會上向別人做presentation,形式一般是用PPT,花半個小時,向對方講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需要對方提供什么幫助或者反饋。有一次,我正在準備一個很重要的presentation,家里打來電話,我媽問我在做什么,我說:“我在準備一個……”我媽不懂英文,顯然不能跟她講presentation,但應該用中文里面的哪個詞代替呢?演講?報告?匯報?演示?最后我選擇了“匯報”。所以,在我媽的印象里,我每天忙的就是向上級匯報工作。
想不到中文詞更讓人感到孤獨,就好像回到了久違的家鄉(xiāng),但再也沒有認識的人了。
我曾經想,如果將來我有小孩,一定讓他們從小掌握三種語言,這樣也許就不會像我一樣,體會到如此多的語言孤獨。但仔細想想,語言不過就是一串音節(jié)、一組符號,本無意義。不同地方的人賦予其意義,并自得其樂,本是一件美好的事。就像出門遠行一樣,既然有勇氣跨過一座座橫跨溪流的橋,就別怕有孤獨陪伴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