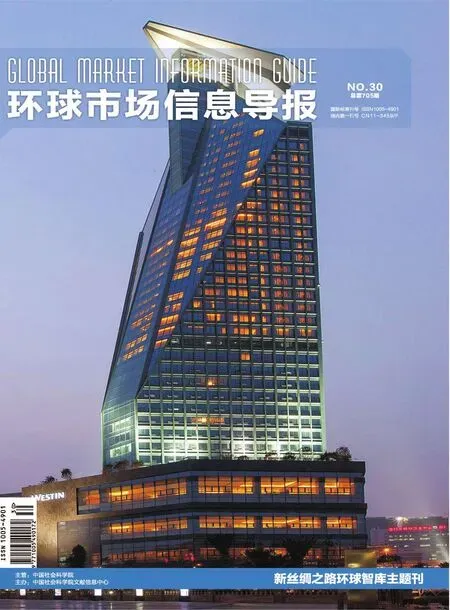職稱對(duì)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吳玉云
職稱對(duì)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吳玉云
目的:探討不同職稱對(duì)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方法:運(yùn)用主觀幸福感量表,隨機(jī)抽取720名的教師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結(jié)果:不同職稱的教師主觀幸福感存在差異,中學(xué)三級(jí)以下(含未定級(jí))教師得分顯著高于二級(jí)教師、一級(jí)教師;一級(jí)教師得分顯著高于二級(jí)教師。
問題的提出
教師的職責(zé)是教書育人,教學(xué)過程是教師對(duì)學(xué)生的影響過程,因此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教育教學(xué)質(zhì)量提高的基礎(chǔ)與保障。而教師主觀幸福感是其心理健康狀況與生活質(zhì)量的重要體現(xiàn)。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指?jìng)€(gè)體根據(jù)自定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其生活質(zhì)量所作的總體評(píng)價(jià),是反映某一社會(huì)中個(gè)體生活質(zhì)量的重要心理學(xué)參數(shù)。
隨著素質(zhì)教育與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 有關(guān)教師主觀幸福感的相關(guān)研究也應(yīng)運(yùn)而生。王陳等人對(duì)影響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因素進(jìn)行了廣泛的研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教師的性別、年齡、收入、職稱、從教科目、從教年級(jí)、教齡、學(xué)校類別以及工作地區(qū)等人口學(xué)變量均對(duì)教師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影響。邱秀芳對(duì)高校教師職稱、月收入對(duì)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其交互作用分析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主觀幸福感隨職稱和月收入的升高而增強(qiáng)。
由此可見職稱對(duì)教師的主觀幸福感有著重要影響。職稱是指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的專業(yè)技術(shù)水平、工作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級(jí)稱號(hào)。在目前中國的現(xiàn)狀下,職稱主要代表社會(huì)地位,象征著一定的身份,有高職稱的人享有較高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福利待遇。因此本項(xiàng)目假設(shè)教師主觀幸福感在職稱因素上存在顯著差異。
對(duì)象與方法
研究對(duì)象。隨機(jī)抽取十二所學(xué)校的教師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共發(fā)放問卷720份。中學(xué)三級(jí)及以下教師人數(shù)76(11.4%),二級(jí)教師人數(shù)241(36.2%),一級(jí)教師人數(shù)275(41.3%),高級(jí)及特級(jí)教師人數(shù)74(11.1%)。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主觀幸福感問卷,測(cè)得本研究總體信度是0.830,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各維度信度分別為0.847、0.854、0.841。將所有數(shù)據(jù)錄入SPSS16.0統(tǒng)計(jì)軟件包,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進(jìn)行數(shù)據(jù)處理和統(tǒng)計(jì)分析。
結(jié)果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jié)果表明,不同職稱的教師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差異(見表1)。事后多重比較發(fā)現(xiàn),中學(xué)三級(jí)以下(含未定級(jí))教師得分顯著高于二級(jí)教師(P<0.001)、一級(jí)教師(P<0.05);一級(jí)教師得分顯著高于二級(jí)教師(P<0.05)。倦怠,這使得他們主觀幸福感較低。對(duì)于一級(jí)職稱的教師,其教齡相對(duì)較大,在長期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中,他們的職業(yè)倦怠現(xiàn)象較低級(jí)別職稱教師突出,身體和精神狀況也相應(yīng)下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主觀幸福感。但這個(gè)階段的教師一般都有穩(wěn)定的家庭和事業(yè),安居樂業(yè),因此,一級(jí)教師比三級(jí)以下職稱的教師主觀幸福感低,而比二級(jí)教師的主觀幸福感高。

表1 不同職稱的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差異比較(χ±s)
討論
研究表明,不同職稱的教師在主觀幸福感方面得分差異顯著。中學(xué)三級(jí)以下(含未定級(jí))教師主觀幸福感得分顯著高于二級(jí)教師、一級(jí)教師;一級(jí)教師得分顯著高于二級(jí)教師。其總體趨勢(shì)為,教師的職稱越高,其主觀幸福感越低。但在這個(gè)總趨勢(shì)下出現(xiàn)了一種特殊的現(xiàn)象:居于中間的二級(jí)教師的主觀幸福感顯著低于三級(jí)以下和一級(jí)職稱的教師。對(duì)于這種現(xiàn)象,筆者認(rèn)為,三級(jí)以下的教師,多是較為年輕的新教師。近些年,學(xué)校對(duì)教師學(xué)歷的要求提高,許多地區(qū)的中學(xué)只招大學(xué)本科學(xué)歷及以上的教師,從而使得新任的年輕教師相比一些老教師在學(xué)歷上有優(yōu)勢(shì)。盡管他們的職稱暫時(shí)較低,但是由于他們?nèi)温毑痪茫瑢?duì)自己的職業(yè)有更多的激情和憧憬,對(duì)職業(yè)的認(rèn)同感較高。除此,年輕教師的教學(xué)技能和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相對(duì)不足,對(duì)于他們,每天的教學(xué)工作是積累經(jīng)驗(yàn)、學(xué)習(xí)和進(jìn)步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其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要,從而體驗(yàn)到較高的幸福感。對(duì)于居于中間的中學(xué)二級(jí)教師,他們更希望晉升,但新任的年輕教師在學(xué)歷上的優(yōu)勢(shì)增加了他們?cè)诼毞Q評(píng)定上的競(jìng)爭(zhēng)壓力,加之多年重復(fù)單調(diào)的教學(xué)活動(dòng)使得許多教師產(chǎn)生了職業(yè)
對(duì)策
教育制度改革。國家教育部門應(yīng)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努力普及素質(zhì)教育,改變以學(xué)生升學(xué)率作為衡量教師教學(xué)能力水平的標(biāo)準(zhǔn)的制度,以及改革完善教師晉升考核制度,為教師提供透明化考核制度,創(chuàng)造更好的教師晉升條件,使教師看到職業(yè)發(fā)展的前景,感受到自己的價(jià)值以及自身工作的意義。
明確職稱評(píng)定制度,針對(duì)性的提高不同職稱教師主觀幸福感。學(xué)校應(yīng)使教師職稱評(píng)定制度、晉升制度明朗化,做到公開、公平、公正,使教師充分了解職業(yè)前景和晉升程序,從而設(shè)計(jì)職業(yè)規(guī)劃,明確目標(biāo)。針對(duì)不同職稱的教師群體,學(xué)校應(yīng)結(jié)合各個(gè)群體的現(xiàn)實(shí)需要和所面臨的課題給予相應(yīng)的支持和幫助,引導(dǎo)各級(jí)教師合理看待職稱評(píng)定問題和設(shè)立長遠(yuǎn)規(guī)劃,調(diào)整心態(tài),提高幸福感受能力。
重視身體健康,奠定幸福基礎(chǔ)。本研究表明,職稱較高的教師的主觀幸福感比較低,其中一個(gè)原因是由于高職稱教師的年齡相對(duì)較大,身體健康水平和精神狀況有所下降。因此,教師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以實(shí)際行動(dòng)維護(hù)、優(yōu)化身體素質(zhì),保持健康的身體。
(作者單位:河源技師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