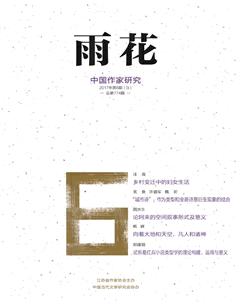于荒誕中拷問存在的意義
鄧全明
范小青在接受傅小平的采訪時曾說:“我喜歡人與人之間的微妙的感覺,這種細膩的關系,一直深入到肌理細紋里的,深入到骨髓里的”,①這道出了范小青一以貫之的一個審美傾向:她喜歡洞察人情世故,擅長在人性之細微處下工夫,以極具現實感的方式營造她的藝術世界。施戰軍將范小青的小說稱為“當代世情小說之翹楚”②,大體也是指范小青小說的這一審美特征。世情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作者與作品中的人物保持同等高度的敘述眼光,和人物一樣在小說世界浮沉、逐流,而不愿意跳出作品,以居高臨下的眼光評判他的人物、他描寫的世界。以《褲襠巷風流記》和《女同志》為代表的范小青前期小說,確實帶有濃厚的世情小說的色彩,不過,從創作《赤腳醫生萬泉和》開始,范小青世情小說審美傾向發生了改變:高度仿真的原生態的世情被較強符號化“第二自然”代替,而荒誕、混亂、無序成為第二自然的主色調。這標志著范小青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一、《赤腳醫生萬泉和》:主體被懸擱的悲劇人生
作為范小青進入新的創作階段的第一部作品,《赤腳醫生萬泉和》延續了范小青小說從細處落筆、從人情的細微處反映歷史大潮流的風格:通過一個鄉村醫生的命運和江南水鄉一個名叫后窯村的村莊醫療事業的發展史,展示建國后半個世紀中國政治的風云變幻和歷史的起起落落。不過,與以前的小說不同,《赤腳醫生萬泉和》的荒誕性明顯增強。《赤腳醫生萬泉和》的荒誕性突出體現在主體被懸擱的生存事實上。人的主體性是自文藝復興后的人文主義對人的一個基本預設和價值原則,人可以自由地選擇、按照自我的選擇實現自我的價值是人的主體性的重要內涵,而萬泉和最大的悲劇在于他的主體性被懸擱、強暴。萬泉和的人生理想是成為一個木匠,然而,命運弄人的是,他這樣一個沒有醫生的資歷、能力,也沒有意愿做醫生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到醫生的位置。萬泉和第一次成為醫生,是他的父親一再在隊長前面叫苦,要求增加一名醫生,而后窯村又沒有合適的人選,隊長裘二海便讓他做醫生。盡管萬泉和本人、還有他的父親堅決反對,“他就是政策,他就是道理”③的裘二海全然不理會,更有愚昧的村民以為父親是醫生、兒子就能是醫生,也堅持要他做赤腳醫生。萬人壽癱瘓、涂醫師回到鎮醫院后,萬泉和有了結束赤腳醫生生涯的機會,但裘二海半是賴皮、半是無奈,讓萬泉和繼續一個人堅持把合作醫療社挺下來。農村土地承辦到戶后,萬泉和作為那個時代特殊產物的赤腳醫生的身份也隨著時代的遠去而失去,萬泉和理應結束強加于他的醫生生活。但時代再一次和他開了個玩笑,在萬小三子和馬莉的綁架下,萬泉和再次成為鄉村醫生。萬泉和在愛情上也遭受了類似的命運。萬泉和先后愛過三個女人:劉玉、裘小芬和許琴英,這三個女人也都曾對萬泉有意,但鬼使神差的是這三個女人都離他而去:劉玉因為與醫療所的退伍軍人吳寶有染而遠嫁,裘小芬因為惡心萬泉和做人工呼吸吸到病人的痰而遠去,許琴英因為萬泉和屢次爽約而離去。萬泉和和馬莉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他也不喜歡馬莉,馬莉卻像狗屎一樣粘著他,甚至阻止萬泉和和劉玉的“和好”。被強加的還不止這些:劉玉不僅欺騙了萬泉和,還把自己的兩個孩子強塞給了他。萬泉和的人生,始終是被強加的,想要的人生不能要,不想要的卻被強加而不能不要,主體喪失、無可挽回的人生困境陡然增加了作品的荒誕色彩。但《赤腳醫生萬泉和》不想在此止步:它還要表現人在無法選擇的荒誕中的主動選擇。深入萬泉和的受難后,我們會發現,他也并非完全被動,而有主動受難的因素。無論是“文革”時代的裘二海的政治壓力,還是改革開放時代萬小三子的經濟誘惑,萬泉和都不是完全沒有躲避的可能,他之所以承擔起那份可能不能承擔起的沉重責任,多少有點殉道的意味。既然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無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雖然他也不是理想的人選,但既然沒有更好的人選,他也就不再推三阻四了。在這過程中,萬泉和也有過動搖,有過困惑,但最后,他終于達到了孔子所說的知天命的人生境界。作品最后寫到后窯村民出錢,再次成立醫療所,但沒有醫生,村民們再次將目光投向萬泉和,他經過一陣慌張、逃跑之后,終于平靜下來,靈魂也回來了。我想,如果村民們真的需要他再次犧牲,他也只好平靜地接受天命——這個天命并不是上天,而是某種歷史的特殊機緣。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看似智力不及一般人的萬泉和身上,卻有著人的高尚之處,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沉甸甸的東西。這也表明,范小青轉向之后,基本價值取向還是沒有大的變化。
二、《香火》:信仰崩潰之后的空洞人生
《香火》仍具有較強的生活質感和史詩性:從一個寺廟的興衰和一個村莊村民信仰的嬗變展現了后社會主義時期廣大農村農民的思想史、心靈史。同時,《香火》也是一部具有較強的形而上色彩的作品,它揭穿了宗教、信仰的實質,將人類放逐到了無意義的荒原,讓人看到了荒誕的存在。《香火》中的那個沒有出現名稱的村子和古老中國的許多村莊一樣,你或許可以說它愚昧、落后,但不可否認,它原本有著自己的精神家園——太平寺和陰陽崗。雖然小說沒有寫到,在“文革”破“四舊”之前,那里的村民如何信奉太平寺的菩薩,如何供奉自己的祖先,但從他們極力保護菩薩和祖墳的舉動中——老屁、四圈等村民自告奮勇承擔了保護菩薩的責任,我們不難推測太平寺和太平寺里的菩薩、祖宗在他們的精神世界有著什么樣的位置。當政治運動來臨時,這些村民無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最終,太平寺還是關門了,陰陽崗的祖墳還是被夷為平地,種上水稻。敲菩薩、毀寺廟、掘祖墳事件產生的破壞作用,遠不止禁止村民們信奉菩薩和祖先那么簡單,而是讓他們看到了信仰的虛幻性。以前,村民們敬畏菩薩、供奉祖先也不一定是出于十分虔誠的宗教信仰,或許只是一種習得的傳統、思維定勢所然。不管是習得的行為還是虔誠的信仰,有一點是相同的:菩薩和祖先是不可冒犯的神靈,一旦冒犯,就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故此,誰也不敢冒險去冒犯看不見、摸不著的神靈,對依附于菩薩、祖先的那些甚至不知所以然的信條、教義也保持程度不等的敬畏之心。“文革”中的造反派借助新生政權的革命性力量,褻瀆了這些村民們從來都不敢褻瀆的神靈,讓村民發現了一個事實:神靈原來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也不能為他們提供任何保佑。神靈或者說神靈的權威不存在了,依附于他們的信條、教義也失去了合法性,變得虛妄不實了。老屁說的“尊敬菩薩有屁用,菩薩又保佑不了我”④突出反映了村民心靈的變化:神沒有了,這世界沒有什么可害怕、敬畏的了。中國歷史上并非沒有這樣的宗教災難,如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滅佛運動,但滅佛運動只是以一種神代替另一種神,而不是滅掉神靈本身。解放后的滅神運動去除了原先所有的神靈,但并沒有造新的神靈。《香火》中除了寫菩薩、祖先為代表的民間信仰外,還寫到大傳統——新的意識形態中的信仰。烈士陵園的主任是一個符號性很強的人物,他不辭辛勞地尋找烈士的后代、維護烈士陵園是他信仰的突出體現。與主流意識形態完全拋棄傳統文化不同,他按照傳統的思維模式,將文化中“大傳統”與文化“小傳統”結合,如他認為烈士無所不知,實際上是將他們神化——與孔子、關羽的神化類似。烈士陵園的主任企圖像過去一樣,將新政權的神加入到諸神系列,以達成民間信仰與官方信仰的統一,保持信仰的連續性,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新的政權信奉唯物主義,有信仰但沒有神,沒有神的信仰似乎失去了進入民間信仰的通道——兩者之間的統一性被破壞了,其結果是無論國家信仰還是民間信仰影響力都大大弱化。神靈的消失,并不是當代中國一個國家的事,其實,西方早已驚呼“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人被拋棄在沒有意義、沒有歸宿的荒原,這正是人世的荒誕所在,也是現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現代派藝術熱衷表達的生存本相。《香火》向我們揭示的正是這樣的世界,雖然香火的村子里還有陰陽崗,還有太平寺,但那都是用來賺錢的工具,與精神的家園沒有關系。精神家園沒有了,村民們該如何去生活,中國人該如何面對傳統神靈被摧毀之后的價值荒原,這正是范小青所擔憂的。
三、《我的名字叫王村》:沒有真實的荒誕世界
201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我的名字叫王村》是范小青現代派色彩最濃、也是對現實最為失望的一部作品。《我的名字叫王村》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我”及家人因為弟弟是一個精神病人給家里帶來諸多麻煩而決定將他拋棄,把他拋棄后又因為有名的——外界的道德指責和自我良心的譴責——和無名的——既然無名當然也無法言說——理由,費勁周折尋找弟弟,最后把弟弟找回來了,卻不能確定找回的是不是自己的弟弟。關于這一情節的敘述倫理,范小青說:“我在小說中反復使用‘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之類的繞口令似的迷徑,應該是通過這種設置,體現現代人迷失自己、想尋找自己又無從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確定自己的荒誕性”⑤。從中可以看出,范小青將荒誕性作為這部小說主要的敘述倫理。何同彬對此有不同的理解,他將重點放在了不確定性上。在《靜默與無名的‘問題性——〈我的名字叫王村〉讀札》一文中,何同彬寫道:“‘不確定性是后現代哲學描述當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判斷……《我的名字叫王村》的確以其異質、斷裂、矛盾和豐富的可能性完成了一次純粹意義上的‘不確定”。⑥對于何同彬來說,《我的名字叫王村》不確定性才是現實的本質——包括荒誕性。人或者說現代人有沒有本質,有沒有精神家園,這一作者要追問的問題在“我”尋找弟弟的路途中逐漸展開。一開始,無論是對王全自己還是他的熟人,王全是不證自明的,他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他沒有精神病,有精神病的是他的弟弟。但隨著尋找弟弟情節的發展,他逐漸變得不真實了。先是江城救護站的工作人員認為他就是他弟弟,后來他村里的人把他當作了他弟弟,甚至他的家人也認為他精神不正常了甚至他就是他弟弟。于是,王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他不是他自己了。最后,王全終于找回了弟弟,他的合法性似乎無可懷疑了。但事實并不是這樣:他是找了一個弟弟回來,但找回來的弟弟卻不承認自己是他的弟弟——找回來的是不是他的弟弟卻得不到確認。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弟弟是一個象征符號——“寓意著當代社會在片面追逐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情景下,人們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⑦,失去弟弟,是自我的迷失,尋找弟弟,是尋找迷失的自己。最后無法確認找到的是不是弟弟,是否有弟弟,其寓言意義則是人是否真的有自我,真的有本質。最后敘述人對于王全找回的是不是他的弟弟、小王村是不是過去的小王村這些問題,并沒有告訴我們肯定的答案。一切都籠罩在不確定性中——真實與不真實的荒誕中。《我的名字叫王村》的荒誕主題也體現在無處不在的生存悖論。王全歷盡千辛萬苦找回了弟弟,弟弟卻不承認他是王全的弟弟,更令人沮喪的是:弟弟回家了,家鄉小王村卻不見了。“小王村的人個個都在家里,卻沒有了家,我弟弟—直在外面混,卻偏偏他有個家”。⑧“我弟弟是個病人,他們卻不敢說他有病”⑨,我不是病人,總是被人懷疑有病。“我告訴她我弟弟是老鼠,她走了,分明是嫌棄我家有一只老鼠;后來我再告訴她老鼠丟掉了,她又走了,又好像她對我丟掉弟弟有很大的不滿”⑩。這些都表明無論是“我”還是小王村的存在,都是一個悖論。另外,《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各種光怪陸離的亂象,如“我”行將就木的父親忙著結婚、結婚,村長和王圖是“一對夫妻一個家庭”也在展示存在的荒誕性。
四、荒誕中存在意義之拷問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范小青近期小說的荒誕色彩越來越濃,特別是《我的名字叫王村》儼然一部演繹非理性思想的、典型的現代主義作品,與她前期作品的主題迥然不同。其實不然,范小青近期三部作品確實展現了世界的另一面——荒誕、虛妄、無意義,但筆者并不認為范小青在演繹存在主義的世界是荒謬的主題。筆者更傾向于認為:范小青小說雖然展示了世界的荒誕性,但并不一定就認為世界的本質是荒謬的。何同彬反對將《我的名字叫王村》看作卡夫卡《城堡》式的寓言,也反對將其視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而愿意以“不確定性”來歸納作品中的種種亂象。筆者以為,何同彬認為范小青小說雖然表現了世界的荒誕性,但未必就是表現世界是荒誕的主題:在前者,荒誕可能只是世界諸多屬性中的一種,在后者,荒誕成為世界的本質屬性。范小青小說中的荒誕不僅與存在主義的荒誕具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她處理荒誕的態度也與存在主義、激進的現代主義不同。承認世界的荒誕性并直面這種荒誕性是范小青近期小說的一個突出特征——表明她對人性、世界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認識。比直面人世的荒誕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不無荒誕的人世,對于一部偉大的作品來說,后者也許比前者更重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孔子重要的人生信條,反映的正是孔子如何面對不無荒誕性的世界。為何會“不可為”?是一時“不可為”,還是宿命般的永遠“不可為”?先說第一個問題。所謂“不可為”并非不能為,而是“為”了也達不到自己的目標,“為”了等于白“為”。“不可為”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其中或許包括世界存在荒誕性,也還有時有利與不利的問題。“亂”——混亂、荒誕——是亂世的本質,生于亂世就會“不可為”,但人必須直面“不可為”的亂世。孔子直面亂的方式是“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不可為”,為何還要“為之”,這就是儒家所說的“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的仁,“為之”是人尊嚴的體現,人的高貴的體現。再說第二個問題。儒家以治世、亂世論世,有亂世必有治世,因此“不可為”并非宿命,永遠不可為,而是一時一地“不可為”。筆者認為范小青小說中的荒誕與儒家學說中的亂世有著相似的性質,也正因為此,范小青沒有將世界推向荒誕的極端,也沒有將自己推向與塵世決絕的極端,而是在表現“對一切的一切的疑惑”的同時,也帶著“一切的一切的溫情” 。“萬泉和、香火、‘我(王全),都是一類人物……他們都成為堅韌的承受者,他們是我最愛的、投入最多情感的人物,他們的內心世界和我的內心世界是相通的,相同的” ,萬泉和、香火、王全是愚者,也是智者,如果我們不以普通的生活邏輯解讀他們的生活細節,他們可以說是那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范小青在表現世界的荒誕性時,仍然塑造了“堅忍的承受者”,仍然不忘對現實問題的關心,仍然流露悲憫的情懷,這反映了她對人世、存在的基本態度——人性有惡不乏善、世界存偽不乏真,也反映了她寫作的基本立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喚醒“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之仁。
注釋:
①范小青、傅小平:《中庸是一種強有力的內斂的力度》,《文學報》,2014年4月10日第3版。
②施戰軍:《當代世情小說之翹楚——范小青論》,《揚子江評論》,2009年第1期。
③范小青:《赤腳醫生萬全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頁。
④范小青:《香火》,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版,第226頁。
⑤范小青、傅小平:《中庸是一種強有力的內斂的力度》,《文學報》,2014年4月10日第3版。
⑥何同彬:《靜默與無名的“問題性”——<我的名字叫王村>讀札》,《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4期。
⑦賀紹俊:《長篇小說:講出中國故事的世界意義》,《文藝報》,2016年9月14日,第3版。
⑧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98頁。
⑨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頁。
⑩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頁。
范小青、傅小平:《中庸是一種強有力的內斂的力度》,《文學報》,2014年4月10日第3版。
范小青、傅小平:《中庸是一種強有力的內斂的力度》,《文學報》,2014年4月10日第3版。
[本文為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從建構性價值取向看詩意江南的失落與重建——以新時期蘇州小說創作為例”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090-2015SJD601]
(作者單位: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