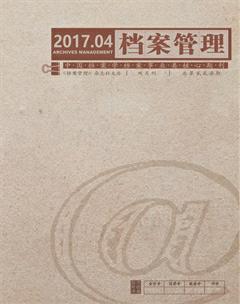檔案犯罪的立法完善
張勝全
摘 要:檔案犯罪的現行規定,存在保護范圍太狹窄、概念表述不嚴謹、與檔案法不銜接等缺陷。應當把非國有檔案納入刑法保護范圍,完善相關條文的語言表述,增設一些新的檔案犯罪罪名。修訂后的檔案犯罪罪名包括非法獲取檔案罪,非法出賣、轉讓檔案罪,故意損毀檔案罪和偽造、變造檔案罪。
關鍵詞:檔案犯罪;立法缺陷;立法完善
Abstract:There are some legislative defects in current provisions of archive crimes, such as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is too narrow, the concept expression is not rigorous, it does not converge with the Archives Act, and so on. The non state-owned archiv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mproving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providing some new archive crimes. The revised archive criminal charges include the crime of illegal access to archives, the crime of illegally selling or transferring archives,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ly damaging archives and the crime of forging or altering archives.
Keywords:Archive crime; Legislation defects; Legislation perfection
1979年刑法沒有單獨規定檔案犯罪,僅在第100條規定的反革命破壞罪中規定了以反革命為目的的搶劫國家檔案行為。1997年修訂刑法,在第329條增設了兩個檔案犯罪,即搶奪、竊取國有檔案罪和擅自出賣、轉讓國有檔案罪。相較于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將檔案犯罪歸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將檔案犯罪的對象由國家檔案修改為國有檔案,將檔案犯罪的行為方式由搶劫修改為搶奪、竊取、擅自出賣、擅自轉讓,立法的科學性有所增強,但還存在不少缺陷,尚有進一步發展完善的空間。本文擬在剖析檔案犯罪立法缺陷的基礎上,對檔案犯罪的立法完善作以探討。
1 擴大檔案犯罪的保護范圍
刑法從所有權的角度界定檔案的保護范圍,也許反映了立法者希望利用有限的刑事司法資源重點保護國有檔案的初衷,但這種選擇性立法不僅理由不充分,而且還有身份歧視之嫌。檔案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其價值的大小并非取決于所有權的歸屬。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刑法在檔案保護范圍上的立法缺失及其帶來的消極影響日益顯現。
首先,缺乏界定檔案所有權的法律標準。雖然檔案法把檔案分為國有檔案、集體檔案和個人檔案,刑法也將保護范圍限定為國有檔案,但確定檔案權屬的標準是什么,兩部法律均沒有作出規定,進而造成認識上的歧見。在理論界,有的從檔案的保管場所來界定國有檔案,認為國有檔案是指國家檔案館保管且所有權屬于國家的檔案。[1]有的從檔案的來源來界定國有檔案,認為國有檔案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由國家(財政)提供經費的單位在管理國家事務活動中形成的為國家所有的檔案。[2]有的從檔案的管理單位來界定國有檔案,認為國有檔案是指由國家檔案部門、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管理的檔案。[3]檔案權屬界定標準的付諸闕如,必然給刑法的適用帶來困惑,例如,對國家檔案部門代管的或寄存于國家檔案部門的集體檔案、個人檔案是否屬于國有檔案,理論上可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其次,非國有檔案具有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厚此薄彼的身份立法觀念不僅與現代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而且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雖然仍是國民經濟的主體,但非公有制經濟已占據半壁江山,其法律地位已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非國有單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活動中產生的檔案不僅數量愈來愈多,而且有些檔案對國家和社會也極具保存價值。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管理的創新,呼吁刑法與時俱進,把非國有檔案也納入保護范圍。
最后,刑法將保護范圍限定為國有檔案有違對檔案法的立法精神。檔案犯罪屬于法定犯或行政犯,既具有行政違法性,又具有刑事違法性,而且行政違法性是刑事違法性的前提。刑法對于檔案犯罪的規定應當以檔案法的規定為基礎,應與檔案法的規定相協調。《檔案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的9種違法行為中,除了損毀、丟失和擅自提供、抄錄、公布、銷毀的對象為國有檔案外,其他7種違法行為的對象都是檔案,既包括國有檔案,也包括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或者應當保密的檔案。這說明檔案法雖然基于行政管理的便宜把檔案分為國有檔案、集體檔案和個人檔案,但這并非旨在強調只對國有檔案給予刑法保護,而把非國有檔案拒之刑法門外。刑法把檔案犯罪的保護范圍局限于國有檔案,是有違檔案法的立法精神的。
總之,在國有檔案與非國有檔案的界定上沒有形成統一觀點的情況下,在刑法上區別對待國有檔案和非國有檔案缺乏理論基礎;將國有檔案與集體所有和個人所有的檔案區別對待,還有從身份上歧視非國有檔案財產之嫌。[4]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加強檔案文化信息資源的保護,必須擴大刑法對檔案的保護范圍,應把所有檔案均列入刑法保護范圍。需要指出的是,把非國有檔案納入刑法的保護范圍雖然是理論界的共識,但在此前提下是否仍然需要有所選擇或側重,理論上有種觀點主張,除國有檔案外,只將集體、個人所有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保存價值的珍貴檔案納入刑法保護范圍。[5]其實,這種限定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根據《檔案法》第2條對檔案定義的規定,能夠稱作檔案者,必須是“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歷史記錄,否則,就根本不是檔案法所規定的檔案。
2 修訂檔案犯罪的構成要件
現行刑法將檔案犯罪的行為類型規定為搶奪、竊取、擅自出賣、擅自轉讓4種,相對于1979年刑法的規定,行為類型有所增加,但相對于檔案法的規定而言,行為類型又有遺漏。此外,檔案犯罪的條文在語言表述上也不夠嚴謹。正如有學者指出,1997年刑法將1979年刑法規定的“搶劫”改為“搶奪”,容易使人產生模糊認識,誤以為搶劫國有檔案的不構成犯罪,只有搶奪國有檔案的才構成犯罪。但從立法本意上看,搶劫國有檔案仍然構成犯罪,只是將搶劫一詞隱含在搶奪詞語當中而已,搶奪國有檔案當然包括搶劫國有檔案的行為。[6]又如,關于擅自出賣、轉讓國有檔案罪,刑法條文表述為:“違反檔案法的規定,擅自……”然而,根據《檔案法》第17條第1款的規定,國有檔案是禁止出賣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擅自”出賣國有檔案的問題。所謂的擅自出賣、轉讓,是針對非國有檔案而言的,亦即非國有檔案經過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的許可,是可以出賣或者轉讓的;未經許可的,則屬于擅自出賣或者轉讓。另外,從語言表述上來看,“違反檔案法的規定”與“擅自”也純屬同義語反復,因為,只要違反檔案法的規定出賣、轉讓檔案的,就屬于擅自出賣、轉讓檔案,反過來說,擅自出賣、轉讓檔案的,肯定違反了檔案法的規定。換言之,“擅自”一詞純屬多余,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完全是冗余的表述。
因此,根據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結合檔案法的相關規定,應對現有的兩個檔案犯罪的構成要件作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具體來說,就是將搶奪、竊取國有檔案罪的構成要件修訂為:“搶奪、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檔案的,處……”罪名相應地確定為非法獲取檔案罪。將擅自出賣、轉讓國有檔案罪的構成要件修訂為:“非法出賣、轉讓國有檔案的,或者未經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出賣、轉讓集體檔案、個人檔案或者其他不屬于國家所有的檔案,情節嚴重的,處……。非法向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出賣、轉讓檔案的,從重處罰。以牟利為目的,倒賣檔案的,從重處罰。”罪名相應地確定為非法出賣、轉讓檔案罪。之所以作如此修訂,主要是為了與檔案法的相關規定相協調。根據《檔案法》第17條和《檔案法實施辦法》第18條的規定,國有檔案禁止出賣,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因資產轉讓需要轉讓檔案的,須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所以,對非法出賣、轉讓國有檔案的,不作情節嚴重的要求。根據《檔案法》第16條第2款和《檔案法實施辦法》第17條的規定,集體檔案、個人檔案以及其他不屬于國家所有的檔案可以出賣、轉讓,但如果是向各級國家檔案館以外的單位或個人出賣、轉讓的,須報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批準。所以,非法出賣、轉讓非國有檔案,只有情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根據檔案法的規定,嚴禁倒賣檔案牟利,嚴禁將檔案出賣、轉讓給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所以,對這些違法行為作出從重處罰的規定。
3 增設新的檔案犯罪罪名
《檔案法》第24條和第25條共規定了9種違法行為,并且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1997年修訂刑法時,除了增加了檔案法沒有規定的搶奪、竊取國有檔案罪外,只將檔案法規定的擅自出賣、轉讓檔案的行為納入刑法之中,而且將犯罪對象由檔案修改為國有檔案,對于檔案法規定的涂改、偽造檔案,損毀、丟失檔案,擅自提供、抄錄、公布、銷毀國有檔案,倒賣檔案或向外國人出售、贈送檔案,非法攜運檔案出境等行為,并沒有予以吸納規定為具體罪名。對此,刑法學界的解釋是,現行刑法并非將《檔案法》第24條規定的情況全部規定為犯罪,而是有重點地進行選擇規定,這樣既有利于對檔案的保護,又避免了刑罰的過度介入,形成對檔案保護輕重結合的法律體系。[7]但是,刑法是后盾法,沒有刑法的保障,其他法律的威懾力就會大打折扣。刑事立法的這種做法雖然彰顯了刑法的謙抑精神,但卻使得檔案法的規定形同虛設,以致檔案界發出了檔案法是“軟法”的嘆息。
現行刑法關于檔案犯罪的罪名體系,已經無法滿足檔案刑法保護的實際需要,增設檔案犯罪的罪名成為學界的共識。但應當增設哪些罪名,意見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主張增設毀損、丟失國有檔案罪,涂改、偽造檔案罪,攜運禁止出境的檔案或其復制件出境罪,非法持有國有檔案罪,擅自提供、抄錄、公布、銷毀國有檔案罪。[8]有的主張增設偽造、變造檔案罪,故意或過失毀損珍貴檔案罪,擅自拋棄、銷毀國有檔案罪,擅自公布受控檔案罪,非法攜運檔案出境罪。[9]有的主張增設故意毀損檔案罪,過失毀損檔案罪,偽造、變造檔案罪,非法向外國人出售、贈與檔案罪,非法攜運檔案出境罪,搶劫檔案罪。[10] 有的主張增設故意損毀珍貴檔案罪,過失損毀珍貴檔案罪,非法向外國人出售、贈送珍貴檔案罪,擅自提供、抄錄、公布、銷毀國有檔案罪,偽造、變造檔案罪,走私檔案罪。[11]上述觀點的共同點是以《檔案法》第24條和第25條的規定為根據增設新罪名,不同點在于犯罪對象的確定上。我們認為,增設檔案犯罪罪名,不僅要考慮檔案法的相關規定,而且還應保持罪名體系的協調,既要避免重復,又要防止遺漏,所以必須對檔案法規定的違法行為進行整合,僅增設一些必要的罪名。
首先,犯罪對象只規定為檔案即可,既不能仍然限定為國有檔案,也無必要限定為珍貴檔案。把檔案犯罪的對象限定為國有檔案的不合理性上文已述,在此不贅。將檔案犯罪的對象限制為珍貴檔案,一方面沒有檔案法上的依據,另一方面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將文物藏品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又分為一、二、三級,并制定了極為詳細具體的定級標準,所以,刑法將部分文物犯罪的對象限定為珍貴文物,不僅有文物保護法的明文規定,而且存在具體的標準可供參照執行。但是,檔案法對檔案的界定標準只有一個,即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并無珍貴檔案與普通檔案之分。《檔案法實施辦法》第3條雖然規定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的永久保管檔案分為一、二、三級管理,但這只是一種管理標準,而非價值等級標準,據此并不能認為國家檔案館館藏的永久保管檔案就是珍貴檔案,其他檔案都是普通檔案。所以,將檔案犯罪的對象限定為珍貴檔案沒有必要性與可行性。
其次,沒有必要增設搶劫檔案罪,非法向外國人出售、贈送檔案罪,走私檔案罪(非法攜運檔案出境罪),擅自提供、抄錄、公布、銷毀國有檔案罪。因為,搶劫檔案的,可以歸屬于非法獲取檔案罪;非法向外國人、外國組織出賣、贈送檔案的,可以歸屬于非法出賣、轉讓檔案罪;走私檔案或者攜運禁止出境的檔案或其復制件出境的,可以按照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擅自提供、抄錄、公布檔案的,可以通過涉密犯罪、信息犯罪(如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等)等予以規制,均沒有單獨設罪的必要。
再次,增設故意毀壞檔案罪。擅自銷毀檔案,侵害了檔案的實體安全,危害性較大,應予犯罪化。以處罰故意犯罪為原則、以處罰過失犯罪為例外是世界各國刑法立法之通例,在檔案犯罪的立法上亦應如此。雖然刑法將故意損毀文物與過失損毀文物都規定為犯罪,但在檔案犯罪立法上應僅限于處罰故意損毀檔案的行為,并且以造成嚴重后果為限,由于過失造成檔案丟失的,不宜以犯罪論處。犯罪構成要件表述為:“故意損毀檔案,造成嚴重后果的,處……”
最后,增設偽造、變造檔案罪。檔案的本質屬性是原始記錄性,檔案的基本價值是情報價值和證據價值,所以,涂改、偽造檔案是一種極為嚴重的破壞檔案真實性的違法行為,必須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由于刑法沒有相關罪名可以適用,司法實踐中曾出現將涂改人事檔案的行為以變造國家機關公文罪定罪處罰的案例,嚴格說來,如此判決并非十分妥當和精準,因為,根據檔案學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檔案與公文是有區別的。關于變造檔案,檔案法中稱為涂改檔案,為了保持刑法用語的統一性,可將檔案法中涂改表述為刑法中變造。犯罪構成要件表述為:“偽造、變造檔案,情節嚴重的,處……”
參考文獻:
[1]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885.
[2]張玉國.論涉檔犯罪行為的對象[J].中國檔案,2006(2):18~19.
[3]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84.
[4]王成玉.論非國有檔案的刑法保護[J].中國檔案,2006(6):16~17.
[5][9]李娜,余翔.論我國刑法中檔案犯罪的立法完善[J].檔案時空,2007(6):8~9.
[6]栗娜,溫軍.我國現行刑法檔案保護中存在的問題[J].中國檔案,2001(10):18~20.
[7]趙秉志.新刑法典的創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19.
[8]廖軍.淺議完善刑法對檔案犯罪的規定[J].人力資源管理,2010(5):1.
[10]牧曉陽.論我國檔案犯罪的立法完善[J].蘭臺世界,2010(18):29~30.
[11]王駿.檔案保護刑事立法中的“三個應當”[J].檔案學通訊,2010(4):76~79.
(作者單位:河南科技大學法學院 來稿日期:2017-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