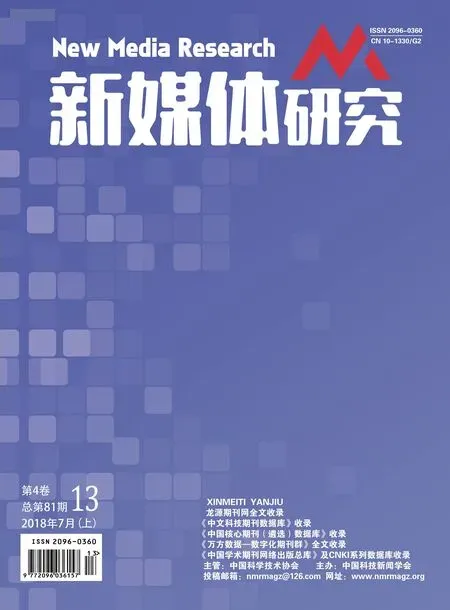益智類電視節目中角色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張玉潔
河北地質職工大學,河北石家莊 050000
摘 要 近年來,益智類電視節目在我國逐步成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形式,并具備了一定的特色,節目中特有的知識性、參與性和互動性越來越受到觀眾的認可,從節目構架而言也呈現出相對穩定的設置,因此,在研究益智類電視節目的傳播效果時,參與者、知識、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就成為了一條途徑,而這一視角的運用便來自于德國學家M·舍勒和美國匹茲堡大學伯·霍爾茨納教授關于知識社會學的闡述。文章結合“知識社會學”中對于參與者、知識、社會三要素的剖析,將節目中的參與者以不同的社會角色進行劃分,并將節目中不同角色具備和呈現的知識進行分類,進而從節目內容的知識性、參與的真實性和互動性等方面探討受眾對于節目內容的興奮點,以及電視節目的權威性和影響力,最終了解觀眾將益智類電視節目視為“營養佳品”的原因所在。
關鍵詞 益智類電視節目;角色研究;知識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7)13-0034-02
1 節目中角色的知識應用與呈現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在媒介技術大發展且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的今天,大規模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成為可能,從而形成“知識密集型社會”,益智類電視節目呈現的內容即為一種高效而密集的信息(知識)從而影響受眾,人們對于獲取到的信息雖然越來越碎片化,但記住的便可稱為一種“知識”,促進人們接下來的生活或工作。
伯·霍爾茨納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將知識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為常識,根據自己的文化所界定的日常現象中的種種定義;第二種為專門化的知識,形式上是經驗的、實際的知識,即通過實際經驗所學到的知識,它與常識一樣都是非正式的;第三種是正規知識,它則包含實用性知識和正規技術性知識,并且有許多不同類型,知識越是正規化就越容易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最后一種是人類社會最正式的、最重要的知識類型——科學調查和科學知識,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科學研究。
在節目的角色劃分上,則可分為主持人、評委(嘉賓)、參賽選手和觀眾四類。這其中能夠利用并展現在受眾面前的“知識”多為前三種:從嘉賓評委的角度來說,這一類角色可以將自身擁有的“正規知識”或者“專門化”知識直接地呈現到節目中,例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耳熟能詳的毛佩琦、酈波、蒙曼、錢文忠等幾位教授對于知識點的講解與點評;對于主持人來說,其角色本身對于知識文化的把握不僅需要自身“專業化知識”作為職業技能將節目的各個環節、各個角色以行云流水的態勢給予聯系和捆綁,更需要日常的積累形成的“常識”對節目中的相關知識進行一定程度的了解;運用知識則相對復雜的應屬選手這一角色,他們除去一些與自己專業或從事的工作相關的題目外,其余更多地需要運用的則是“常識”。
總體而言,益智類電視節目就是通過不同社會角色所掌握的不同知識,將節目中以“知識”作為內容的主題特色表達出來。
2 節目的角色定位與參與關系
從社會學來講,每個社會個體都會因為其所處“位置”的不同,而影響看待問題的視角和方向,這里的“位置”即社會不同成員在社會結構中的“參考系”或者稱為“參考框架”。在益智類電視節目中同樣如此,由于每個角色的節目取向不同、社會所處參考系不同,每個角色所擁有的角色權利和資源是不盡相同的,從而在節目中所呈現的知識狀態也不盡相同,并在這一過程中達到資源共享的效果。
在益智類節目的參考系中相對穩定的角色即為評委(嘉賓),由于他們多位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掌握著大量權威的知識資源,因此充當著專業程度較高的“權威者”的角色,并在角色關系中形成了“資源權利”,當然,他們在被賦予這種“權利”的同時,也承擔著對臺上選手公平評判的責任以及對公眾普及相關知識、提供資源的職責。對于他們所承擔的“角色”并不需要刻意扮演,他們更需要注重的是向觀眾提供權威、全面、有深度的知識。
參賽者在節目中的參與目的和心態相對復雜,一方面是通過角色參與感受自我價值的實現,從而獲得“自我認可”;另一方面則是實現的替代性滿足,從而使自己體驗到“明星崇拜”感,獲得“社會認可”“社會地位”,另外,另外一些參賽者則傾向于對物質獎勵的追求……對于觀眾來說,因參賽者調動的“知識”不明確而缺少權威性,從而資源交換上相對平等,但節目結構這一大的框架下進行分析時,參賽者則更多處于信息資源匱乏的一方。
觀眾作為一個大的群體性角色,大致可以分為現場和“屏幕”觀眾兩種,現場觀眾以顯性互動直接參與到節目中,并為調動現場氣氛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屏幕”觀眾在新媒體的驅動下,呈現著出更為靈活的互動形式,他們開始有機會與節目現場進行看不見的“隱性”互動,由于觀眾社會角色的不確定性,節目觀看心理和目的的紛繁復雜,節目的互動也為此呈現出多樣的形態。
主持人作為一檔節目的“引領者”,在節目中往往承擔著“多面手”的角色。他們在節目開場負責引領觀眾、渲染節目風格與特點;在答題過程中,又或以考官姿態營造緊張氛圍,或以交流的狀態引導選手并及時引導與評委(嘉賓)的平等交流,使節目中的各個角色與各個環節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可以看出,無論是怎樣的互動形式,都存在著“知識互惠”內在運行模式。益智類電視節目就是將“知識”這一資源以游戲互動的模式進行構建,從而使不同角色在節目中獲得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機會,并對既定信息進行共享和交換,形成或推動某種文化熱潮。
3 節目中的文化自覺與自覺參與
所謂“文化自覺”,借用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觀點: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就我國益智類節目而言,近期出現的大批以我國傳統文化為特定領域進行制作的電視節目就受到了廣大觀眾的關注,較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推出的一些列《中國詩詞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謎語大會》等,以及地方臺為觀眾呈現的《中華好詩詞》《成語英雄》《漢字英雄》等,在這些節目中,觀眾在獲取知識之余,感受到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回歸,而且這些節目已然成為了全民參與的文化活動,使中華文化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益智類電視節目在播出的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自覺”的現象表現在觀眾的日常生活中即可視為一種“自覺參與”,無論觀眾是何種動力的驅使,都會或多或少地將自己的注意力投放在與節目相關的文化知識中,或者說,觀眾們在電視節目的參與上發揮著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但要注意的是,雖然益智類電視節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化自覺,但受眾的自覺參與并非完全建立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其參與動機依舊存在著差距,參與方式也多種多樣。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人們通過電視節目傳達和表現的文化自覺,不再僅僅是單線條的傳播與接受,除了時時與場內互動,受眾還可以通過網絡平臺獲取更多的相關信息。例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不僅建立了官方網站,使受眾能夠更全面地了解節目近況,而且定期在微博上普及漢字知識,使關注者能夠長期獲得漢字相關的有效信息,建立長效的知識傳播機制。
從節目的“參與自覺”的角度進行分析,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造星”運動下催生的“明星夢”,他們通過網絡或社會報名等方式成為節目中的一員,這些人也是節目必不可少的元素;第二類為屏前時時互動,這種互動多以短信、微信、“搖一搖”、二維碼等方式進行,且多與商業利益相結合,受眾會為了獎品或支持的選手而積極參與其中;第三類為網絡平臺互動,這種互動對于時效性沒有特定要求,但是可以建立長期互動關系,并且這一自覺的參與會使受眾對節目理念及節目所要傳達的主流思想有更加細致的了解。可以說,受眾在新媒體發展的背景下,能夠更好地發揮主動權,并推進節目內容的改進和創新。
當前各類自制研發的益智類電視節目已經以成熟的姿態呈現在了受眾面前,節目中所體現的知識內核,在多種角色和互動環節設置的相互配合下,開始促動受眾的文化自覺和“自覺參與”。當然,如何將節目內容中對于“知識”的前期預設與后期表達效果更好地貼合并形成更高質量的視聽體驗,在未來的節目制作道路上還面臨著許多問題與挑戰。
參考文獻
[1]孫寶國.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形態學[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2]秦啟文,周永康.角色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3]伯·霍爾茨納.知識社會學[M].傅正元,蔣琦,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4]約翰·菲斯克.電視文化[M].祁阿紅,張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