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旅行中的因與果
所有的悖論都與時間循環類似,迫使我們去思考因果關系。結果能先于其原因出現嗎?當然不可能。按定義來說,這是很明顯的。大衛·休謨(蘇格蘭哲學家)一直說“原因是一件事,只不過這件事之后尾隨著另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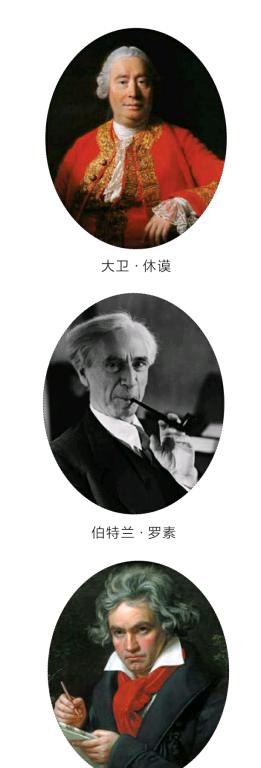
但我們不是很善于搞清原因。有史以來,有文字記載的、試圖通過推理的方式分析因果的第一個人,是亞里士多德。他創造性地為復雜性劃分層次,但其造成的混亂卻一直延續至今。他區分出了四種不同類型的原因,分別被命名為動力因、形式因、質料因和目的因。不管怎樣,我們最好記住這一點:當我們仔細觀察時,沒有什么事物是有一個明確而無可爭辯的起因的。
“關于事實問題的所有推理,似乎都是建立在因果關系上的。”休謨說。但是他發現,推理過程向來十分不易,而且難以確定。太陽是使巖石變暖的原因嗎?侮辱是使一個人憤怒的原因嗎?只有一件事可以說是肯定的:原因是一件事,只不過這件事之后尾隨著另一件事。如果一個結果不一定是由一個原因產生的,那么這個原因到底還是不是一個原因呢?盡管伯特蘭·羅素(20世紀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 在1913年試圖借助現代科學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些爭論一直以來都在哲學大廳的走廊里回響,并且持續到現在。“說來也奇怪,在諸如引力天文學一類的尖端科學中,‘原因一詞從未出現過。”他寫道,“時間對哲學家而言就像程序。事實上,物理學界停止尋找‘原因的原因就在于根本沒有原因這回事。我認為,在哲學家看來,因果律也就是合格而已,它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的遺跡。之所以能夠幸存下來,只是因為它被人們錯誤地認為不會有害。”
羅素已經有了超越牛頓學派的科學觀點。而早在一個世紀前,拉普拉斯(法國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天體力學的集大成者)就已經對此觀點進行了描述——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被嚴格鎖定在一個由物理學定律構成的機制之下。拉普拉斯稱過去為未來的起因。但是,如果這整臺機器都是在步調一致地隆隆前進的話,為什么我們要把任一特定的齒輪或杠桿,想象成比其他任何部分都更具有‘因的特質呢?我們可以認為馬是馬車運動的起因,但這只是偏見。不管你喜歡與否,馬也是完全被決定的。羅素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而且他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當物理學家用數學語言寫下他們的那些定律時,時間是沒有其與生俱來的方向性的。“定律在過去和將來是沒有區別的,”他寫道,“未來‘決定著過去,與過去‘決定著未來有著完全相同的意義。”
“但是我們被告知:你不能改變過去,但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未來。這種觀點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我把目光只停留在了因果律的那些錯誤上,而我的目標似乎就是要把因果律干掉。如果過去已經是那樣了,你就不能讓過去變得不再是它曾經的樣子……如果你已經知道過去是什么樣子,希望它變成另外一副模樣很顯然也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同樣的,對于未來注定要發生的事,你也不能改變它——如果你正好知道未來將要發生什么的話。例如, 對于即將發生的日食
(或月食),盡管你不希望它發生,但就和你希望過去發生改變一樣,是毫無用處的。”
然而,盡管羅素這么說,但科學家還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因果律。休謨是對的,“關于事實問題的所有推理,似乎都是建立在因果關系上的”。往往,我們談論的所有問題,都是因果問題。因果關系線無處不在,有些短,有些長,有些穩固,有些則脆弱,它們看不見摸不著,相互交織在一起,讓人無法逃脫。它們都向著同一個方向運行,那就是,從過去到未來。
比如說,1811年的一天,在波西米亞西北部(今捷克西北部)的特普利采鎮,一個名叫路德維希的男人(譯者注:這里指的是貝多芬,貝多芬全名為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在他筆記本里的五線譜上寫下了一個音符。而到了2011年的一個晚上,一個名為雷切爾的女人在波士頓交響樂大廳吹響了小號,其效果立刻顯現了出來:房間里的空氣以每秒444個循環的主波長振動了起來。誰能否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紙上的筆記造成了兩個世紀后的空氣振動呢?但是,哪怕賦予你拉普拉斯那神話般的“能夠領悟所有力學奧秘的智力”,要想使用物理定律計算出從波希米亞的分子到波士頓的分子的影響路徑,也將是一次極富挑戰性的計算。這里存在的那條完整的因果鏈,是一條信息鏈。
在羅素宣稱因果關系的概念已經是一個過去了的時代的遺跡時,他的話并沒有說完。哲學家和物理學家不僅僅在因果上糾纏不休,他們還在這因果混雜之中增加了新的可能性,逆向因果關系(也被稱為反向因果關系或逆時序因果關系)現在成了他們糾纏的一個主題。邁克爾·杜梅特,英國杰出的邏輯學家、哲學家(也是一位科幻小說讀者),似乎已經于1954年,以他的論文《一個結果能夠先于它的原因嗎?》給這一課題開了頭。10年后,他不再那么躊躇不定,又寫了一
篇《造成過去》。在他提出的眾多問題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假設一個人在收音機上聽到他兒子乘坐的船已經在大西洋沉沒的消息,并向上帝祈禱,祈求他的兒子能夠成為幸存者之一。那么,這個禱告在功能上是否等同于他為兒子的安全而事先進行的祈禱呢?
有什么東西可以激勵現代哲學家反對一切先例和傳統,去思考結果可能先于原因的可能性呢?《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時間旅行。事實上,諸如出生與謀殺一類的所有關于時間旅行的悖論都源于逆向因果關系。
反對因果序(即時間序)的第一個主要論點是,暫時性的逆時間序因果關系是可能的,比如在時間旅行的情況下。這種可能性看起來似乎玄之又玄、深奧難懂,但在法則上是可能的,因為哥德爾證明愛因斯坦的場方程有允許循環路徑存在的解。
“并不是時間旅行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中可能有各種各樣的不和諧,”《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警告說,“包括改變既成事實的不和諧,或者是產生因果循環的不和諧……”而那些勇敢的作家,卻愿意冒著風險,采納這些不和諧。菲利普·K.迪克在其《逆時鐘世界》一書中讓時光倒流,而馬丁·埃米斯在其《時間之箭》一書中也是如此。
我們似乎是在兜圈子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