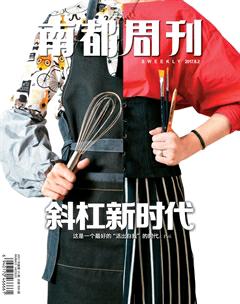醫療“微”革命
沈三
三十年前,微創介入這項新技術引入國內所遭到的冷遇和質疑,一度讓醫學界的先驅者們懷疑是不是因為“中國的病人還是偏保守”。三十多年后,這場醫療界的“革命”在國內掀起新的浪潮,微創介入的本土化發展正釋放出一股“創新沖擊波”。
大門口的“陌生人”
2016年,中國的冠心病介入治療病例突破了66.6萬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微創介入治療大國。心血管介入手術已成為急性心梗患者的天然之選。在患者論壇里,討論“哪一種支架植入效果更好?”的帖子司空見慣。
就在三十多年前,“介入”或者“微創” 治療在歐美方興未艾。但對于剛剛打開國門,重新恢復與外界往來的中國醫學界,卻還是一個陌生的詞匯。
已屆耄耋之年的中國心血管病的泰斗高潤霖院士,當時還是一名年輕的心臟內科醫生。在1984年考取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后,他獲得了赴美進修冠心病介入治療的機會。“在美國一年,大概參加了140多例PTCA(球囊擴張)手術,準備回國以后,在阜外醫院開展這項工作。”
與從赴美“取經”歸國的高潤霖同機抵達的,還有一皮箱“寶貝”。“當時全世界只有USCI、ACS、Cordis等兩三家公司有能力做跟PTCA有關的引導導管、引導鋼絲、球囊等器材,國內完全沒有見過這些‘新式武器,在美學習期間,有些臨床打開以后沒有用上的,或是用過以后仍然保存完好的器械,他們就特意為我留著,美國的護士幫我沖洗、消毒以后,再帶回國。”
1986年9月,帶著一皮箱“寶貝”歸國準備大干一場的高潤霖,卻沒有想到,這種在他看來“效果遠好于當時一般用于冠心病治療的吃藥”的新技術在國內卻遭到了冷遇。“我們每年收治那么多心肌梗死和冠心病病人,按理說都非常適合介入治療。我們就試圖動員,跟病人說這項新技術,病人挺高興,但是一說潛在風險,病人就泄氣了,說還是吃藥吧。”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剛投入臨床應用的球囊擴張術,尚存一定的風險。“因為球囊把病變撕裂擴張以后,管腔就擴大了。有大概3%-6%的病人,由于撕裂創傷過大以后,造成急性閉塞,需要急診搭橋手術。”高潤霖說。
懷著滿腔熱情想要改變心血管病治療現狀的高潤霖,終于在三個月后等來了他的第一例心臟介入治療病人。那是一個40出頭的年輕人,因為發病的年紀尚輕,有強烈的根治意愿,最終促使他接受了這個“冒險”的建議。“他當時心絞痛的癥狀,吃藥效果也不是特別好。而且他的前降支有70%、80%的狹窄,情況非常適合做介入。”
時隔三十年,高潤霖重憶起在手術臺上的點滴細節,仍然如數家珍。“當時根據醫院規定,同臺的還有放射科醫生,外科也從旁待命,一旦出現不良反應就做好心臟搭橋手術的準備。”而在介入手術的關鍵環節,通過球囊給血管加壓的過程中,“我們自己的心跳都要加快,直到球囊抽癟打造影劑,冠狀動脈通了,才放下心來。”
術后的24小時內,他甚至對電話鈴響都噤若寒蟬,“因為閉塞可能發生在24小時之內”。怕什么,來什么,就在24小時的限期將過時,桌上的電話咣當當地響個不停。高潤霖接起電話,“聽說病人沒事,懸著的心才徹底放下來。”
萬事開頭難,回想微創醫療在國內的艱難起步,高潤霖至今頗為感慨,“從第一例到爭取到第二個病人,又過了很長時間,一年中,做了不到十例。發展非常緩慢。”究其原因,他認為,“歸結起來,一是掌握這項技術的醫生當時還很少,第二是器材的供應很有限,第三是病人的接受度還比較低。”
學科邊界的消融
在微創治療開展之初,敏感度高的同行越來越意識到這項新技術廣泛的應用潛力。
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在醫科大學就讀的現北京安貞醫院血管外科主任陳忠教授就是這其中一員,而且他敏銳地感覺到,“一場醫療‘革命山雨欲來。”
陳忠在醫學院就讀及在宣武醫院實習期間追隨的董宗俊教授,也是從北美學習歸來后,最早把血管疾病領域的微創治療引入國內。二十多年過去,陳忠憶起當年初次接觸微創的“神奇”,言談中的興奮絲毫未見褪色。
那個年代外科的概念一定是開大刀,我第一次在臨床上看到了關于微創治療腎動脈狹窄的手術,用一根小小的針(穿刺針)、一根細細的導絲能夠達到人體的內臟深部、達到腎動脈的開口,繼而又通過這根柔順的導絲順入一個球囊,以球囊擴張的方式,把原來腎動脈狹窄得以施治。我當時感到非常驚奇,我想這樣的技術如果能夠得以推廣,將來一定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將會打破,甚至是徹底打破外科的傳統觀念。”
初識微創威力的陳忠,在醫學院畢業后的去向選擇上,做出了一個當年在不少同行看來近乎悖理的決定。他放棄了進入當時風頭正勁的心臟外科,而是選擇了進入冷僻的血管外科。“在那個年代血管外科從事的人員鳳毛麟角,不要說從事的人員,連知道血管科這個概念的人幾乎都很少。”
二十多年過去,他當年的大膽決斷,成了先見之明的力證。血管外科如今的治療領域遠超出傳統心血管疾病的范疇,甚至下肢缺血以及既往必須通過開胸、開腹解決的胸腹主動脈瘤等這一類大動脈頑疾,都可以通過血管外周介入療法而得以治療。在業內,近年來更有著這樣的說法,“血管外周介入的應用,打破了心血管內科與外科的界限,可以解決很多外科解決不了的問題。”
據陳忠介紹,最初微創技術在血管外周領域的應用,起于血管造影。“因為血管造影必須要在血管上做穿刺,通過穿刺以后,順著導絲導管達到相應的部位,然后通過導管末端高壓注射器打入造影劑,X光下才能夠顯影整個血管的影像。這可以說是微創發展之前的雛形,那時候不叫微創治療,而叫微創檢查。”
隨著微創技術及器械的不斷演進,從球囊到支架,再到減容裝置等完備的血管介入器械的出現,“比如說波士頓科學的產品線幾乎覆蓋了所有的血管疾病范疇,像頸動脈疾病、內臟動脈疾病、肢體動脈疾病,甚至包括靜脈疾病等。”陳忠直言,技術及器材的進步,也使得一開始血管介入治療局限于治療狹窄性病變,逐漸發展到治療擴張性病變,乃至動脈瘤等原先只能通過開胸、開腹手術治療的極其兇險的疾病。
“既往對于動脈瘤的治療必須通過開胸或者開腹,甚至有可能需要心臟停跳、停循環,要靠輔助循環的基礎上,才能夠把動脈瘤切除,然后再把一根人造血管,一針一針縫到原來血管的部位,來重建血管的通路。但是,現在隨著微創技術不斷發展和耗材的不斷革新,僅需要通過一個穿刺孔,就是一個相當于比穿刺針眼粗大約六到七個毫米的管路,就可以達到治療的目的。”
正如陳忠當年所料,微創介入的發展使得血管外科變成“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它上可以治療頸動脈,下可以治療下肢,甚至于足趾、末梢。”對于像下肢缺血這樣的疾病,由于其病灶與病源的分離,過去病人甚至常常誤將其當做“腰椎間盤突出”四處尋醫問藥,錯失了最佳治療時機。以至于最后被送到血管外科來的病人,不得不采取傳統的外科手術“三部曲”:第一步取栓、第二步血管搭橋、第三步截肢。“有了微創治療以后,使傳統的‘三部曲得到了根本改變,很多既往根本沒法搭橋的血管,我們可以通過微創治療得以給病人重新保留肢體的希望。”
如果說血管外科的建立,得益于上世紀上半葉抗凝藥物及人工血管的發明;那么,它的救治手段的升級及治療領域的拓展,則要歸功于微創介入的應用。用陳忠的話說,“這是血管外科領域的‘第二次革命。正是由于這次微創技術帶來的革命,我們才跟上了西方發達國家醫療水平發展的步伐”。
被改變的“疾病譜”
微創介入在心血管病及血管外周領域的迅猛發展,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也在消化道、乃至呼吸道疾病的治療領域得以“復制”及擴展。微創的創口小、愈合快的天然優越性,使得它更便于進入腸胃、乃至膽胰等難以通過手術施治的幽深腔內,進行鏡下的診斷與治療。
從八十年代起,就在長海醫院消化內科從事微創介入治療的李兆申教授,最初接觸微創醫學的路徑與心血管外科頗有相似之處,“那時候的介入基本上是一個單純的概念,就是診斷為主。完全沒想到今天介入發展到無所不能、無所不介,這個時代真是遠出乎人們的想象。”
如今看來已經是“小菜一碟”的膽管微創取結石術,患者一般在術后1-2天即可出院,在過去,通過手術的辦法治療,患者的康復期要綿延三個月之久。“因為取出結石后,還需將一個T形管接到患者體外,通過導管引流到掛在體外的袋子。三個月之后,如果造影顯示患者沒結石了,再將導管撥出。這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在冬天問題不大,如果是夏天,還不能洗澡,每天需要換藥,”李兆申直言,“即便是健康人,在經歷這樣一個恢復期后,也要元氣大傷。”
而面對胃癌這樣的惡疾,患者所要承受的治療后創傷,更可能導致終身生活質量的下降。“過去通過手術治療,如果胃的某部分有癌變,整個胃要切掉4/5。先不說腫瘤的影響,切除手術本身就足以對人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隨著近三十年來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化道的惡性腫瘤已位列我國致命疾病的前列(繼排名首位的肺癌之后,二至五位分別是胃癌、肝癌、食管癌和結直腸癌)。且消化道癌癥均有發現晚,五年生存率低的特點。用李兆申的話說,“做了三十多年消化科醫生,感受最深的就是疾病譜發生的改變。”
據中國癌癥中心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消化道癌癥病人的數量在最近的發病率仍為有增無降。單以晚期胃癌而論,每年國家為患者支付的公費醫療數額就高達百億級別。如果通過微創技術及早診斷、治療早期的消化道癌癥,能極大地提高患者五年生存期,且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食管癌、胃癌、結腸癌這三大疾病,如果我們早期發現了病灶,在它很淺很淺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不開刀。我們通過微創介入可以像削蘋果一樣把這個病變給削下來,而且可以做到非常完美,削到以毫米為算,切得非常干凈。”據李兆申介紹,近年來,國家積極推動微創介入在胃癌防治領域的開展,期待早期胃癌的診斷率提高到70%,可以為每個患者省下20萬-30萬元的治療費用。
目前,腫瘤介入領域的微創治療正在成為繼化療、手術治療及藥物治療之外的癌癥治療“第四大療法”。我們相信,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微創介入的應用將更加寬廣、更備受青睞。
創新發展的沖擊波
微創治療在大約三十年時間內所引發的醫療“革命”,用高潤霖院士的話說,“技術上的創新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器械的創新。”
在微創醫學剛剛進入中國時,早期先驅者們的實踐還往往受制于器械的限制,陳忠在回憶血管外周介入領域開拓者們的實踐時,就直言不諱地說,“當時國內還沒有一家公司生產任何一款用于微創介入治療的產品,可以說,在起步階段所使用的耗材,所有東西都是人家國外用過的一次性的廢棄產品,拿回來重新消毒再使用。”
而今,隨著醫療領域政策的進一步開放,越來越多的國際醫療器械公司進入中國,帶來了世界領先的醫療器械。例如全球范圍內微創介入領域的領跑者波士頓科學,近年來以每年50多項的速度加速引進全球領先的微創技術和產品,也正在消弭微創介入在國內外開展的“代差”。
從最早開展心血管病領域的微創治療,一年也等不到幾個病例,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在2016年,我國冠心病介入治療病例數超過66.6萬例,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血管外周領域的介入治療每年也已達“5萬到8萬例”;此外,受益于國家對于消化道腫瘤微創介入的推廣,更使得胃癌的早期治療率提升至70%,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在這背后,則是急劇膨脹的醫療器械市場。據《2016年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發展藍皮書》統計,2016年中國醫療器械市場總規模約為3,700億元,比2015年度增長了約20.1%。《2017中國醫療健康產業投資白皮書》分析,從藥械比來看,目前我國器械市場與醫藥市場的規模比例僅為1:7左右,遠低于全球1:3的水平。從人均醫療技術與醫療器械費用看,我國目前人均費用僅為6美元,而發達國家人均費用都在100 美元以上,美國達到329美元/人,瑞士更是達到513 美元/人。因此,無論從診療方法學,還是從消費水平來衡量,中國醫療技術與器械市場均具備巨大的成長空間。
微創介入術在臨床的廣泛開展,也進一步加速了微創技術的迭代。以心血管病治療領域為例,從微創介入術的出現到其應用于心臟病的臨床治療,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探索;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球囊擴張術的成熟到支架植入的普遍開展,只用了不到二十年。進入新世紀,心臟支架更經歷了從第一代裸金屬支架到第二、第三代藥物洗脫支架、乃至第四代可降解支架的“迭代”式發展。
用高潤霖院士的話說,“當前,介入治療在我們國家的發展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就是發展創新的階段,不僅臨床治療例數的增加非常快,每年的增幅達到了15%-20%,甚至30%;并且在介入的術式和治療方法上都有創新,治療水準上也在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
成立于1979年,專注于微創介入領域產品與技術研發的波士頓科學,進入中國市場也已逾20年,可以說見證了微創介入在中國蓬勃發展的20年。伴隨著行業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騰飛,波士頓科學自2012年以來更不斷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投入,先后在上海成立了創新培訓學院、首個三維互動體驗中心(3D VisLab),不斷加大與本土科研力量的合作,并為國內培養了近萬名掌握最新技術的微創介入治療的醫師。今年,波士頓科學與清華大學合作成立國際健康產業創新中心和創新基金,更為進一步促進高端自主醫療器械的技術創新、產品研發和企業孵化,使得微創介入醫學的發展在中國進入了全新的階段,正釋放出本土化的強大“創新沖擊波”。
“我們始終秉承著創新創業的理念,不斷突破醫療的邊界,為中國的醫師及患者提供高效的醫療解決方案”,波士頓科學北亞區總裁王欣如此解讀,“隨著科技發展、人工智能、數字化醫療等趨勢,醫療器械的發展也將越來越打破邊界,應用到更多疾病領域,惠及更多患者。”
曾以發明“膠囊式內窺鏡”蜚聲國際的李兆申教授,這樣為《南都周刊》的記者暢想微創的未來,“二十多年前,沒有多少人敢想微創介入不僅能用來診斷,而且可以運用于治療,這直接使得開胸、開腹的‘大手術時代正在成為過去,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通過微創的進一步發展,會把內科、外科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進一步消融兩者之間的界限。”
目前,國際微創的發展前沿,不僅向著體內植入的微小化、乃至可降解的方向演進,而且,通過融入大數據乃至人工智能,微創介入可以持續地反饋患者的疾病體征、并對手術的愈后進行實時跟蹤與管理,正在重建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可能改變整個醫療服務的方式和體驗。
過去近三十年“革命性”的發展,讓親歷了這場醫療巨變的參與者,回首過往仍不免驚詫,“在30多年前,我剛走出醫學院校門的時候,決不會想到我未來選擇的外科專業已經不是用刀,而是用導管、用導絲、穿刺針”,面對未來,陳忠則顯得更為豁達,“我們為什么不能想象微創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還會再帶來更加不可想象、翻天覆地的變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