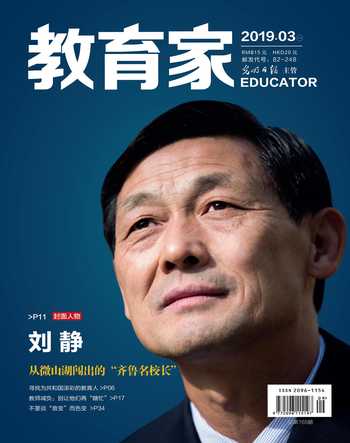從“寫字機器人”談中小學“減負”窘境
楊欣
事件回顧
2019年春節剛過,哈爾濱市張女士發現,正在讀初三的女兒用壓歲錢訂購了一臺價值800多元的“寫字機器人”,它不僅可以模仿孩子的筆跡抄課文、抄生字,還能畫手抄報,女兒的語文作業就是機器人幫著寫的。于是,張女士一怒之下摔碎了“機器人”,還怒罵了女兒一頓。
“減負”二字,說起來簡單,卻一直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大問題。所謂“減負”,就是減少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擔,讓學生可以擁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或者說更多玩耍的時間。“減負”的口號念了十幾年,相關部門出臺的政策也有很多,可學生的負擔卻越來越重,這是為什么?
從哈爾濱張女士的經歷在網絡上流傳開后網友的反應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網友頗具代表性的看法有:“寫字機器人”的誕生是因為現在學生課業負擔太重;不少作業是重復的、機械的甚至無意義的;“寫字機器人”是現在學生用高科技手段“減負”的創舉;孩子們越學越累,除了要做學校的作業,還要面臨父母的“增負”。
初三學生面臨日益高漲的升學壓力,不僅要面對學校沒完沒了的作業和測試,放假回家還要做父母因為“關心”和“擔心”額外增加的重復而又機械的作業,孩子為了應付這些已經掌握或者不重要、不想學的知識,求助諸如“寫字機器人”之類的工具實現自我“減負”,此舉,既解放了自己也滿足了父母。管中窺豹,可見當下中小學“減負”之窘境。
中小學“減負”的突破口在哪
當下,我國政府對“減負”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是罕見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減負”話語就開始頻繁出現于國家重大教育決策與議題之中。不僅幾代最高領導人對此作出過重要批示和講話,而且從教育部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先后出臺過若干的政策文件來解決這一問題。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探索,“減負”工作起到一定成效,但是學生繁重的課業負擔仍未從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有些地方甚至還相當嚴重,仍然是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嚴重障礙。需要看到的是,我國系列“減負”舉措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緩解了學生學習時間長、任務重、難度大等問題,但要以此徹底解決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仍非朝夕之事。其中耐人尋味的是,為什么有關部門出臺了眾多“減負”政策法規之后,學校、家庭給學生“違規增負”的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促進學生生動活潑學習、健康快樂成長”的良苦用心為何遭到部分教師、家長甚至學生的抵制?原因可能有很多,如傳統考試文化、就業壓力、高考指揮棒、過分強調知識傳授的教育方式等。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千百年來形成的考試文化造成了社會與學校都以考試分數來“定乾坤”“排高低”“選人才”。
同時,為了維護社會公平、教育公平,我國中高考也不得不用考試分數作為錄取依據,這導致學生為了取得更好的名次或分數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機械重復學習。為了解決學生課業負擔問題,我國基礎教育在中考、高考評價與錄取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嘗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要徹底解決這一難題仍然需要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的過程。而這就對“減負”提出了新的議題:對當下教師、家長、學生以及其他關注和討論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人而言,如果考試制度不改變,未來“減負”是否可行?它的突破口與著力點在哪?這既是“減負”的問題,也是思考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的一個角度。
應不應該布置重復、機械的作業
那位張女士的女兒之所以用“寫字機器人”完成父母布置的作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作業是重復、機械的抄寫。試想,如果換作一些需要想象力和邏輯推理能力的靈活的作業,寫字機器人還能發揮絲毫作用嗎?答案顯然是不可能。而這也直指當下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核心“痛點”:一些學生為了考出好成績而不得不采用“題海戰術”,通過重復、機械的做題以達到在考試時“快而準”的效果。重復、機械的作業固然令人生厭,但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杜絕布置重復、機械的作業。實際上,這類作業的本質是要讓學生記住知識,更牢固地掌握知識;另一方面,寫得多了,學生答題也自然更快。另外,它何嘗不是我國“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熟能生巧”的文化表征?況且機械、重復也是因人而異的,A覺得機械、重復的內容,可能卻是B學習的基礎和起點。面對上述現實“利益”、學習文化以及個體差異,要真正做到減少或者杜絕重復、機械的作業,豈又是一紙“減負令”可以趕盡殺絕的。
從當下的現實情況來看,最可行的方式是讓學生除了做一些加深記憶和反應的機械、重復作業,是不是可以面向學生的觀察力、想象力、判斷性思維等高級思維方式,布置一些高質量的、具有創新性和挑戰性的作業。
科技是否有助于學生脫離題海
對身處題海的學生而言,科技可否助其脫離苦海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畢竟對21世紀的人而言,科技改變生活已不是一句空話,掃地機器人、做菜機器人、家電類機器人已經走進了人們生活。筆者相信,如果市場足夠大,做題機器人也一定會應運而生。它除了會做這些重復、機械的題,結合當下深度學習的算法,其他類型的題目也將不在話下。畢竟李世石都可以被電腦擊敗,還有多少中小學的題目可以難得住它?但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科技發明在一定程度上會讓學習者變得更加懶惰。所以,筆者有理由相信未來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一定會讓我們的教育發生更大的變革,它既可以在無邊無際的“題海”中通過大數據分析串聯起一座座啟發、引領學生智慧的“知識小島”,也可以通過深度學習成為學生在“題海”中關注新知、記憶內容、反饋效果和掌握規律的“助手”,但它不應成為代替學生嘗試和體驗做題的“替身”——今天有機器替你做題,明天誰能替你生活?
因為擔心和關心,所以必須“增負”?
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的父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共性:因為擔心孩子考不上好學校、找不到好工作,父母會自覺為學生“增負”。換言之,在父母眼中,現在的學生若想在未來的學校和就業競爭中勝出,就必須比別人付出更多。而這造就了當下教育典型的“囚徒困境”:父母也知道給孩子“增負”可能不好,還不得不“增”。因為這是所有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所能采取的壓倒性策略——不管別人的父母怎么做,這個策略對自己來說都是最好的。然而問題是,父母知道自己“增負”的意義嗎?他們能布置出適合自己孩子的作業嗎?他們能給孩子及時、合理的反饋嗎?這樣做是為了緩解父母內心的恐懼,還是真正關心自己的孩子?如果父母沒有想明白這些問題,就簡單粗暴地以“愛的名義”讓孩子從早到晚深陷題海書山之中,是福是禍,亦未可知。
緩解“減負”窘境的思考
上述“減負”問題再次表明,當下不同群體從自身的利益與視角出發圍繞“減負”開展博弈,或許會使得“減負”更加撲朔迷離,從而陷入不斷的爭論與反復窘境之中。筆者結合近五年來對“減負”研究的思考與經驗,認為緩解當下“減負”窘境的可行之徑有:
看見、看清、看懂“減負”
2018年12月29日,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出臺了史上最嚴的《中小學減負措施》(“減負三十條”),再次表達了國家的“減負”決心。筆者認為當下要切實解決這一難題,除了逐步改革考試評價與錄取制度,積極踐行國家“減負”政策和規定,有必要對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落實情況進行評估,讓更多人看見、看清、看懂“減負”,以此為據可以描述、比較和判斷“減負”目標是否達成以及達成效果,加快實現“減負”督導工作的可視化,最終引導學校、家庭、社會以及教育管理部門用事實和數據構筑全新“減負”話語體系和行動共識。
將“減負”視作一項系統工作
根據系統科學的有關規律,如果某個問題具有以下特征,那么它就可能是一個系統問題而非簡單的線性問題:看似小問題,但要解決它要耗費許多資源;多次試圖解決,卻總是無效;問題看似容易解決,但人們故意不解決;不少人對這個問題有情感障礙,試圖避而不談;新人對此高談闊論,老人則是置之一笑;類似問題一再發生,整改了也沒用。顯然,“減負”正是一項完全符合上述特點的系統性教育問題,而非一個可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簡單問題。對待“減負”這樣的系統性問題,筆者認為有“下、中、上”三策:下策是直接命令“減負”;中策是間接刺激,在教育系統中找可以減輕學生壓力和負擔的東西,比如體育運動;上策是尋求新的共識,比如引導學校、家庭、社會對學生成才形成新的共識——除了考試之外,還有其他可以證明自己的機會和途徑。
“減負”≠減壓縮時+快樂學習
當我們放眼世界時,可能會發現關于“減負”的另一番景象。美國的主流文化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清教徒文化,他們高度重視教育。美國中產階級的主流觀點是一個人要想獲得和保持中產階級的地位首先就要重視教育,而且在教育中強調個人奮斗。美國人認為,上帝對兩種人是加以獎勵的,一種是出生就有好的稟賦,另一種是后天勤奮。而且不少西方發達國家從國際學生成就測評中吸取經驗,不斷提高學術標準,追求學術卓越,緊鑼密鼓地為中小學生“增負”。對這些國外學生而言,快樂是學習過程中的體驗,可能并非追求的終極目的。
當下,盡管不知“減負”路在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減負”≠減壓縮時+快樂學習。因為無論把學習的壓力和時間減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保證學生學得更好;即便讓學生天天開心得像百靈鳥一樣,他們也無法從中獲得知識、能力和成長,這樣的學習又有意義了?難道真的要像尼爾·波茲曼說的那樣“娛樂至死”?
“減負”路漫漫,期盼更多人上下求索。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
責任編輯:楊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