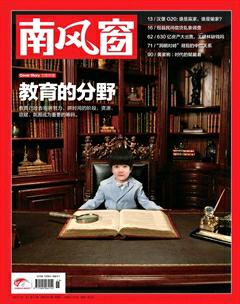為什么我們要談“理解中國”
孫信茹
最近,我認識的一個社會學研究者以70后的身份,作為一個“入門級玩家”,加入了“王者榮耀”的游戲,試圖觀察這個屬于90后、00后的游戲世界。
最終,他完成了《一個社會學者關(guān)于王者榮耀的體驗式觀察》一文。文章很快成為朋友圈的熱文。我的一個學生看了,迫不及待告訴我,她發(fā)現(xiàn)社會學真是個有趣的學科,可以從生活里找到那么多的研究話題。她說,感覺這才是真正的理解中國啊 。
這個學生的感觸讓我有深深的共鳴。事實上,“理解中國”,在今年上半年成了我的關(guān)鍵詞。當然,如何看待中國、如何談?wù)撐覀兯畹倪@片土地,似乎每個人都能說上幾句。可是,要說真正的“理解”和深度的觀察,未必人人都能說得出所以然來了。
我所在的學校云南大學,從2016年開始,就醞釀著以“理解中國”為主題的系列活動,目的就是要把可能人所周知的現(xiàn)實和問題擺出來,說出個所以然。今年年初,我也成了這個“理解中國”團隊中的一員。
我向來不甚熱心這種官方色彩頗為濃厚的活動。當然這還有另一個原因,我看很多問題總是習慣于先從自己的理解和感觸入手,也更多從個體和微觀的生活角度來介入對某些社會問題和現(xiàn)象的討論。

何為“理解”中國?如何理解中國?我總覺得這是和每個個體體驗相關(guān),也必須依托于每個體的活動去完成的。所以,理解中國,于我而言,更多應(yīng)該是通過有著充分主體性的個人行動與實踐去積極完成的,而不需學校采取這種大張旗鼓的方式組織學生們完成。
可是,沒想到,在這個過程中,我很快有了不少觸動和共鳴。我看到身邊不少雖然獨立、滿是個性,但不免缺乏共同關(guān)懷,也對公共事務(wù)不甚感興趣的青年學生;我會想起自己常和學生說的一句話:今天我們的年輕人是不是可以少談一些風花雪月,多有一些社會關(guān)切。我意識到,對于年輕人來說,對中國社會和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和理解,或許真的是一個需要去直面并且鄭重提出的問題。這種期待,在“理解中國”的活動中得到了回應(yīng)。
如何“理解中國”
記得云南大學剛剛開始舉辦“理解中國”系列活動的時候,很多人表示認同,但卻未必對其要表達的深意有所了解。
具體來說,這一活動的推出正是看到了當今中國飛速發(fā)展,青年人面對鋪天蓋地的資訊內(nèi)容和無所不在的信息通道,但是,紛繁復(fù)雜的信息世界并不足以引導(dǎo)青年人正確認知我們國家所具有的復(fù)雜性。
正如這個活動的策劃者王啟梁教授所說:青年人全面理解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的意義就在于,只有理解,才會認同,只有認同,才能熱愛,只有熱愛,才會自覺用行動去展開實踐,當然,也才能更準確地定位自身。因此,對于廣大青年來說,跳出小我,如何以大格局的視角,多元立體的方式去認識、理解中國,確定人生目標及方向,是一個值得關(guān)注和思索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云南大學經(jīng)過充分醞釀,針對青年學生成長成才的規(guī)律和重要環(huán)節(jié),推出了針對全校學生的“理解中國”系列計劃。這一計劃包括了閱讀、高端學術(shù)報告、社會觀察、社會調(diào)研、公益實踐、學生論壇等環(huán)節(jié)。
我想起在這個系列活動的高端學術(shù)講壇中,我國著名的“三農(nóng)”問題研究專家賀雪峰侃侃而談對中國鄉(xiāng)村問題的復(fù)雜性、農(nóng)村養(yǎng)老等問題時,現(xiàn)場爆棚,學生們急切參與和積極討論的場景。我感受到,今天的青年人也許并非不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一些時候,他們的冷漠或茫然,興許是因為不知道從何處入手去理解中國,并以什么樣的一種方式去討論今天的中國。而大家的學術(shù)講座,無疑是一種很好的啟迪與引領(lǐng)方式。
我也想起我的一個學生在深入社會現(xiàn)實進行觀察時,把視角對準了自己的外婆,講那一代人如何在風雨飄搖中命運的不可知,同時,也關(guān)照家-國-個人之間的互動。讀來很感動,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理解中國的方式。
“他們”的理解中國
事實上,“理解中國”并非只是今天年輕人所面對的命題。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筆下的那個開弦弓村就是他眼中的中國,所以他才會在前言中寫下這樣的話:“同大多數(shù)中國農(nóng)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jīng)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遷過程。”
同樣是社會學家的林耀華先生,卻用小說的筆調(diào)寫就《金翼》的經(jīng)典。書中為我們展示福建一個小山村里毗鄰的兩戶人家的命運跌宕。黃家人的命運改變,也是他眼中的中國。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中,一些從海外學成歸國的學者和國內(nèi)一些有識之士深入民間,脫下西裝,穿上草鞋,紛紛投身當時破敗凋敝的農(nóng)村。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人的“致之”精神在這種情境下得以彰顯,這也是他們努力去理解和接近真正中國的方式。
這種理解,是通過自身的實踐、親身參與來完成的。其中,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改造者梁漱溟一生用心于兩大問題: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他自己曾在回憶錄中說,他的家庭,從曾祖父、祖父、父親,到自己,都是生活在城市中,從沒有在鄉(xiāng)村生活的經(jīng)歷。但自己怎么就去搞鄉(xiāng)村建設(shè)呢?
從他的中學時代開始,這個念頭就開始萌生。在讀書的時候,他就很關(guān)心國事。在閱讀中,他感受到,要改造中國政治,必須從基礎(chǔ)做起,從基礎(chǔ)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xiāng)村的自治。就是基于這樣一種想法,一場滿懷激情與理想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開始了。當年才20歲出頭的梁漱溟,鄉(xiāng)建運動成了他此后十年思考自己人生和中國的核心。
時間流逝、風云變遷,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命題。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著名學者曹錦清深入河南地區(qū)做調(diào)查,他認為,觀察轉(zhuǎn)型中的中國社會,可有兩種不同的“視點”。第一種是“從外向內(nèi)看”和“從上往下看”,第二種是“從內(nèi)向外看”和“從下往上看”。而中國的中原鄉(xiāng)村社會是“向內(nèi)、向下看”的理想場所。
于是,作者以私人身份“察訪”中原大地,進入到他的“調(diào)查現(xiàn)場”,而后根據(jù)調(diào)查目的獲取所需的“社會事實”。
在這個過程中,他得以思考兩大問題: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國小農(nóng)問題;地方政府與農(nóng)民關(guān)系。社會學家吳飛將我國華北某縣自殺現(xiàn)象當作自己田野調(diào)查的對象,試圖告訴我們,中國農(nóng)村的年輕婦女和老人們的自殺,經(jīng)常是家庭中的委屈造成的,自殺成了他們追求正義的方式。《浮生取義》專著的誕生被哈佛人類學教授認為是全球范圍內(nèi)迄今為止關(guān)于自殺問題最認真的田野調(diào)查,也是涂爾干以來最優(yōu)秀的自殺研究。
然而,可能一般的讀者無從知曉,吳飛關(guān)于自殺的討論和研究的思想根源卻來自于姥姥。當他不斷品味姥姥講給他的那些事情和道理時,“過日子”這個詞就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最終,他決定把這個詞當作理解自殺問題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為它能使人們更好的理解這些普通人的生與死。吳飛自己覺得,如果沒有多年來讀書的經(jīng)驗和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還是很難顯露出來的。
生長于斯的這些研究者,對于中國的理解,恰恰是從自己早已熟悉甚至是熟視無睹的日常中發(fā)現(xiàn)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有價值,因為它們回應(yīng)的都是不同社會情境下人們所面對的共同性問題。而一些我們文化的“他者”,也用他們獨特的視角在理解著中國。
我想起那個取了個中文名字的美國人何偉,在中國考取了駕照后,用了7年時間,駕車漫游于中國的鄉(xiāng)村與城市,開始自己的“尋路中國”。他的筆下,呈現(xiàn)出了1996年到2007年的中國社會,這正好是中國歷史上經(jīng)濟實現(xiàn)騰飛,中國對外部世界影響力開始增強的關(guān)鍵十年。這個老外的觀察頗為新鮮,從在中國考駕照、上路、路遇各種類型的中國人等細節(jié)入手。不少記述,讓我這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都不免莞爾。
對于汽車飛速發(fā)展起來,司機開始大量增加的那個時期,他這樣描述到:“人們怎么走路,就怎么開車。他們喜歡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總是緊緊跟在別的車輛后面。”“每當交通擁堵時,他們喜歡從邊上擠過去,跟他們排隊買票時的做法如出一轍。收費站也可能十分危險,因為多年排隊的經(jīng)驗,使人們形成習慣,總在不斷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選擇,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斷。駛進收費站時,駕駛員們喜歡在最后一刻變換車道,因此事故頻發(fā)。”
這些話,讓我即便讀過多年也難以忘懷。
今天,我們?yōu)槭裁匆劺斫庵袊?/p>
或許有人會說,他們那些理解中國的方式,普通人難以相比,那是學者和記者本就該干的事。也可能有人說,今天的時代變了,我們和中國、社會的對話方式早已經(jīng)發(fā)生了改變。的確,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什么都在改變,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本身了。
然而,在這個無所不變的時代,有一些東西,或許是并未發(fā)生改變的。譬如,個人敏感的生命體驗和自我審視、理想與追求、現(xiàn)實對個人的束縛及其對人所造成的困境等,是每個時代中的個人都將要面對的永恒話題。因此,盡管時代在變,個體的獨特性和遭遇也天差地別,但是,那些關(guān)乎個人的問題,卻終將一直存在著。
我們當然不能指望今天的年輕人都像當年的梁漱溟、晏陽初等人那般深入到鄉(xiāng)村,用自己的身體真誠地和土地、農(nóng)民擁抱,我們也不可能期盼著今天的年輕人很快就能發(fā)表出學者們那樣振聾發(fā)聵的研究與警醒。可當我們發(fā)現(xiàn)今天一些年輕人陷入到了所謂“軟世代”中(用南風窗記者李少威的話說,這些“軟世代”對文明的再生產(chǎn)毫無興趣,對社會尚待改進的制度或思想缺陷一無所知)的時候,當我們看到那么多的年輕人宅在家中,成為新時代的空巢青年時,即便我們放低標準,不期望這些年輕人身體力行或是做些還有點深度的思考,哪怕只是偶爾抬起頭,關(guān)注一下這個社會和他人,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最起碼的期待也可能成了奢望。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理解中國,盡管可能是極其宏大的命題,但是,卻又是那樣的和個體的活動與生命息息相關(guān)。理解中國,更需要年輕人參與進來。
我又想到了南風窗已經(jīng)持續(xù)多年的“調(diào)研中國”活動,這是一項專門資助大學生的社會調(diào)查活動。我看到在今年的入選團隊中,主要議題涉及到:文化遺址修繕調(diào)查、特殊教育模式的研究、鄂倫春族樺樹皮工藝傳承及生存現(xiàn)狀、農(nóng)村留守婦女、民宿的法律問題與監(jiān)管、共享單車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冬蟲夏草采集對農(nóng)牧民消費行為影響分析、老齡化與老人社區(qū)參與、城中村回遷村民的后續(xù)發(fā)展能力、網(wǎng)絡(luò)食品安全、農(nóng)村法律援助、云南獨龍族文面女生存狀況、紅嘴鷗與滇池濕地保護、農(nóng)村淘寶服務(wù)站電商平臺的調(diào)研等。這些問題,莫不是今日中國社會面對的最真實和極有代表性的問題。
因此,和理解中國這個命題提出一樣重要的是,今天的青年人如何去理解中國?以什么樣的方式去接近最真實的那個社會現(xiàn)實。在我的認識中,“理解中國”,至少應(yīng)該有這樣的三個部分:閱讀中國、調(diào)研中國、對話中國。
閱讀中國,來自于每個個人扎實和豐滿的閱讀。在這個經(jīng)典、厚重閱讀已不太盛行的年代,在今天大學校園里充斥著各類實用培訓和考證補習班的時代。低下頭來,翻翻那些可能已經(jīng)久遠的書籍,和書里描述的世界與想象空間來一趟親密旅程,形成個人思考的框架和理念,從而理解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和社會。
調(diào)研中國,今天的機遇與開放性為年輕人提供了接近中國現(xiàn)實的無數(shù)機會。年輕人既可以參與到各類機構(gòu)組織的調(diào)研與社會實踐活動中,在一些特定的主題引導(dǎo)下,去關(guān)注某個特定的區(qū)域、人群或問題。當然,年輕人也可以帶著自己的眼睛,回到家鄉(xiāng),回到熟悉的日常中,發(fā)現(xiàn)那些既是常識卻又異常重要的現(xiàn)象。
對話中國,既是自己與大師的對話,也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和大師的對話,最為便利的一個方式就是傾聽大師的聲音和討論,各類學術(shù)講座實則是我們和大師近距離接觸的最佳方式。而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則是竭盡一切,將自己的觀察、閱讀付諸筆端。
懷抱一顆真誠與充滿熱情的心,不斷地閱讀、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書寫。今日的青年人,都應(yīng)該努力追求自己理解中國的獨特方式與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