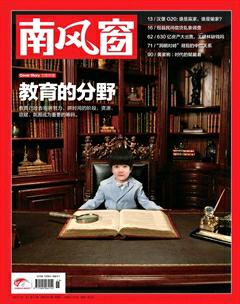世界告別多邊主義?
雷墨
G20峰會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世界主要大國不能達成共識的聲明。7月7日至8日德國漢堡G20峰會發布的聯合聲明,以“我們注意到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這樣的表述,承認了在這個議題上美國與其他19個成員之間的分歧。
作為一種國際治理平臺,G20峰會的誕生與運行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國際社會對某些議題是有共識的,至少是面臨共同挑戰的。2008年首次G20峰會,初衷就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此后歷次G20峰會關注內容不斷擴大,從金融監管、貿易投資、產能過剩到難民危機、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共識”的理念是支撐這個平臺運作的基石。
作為G20峰會的發起國,美國似乎正在削弱這一多邊合作框架,如果不是瓦解的話。
“世界并不是一個‘國際社會,而是一個各自國家、非政府力量和企業彼此對弈、爭奪優勢的競技場。”這是今年5月,特朗普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和高級經濟顧問加里·科恩,在《華爾街日報》上聯合署名文章中的觀點。這兩位是特朗普身邊的高參,也屬于核心決策圈成員。他們的“國際觀”絕不會是個人觀點。
從這一觀點可以看出,首先,特朗普政府根本就不承認國際社會的“存在”,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G20峰會這樣的多邊協作平臺存在的“合法性”。其次,國家間的利益從根本上是競爭性甚至是沖突性的,這就弱化了多邊平臺下合作的“必要性”。
這兩點導出的結論必將是,特朗普不會是奧巴馬那樣的多邊主義者,也不會是布什那樣的單邊主義者,他信奉的是雙邊主義。特朗普會以雙邊的視角來看待問題,比如解決敘利亞危機需要與俄羅斯打交道。他會以雙邊的視角選擇交往對象國,比如與中國交往能在朝核問題上得到什么好處,在經貿領域要做出何種讓步。
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動機的商界邏輯,本能地會更傾向于雙邊主義,而不是“利益均沾”的多邊主義。作為已年屆七旬的商人,特朗普鐘情于雙邊不會只是個人意愿,而是個人本能和不太可能改變的個人世界觀。
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在其《創世親歷記》中,詳細描述了二戰后美國如何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創立了以聯合國、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為支柱的戰后國際秩序。創立這個國際秩序最初的動力,來源于羅斯福總統的多邊主義。因為他清楚,國際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多邊協調與合作。
特朗普對包括聯合國在內國際機構不感興趣,對北約這樣的多邊同盟滿腹牢騷,都與他的雙邊情節不無關系。究其實質,無論戰后國際秩序如何演變,多邊主義依然是各方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正是基于這個原因,特朗普的外交引發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否正在解體的討論。這些討論在西方盟友中更是導致了恐慌。
但“美國版”國際秩序的解體,與多邊主義消失不能劃等號。如果把戰后國際秩序比作一家公司,作為創業者的美國,曾經是擁有絕對控股權的董事長。不過,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這個體系內的持股人變多了,美國這位董事長的股權被稀釋了,絕對控股壓力越來越大。
股權占比降低了,利潤分成就少了。特朗普的選擇是“消極怠工”,把主要精力放在讓美國再次強大這份“自留地”上。但美國的再次強大,不可能獨立于全球經濟體系。這個體系的維系和運轉,也不可能基于點對點的雙邊邏輯。
德國漢堡G20峰會召開前一天,歐盟與日本高調宣布就自貿協定達成協議。這不僅是對國際多邊主義的背書,也傳遞了對特朗普政府摒棄多邊主義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