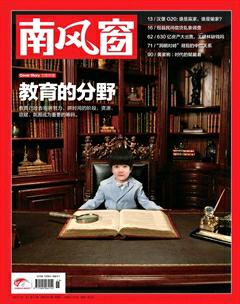誰在村莊?
陳莉莉
他遞過來一張金光閃閃的名片,在他說了“最不喜歡和喝墨水的人打交道”以后。
他是一個線路車司機,嚴格地來說是靠著線路車的生計有了30萬元以上的自有車輛、烏魯木齊市內有兩套房產的生意人。
他把我和攝影記者從采訪地點接出來,跑了三百公里后到了烏魯木齊。他認為我不應該去采訪村莊里的“文化外來人”,而應該采訪他們這些從村莊里走出來的人。
為什么?
“那些畫畫的,有什么意思呢?”他問。我說,不止畫畫,還有寫字的。因為正是有了他們,更多的人才有機會了解新疆、知道新疆,后人們也才有可能知道這個時間里的新疆是什么樣子。
他問我,現在有幾個人還在看書?他以他自己為例,他說他已經10多年沒有看過書了。所以,有什么意義呢?
我對他的疑問一時有點惶恐,雖然我知道他僅是個案,但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個案?哪個地方出了什么樣的問題?作為大眾傳播中的一個環節,我們有意去做一些“大文化”的報道,并試圖去發現文化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它自我繁衍生息的業態,以及它對人心靈的影響。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是我們出了問題?還是社會環境使然?不管是什么,解決之道在哪里?
隨著交談,稍放下心來。
實際上他的問題并不是真的認為與新疆有關的文化行為在歷史發展的橫向、縱向中沒有用,而是“每次去拉客人,他們都要講價,有時從烏魯木齊給他們捎文件,就給20塊錢”,讓他覺得掙得少了,還有點像快遞,不免寒酸了些。
他認為他們應該像他一樣,把時間放在如何努力地掙錢上。他說他渴望去北京、上海、廣州這樣快節奏的城市,每個人都很忙,而且會認為每做一件事情要有成本、利潤的規劃,而不是沒有計較。比如他會偶爾給朋友們提供交通發票上的便利,當然是要收費的,如果自己村里人肯定不會掙這份錢,而是會說“好嘛,好嘛,拿去嘛!”
在他眼中,那些與他同樣出身的人們,不知道像他一樣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

在他出生地的鄉鄰村莊菜籽溝采訪時,我遇見的村民帶給我的感觸是另一番景象。
那位郭姓村民的遷疆始祖是他爺爺的父親,他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兩個兒子讀書走了出去,分別工作在縣城的郵局和醫院。他剛升級成為爺爺。
那種人生收獲的喜悅讓他停下拖拉機,站在路邊跟我們聊天,把我們讓進院子里,看小雞生長,聽樹苗拔節。
這個縫隙里,他講了一段近百年的歷史。爺爺的父親清代末期從甘肅到新疆,落腳叫菜籽溝。先輩們先后離去,住到那邊去了,他指著不遠處的山溝,那里有“郭家墳”,他說他將來也要住到那里去。
他對自己的一生很清楚,從哪里去,到哪里去,中間在人世間做些什么。對這一眼望到歸處的人生,他坦然得要命。如果不是同行者提醒,我沒認為他指向的地方意味著他從這個世間消失、死亡。
這樣的觸動也曾帶給劉亮程,是他在這個都是漢族人的新疆村莊建立書院的原因之一。他說他注意到這個村莊“只有出,沒有進”,但是人與萬物共生的那種自然又吸引了他,所以他與一些藝術家朋友在這里創作、傳播、生活。
有一個問題是,村莊里現在沒有年輕人,將來呢?將來誰在村莊里?等老人們陸續走了以后,等劉亮程和他藝術家朋友與村莊的合同到期后。有人會說,沒有人會問梭羅,多年以后瓦爾登湖附近會怎么樣,有人會說這是自然規律,這是各自的命運,誰都改變不了。
社會劇變中,這個村莊的現狀以及面臨的問題不是個案。農耕文明期間村莊里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在村莊里得到解決,后來需要與政府共同來解決,現在則需要第三方有機組織進行切實有效的路徑探索。
不管怎樣,村莊真正的主人還是村民,需要村民意識以及價值觀的覺醒,需要他們對村莊的認同。當然,前提是社會、政府以及村莊要有村民覺醒以及認同的氛圍和環境,需要社會和政府也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