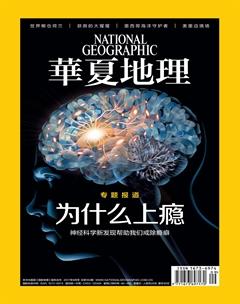海洋的守護者
埃里克·萬斯

一名游客在圣伊格納西奧湖從船上將手伸入水中,希望能觸摸到時常來海灣交配并撫育后代的眾多灰鯨中的一只。漁民曾經很懼怕它們,如今這種出奇友好的動物已經成了當地一個重要的經濟來源。

一位自由潛水者與一群六帶鲹在普爾莫角附近的加利福尼亞灣水域暢游。自從海灣唯一的珊瑚礁成了一片禁漁區,這里的生物量增長了兩三倍。

一只大白鯊在距離下加利福尼亞海岸260公里的瓜達盧佩島生物圈保護區中游曳。作為世界上僅有的兩處有大白鯊聚集的清澈海域之一,它吸引著具有冒險精神的潛水者紛紛前往。下加利福尼亞的生態旅游為墨西哥帶來了億萬美元的收入。
距離日出還有半個小時,濃墨般的海水拍打著沙灘。十幾個漁民正懶散地坐在彭塔阿部瑞歐荷斯的船主辦公室里,一邊大笑一邊談論著他們將在當晚舉辦的派對。
這座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半島中部的小村莊里彌漫著過節似的氣氛,人們盼這天已經盼了一整年——鮑魚季開始了。實際上早在四個月前鮑魚季就到了,但彭塔阿部瑞歐荷斯遵守著一項不同尋常的自我禁令。按照政府規定1月份就可以開始捕撈鮑魚了,但這個社區卻寧愿等到4月,當鮑魚長得更大時才開始捕撈。
我和三位五十來歲的漁民一起向太平洋進發,他們從少年時就在一起干活了。“馬”發動引擎,“鼴鼠”負責把鮑魚拖上船,自然的,“魚”是潛水員。
“魚”一路情緒高昂——他剛從加州的圓石灘回來,他在那兒玩沖浪,打高爾夫球。他穿上嶄新的潛水衣。到達捕撈地點前,“馬”將船停在一片聚滿鮑魚的礁石上方。“這些是綠鮑。”“鼴鼠”說,“得再過一個月才能撈。”
又開了幾公里后,“魚”躍入水中。不出兩小時他就帶著微笑和一整袋健康的鮑魚回到船上。在墨西哥大多數漁業城市,和他們一樣的人靠著從資源耗盡的海水里捕撈少許漁獲勉強維生。是什么讓這些人如此樂觀?他們怎么能買得起新工具,能在精英高爾夫球場度假?
城里的漁會成立于1948年,多年來都像其他漁會一樣經營——盡可能多地從大海中捕撈。但20世紀70年代,幾次讓人失望的捕撈后,漁民們決定嘗試些新方法。他們要對龍蝦(接著是鮑魚)做長遠打算,而不是只看眼前的利潤。
如今,阿部瑞歐荷斯和幾個理念相同的下加利福尼亞社區用同樣的策略捕撈著墨西哥90%的鮑魚。阿部瑞歐荷斯的房子是新刷的。城里有一支棒球隊和一支沖浪隊。龍蝦和鮑魚在一家現代化加工廠罐裝后直接銷往亞洲,賺取最大的利潤。這里的水域有雷達、船只和飛機監管。退休漁民能夠領取養老金。

奧克塔維奧·阿布爾托在加利福尼亞灣的圣靈島附近潛水。這位海洋生物學家正在研究為何有些保護區取得了成功有些卻失敗了。他發現秘密就存在于周邊的社區當中。“要讓人們開始產生自豪感。”他說,“這是生態恢復的保障。”
他們獲得的成功在67歲的薩卡里亞斯·蘇尼加身上得到了最清楚的體現。他的父親參與了漁會的建立,但仍舊要為每天的漁獲操勞。蘇尼加在罐頭廠擔任車間工人。得益于漁會提供的大學獎學金,他的兒子現在成了一位計算機科學教授。
“我們都干活,同時我們也都是老板。”他說。
縱觀全球,魚類的數量正急劇下降,金槍魚、海龜和石斑魚持續不斷地減少。然而,在墨西哥西北部,一些社區已經在著手保護他們的水下資源。這些微型保護區是由社區直接創建或是在社區支持下建立的,許多環保人士將其視作有效環保的關鍵。他們的做法為全世界的漁業社區提供了范本。
下加利福尼亞的漁業發展史就是一部寫滿興衰的傳奇。作家約翰·斯坦貝克在1940年抵達半島時,曾對這里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多樣性驚嘆不已——大群的蝠鲼,成片的珍珠貝,還有數不勝數的烏龜,以至于這里的老人說你可以踩著龜殼穿越大海。但不出幾十年,人類就將大量的野生牡蠣一掃而光。接著人們的目光轉向了海龜、金槍魚、鯊魚、石斑魚和其他十幾種海洋生物。
墨西哥政府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一直鼓勵失業工人改行當漁民。在下加利福尼亞南部,一種自給自足的孤身牛仔文化應運而生。

一群侏儒蝠鲼在埃斯皮里圖桑托島附近吞食浮游生物,這里曾是鯊魚和鰩的聚集地。上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對海鮮的需求暴增,它們的數目驟減。自那時起,得益于地方環保工作的努力,許多魚群都已復蘇。
“人們習慣了靠一己之力單打獨斗。”海洋生物學家奧克塔維奧·阿布爾托說,他研究下加利福尼亞的漁業已經有20年了。“他們從來不指望政府。”
新聞工作者要保持超脫淡定的心態。但當一頭年幼的鯨湊到你的船邊張開嘴,似乎是在求撫摸,就不是保持距離的時候了。
然而經過數十年的過度捕撈,該地區某些特定物種出現了危機,漁民為了追逐所剩不多的魚群只得不停搬家。一些地方的小社區開始想辦法保護他們的資源。最終他們的理念傳播開來。
這些分散的成功故事表明,可持續的、以社區為依托的海洋管理有五個重要法則。首先,和阿部瑞歐荷斯一樣,如果保護區相對偏遠,只有一兩個社區捕撈,事情就更容易。第二,社區需要有高價值的資源,例如龍蝦或鮑魚。能力強、有遠見的社區領導是第三個必備因素。第四,資源恢復時漁民要有其他生存途徑。最后,整個社區要彼此信任團結一致。
下加利福尼亞除阿部瑞歐荷斯之外的其他一些社區說明了這些法則的重要性。在海岸線上向南約30公里處的圣伊格納西奧湖,有種高價值資源的杰出典范不但可以看到,還可以摸到。
根據當地傳說,1972年弗朗西斯科·“小帕科”·馬約拉爾正在潟湖中他經常前往的地點捕魚。和該地區的其他漁民一樣,他用船槳敲擊船身來驅趕靠得太近的灰鯨。在每個人的心目中,灰鯨都是種危險的生物,能將船咬成兩段。沒過多久,有一只灰鯨朝他游過來。他要么是好奇心太盛,要么是膽子夠大,不過出于某種莫名的原因,馬約拉爾伸出手去摸了摸它。灰鯨湊過來,讓他輕撫柔軟而富有彈性的皮膚。那一刻起,一項產業誕生了。上世紀80年代末,馬約拉爾和其他漁民帶領大批游客前去觀鯨。
如今觀鯨已經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經濟活動,生態旅游的小屋在海岸線上星羅棋布。令人吃驚的是,灰鯨和它們的幼鯨依然會湊到船跟前,沒人知道這是為什么。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當地人對這項產業實施管理的方式。在南部的馬格達萊納海灣,導游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帶游客逐鯨,但在圣伊格納西奧湖卻不同,當地將水上的船只數控制在16艘左右。觀鯨季是不允許在潟湖中捕魚的,鯨群因此獲得了更加平靜安寧的環境。
對這片天然港灣的保護不僅僅保護了鯨群,也保護了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繁育棲息的重要場所。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三菱試圖在潟湖入海口建立一座制鹽場,社區組織了一場激烈的運動來阻止該項目,最終大獲成功。
我和游客一起前往海灣,希望能有一場撫摸鯨的奇特體驗。把我們帶到水面上的漁民羅伯托 · 費舍爾警告說能不能摸到甚至看到鯨都不一定。必須是它們選擇接近我們,我們不得追趕它們。幾百米遠的地方,一名社區雇傭的監察員盯著我們,以確保我們遵守規定。突然一股鯨背噴出的水柱出現了,令船上的人們激動不已。
“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嗎?”一名游客喊道。一只當了媽媽的灰鯨羞怯地前來打探我們。它的幼崽則沒有那么羞怯,很快從船的另一側冒出來,游客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臂。鯨媽媽加入進來,另外一頭鯨也參與了一小會兒。
“簡直是一鍋鯨魚湯。” 費舍爾說。新聞工作者要保持超脫淡定的心態。但當一頭年幼的鯨湊到你的船邊張開嘴,似乎是在求撫摸,就不是保持距離的時候了。我伸出手摸了摸它柔軟又凹凸不平的皮膚,然后竟然還摸到了它的舌頭,這太不同尋常了。
保護下加利福尼亞的海洋
海洋環境保護主義者常把加利福尼亞灣稱作“世界的水族館”,但過度捕撈已經威脅到它引以為傲的生物多樣性和生物量。如今當地社區與非營利組織和墨西哥政府合作,保護現有物種。


如今這些動物在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南端西南方約400公里處太平洋上的勒維拉格吉多群島生物圈保護區一類地方的旅游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潛水者能看到蝠鲼如何靠塞拉里昂刺蝶魚清潔身體。
下加利福尼亞周邊海域在上世紀40年代曾經非常繁盛,上了年歲的人說你可以踩著龜背過海。但短短幾十年后,人們就發現資源有限了。

海洋生物在下加利福尼亞的歷史中占有顯著地位。西班牙統治之前的文明在圣弗蘭西斯科山脈的偏遠峽谷中描繪出鰩、鯊魚、海豚、金槍魚和海豹。

在瓜達盧佩島附近,一只北象海豹幼崽窺視著相機,其他年幼的海豹在附近玩耍。保護區創造出一片庇護所,讓曾經瀕臨滅絕的物種得以復蘇。如何最大程度地恢復物種的數量是今天海洋保護區面臨的關鍵問題。

下加利福尼亞的社區居民采取各種策略利用海洋資源謀生。他們有些依靠旅游業,包括一位曾經在馬格達萊納海灣帶領游客觀賞鯊魚、鯨和鵜鶘下水捕魚的前漁民。

馬格達萊納因為環保不力吃了苦頭,但北方彭塔阿部瑞歐荷斯的人們小心管理著高價值的海產品,例如鮑魚和龍蝦。
要做好保育工作,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和信任必不可少。在下加利福尼亞的鄉村,鄰里之間很難找到信任感,但建立信任是可能的。
世界上五個最大的保護區是海洋公園,海洋生物在其中重新煥發生機。但怎樣的棲息地會產生最佳的生態效益?
沒有哪兒比普爾莫角更能說明成功保護海洋環境的第三條法則——擁有具備遠見卓識的領導——的重要性。上世紀80年代,它還是下加利福尼亞最南端附近一座落后的漁村。由于村子太小太貧窮,人們甚至買不起制冰機給魚保鮮,也修不起通往市場的道路。普爾莫角的漁民不多,其中有些人就在近海的珊瑚礁捕魚。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生物學家造訪此地,把潛水面罩借給了漁民。他們看到的景象引起了他們的擔憂——到處都是船錨留下的痕跡和倒伏的珊瑚。魚少得可憐。
“我們把珊瑚礁當作自家的花園,而不是一個生態系統。”一名叫做朱迪思·卡斯特羅的社區領導說,“漁民們沒意識到他們正在造成的損害。”
上世紀90年代早期,卡斯特羅的兄弟馬里奧(漁民兼潛水員)和提托·米哈雷斯(酒吧老板)帶領普爾莫角的漁民做出了一個支持海洋保護的大膽決定。到1995年,在一片71平方公里的水域內大部分捕魚活動都被禁止,從而建立起一片無捕撈保護區——也是該地區唯一一個得到良好監管的保護區。保護區的面積不大,但它證明了想要恢復海洋生態系統并不需要多大空間。如今普爾莫角國家公園的生物量是2000年的兩到三倍,基于潛水旅游的經濟正在蓬勃發展。
如果你的社區擁有當地唯一的珊瑚礁或是有一群渴望愛撫的鯨魚,發展旅游模式是拯救受到威脅的生態系統的一個絕佳途徑。但并非每個漁村都有如此奢侈的資源。另外,旅游業無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在圣伊格納西奧它只為大約200人提供了生計,而且每年只有幾個月的經營時間。旅游季結束后他們就回去捕魚了。
這就不得不提第四條法則了。要想讓環保行之有效,漁民在等待資源恢復的階段就得有辦法賺錢。而且環保還需要勞動力。芒利托社區——位于拉巴斯市旁的海灣邊上——采取了一種有意思的策略。
漁民一度在城市西部廣闊的淺灘上毫無節制地捕撈貝類。截至2009年貝類所剩無幾。在拉巴斯的非營利組織西北可持續發展機構的資金支持下,漁民停止捕魚,開始管理他們的資源。他們通過舉報非法捕撈行為和開展貝類數量統計的生物學調查賺取報酬。第一次調查估計貝類的數量不足10萬。如今其數量約為230萬。
“人們總說漁民給物種造成了破壞,但現在不一樣了。海洋已經給予我們很多,現在我們該回報它了。”一個漁民說道。
但最重要的是,在貝類的恢復期漁民可以通過監管和評估海洋資源獲得收入。向他們支付工資讓他們從漁民變成了專業的環境管理員。
最后一條法則大概也是最難遵循的。要做好保育工作,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和信任必不可少。
在下加利福尼亞的鄉村,鄰里之間很難找到信任感,但建立信任是可能的。至少拉巴斯的環保組織尼帕拉哈把賭注押在了上面。尼帕拉哈致力于下加利福尼亞東南部洛雷托到拉巴斯走廊沿途一片極度荒涼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漁業。在崎嶇的海岸線和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色周邊鮮有人的蹤影,道路就更稀少。但那些遺世獨立的漁村卻擁有該地區最好的未受保護的勝境。
尼帕拉哈組織開始在那些社區展開工作時,它并沒將注意力放在漁業上。它著力于宣傳足球錦標賽。“你是如何開始建立信任的?”負責協調項目的艾米·哈德森問道。“不是從談論漁業開始。你一定是這樣,這些家伙會不會踢我的脛骨,他會遵守規則嗎?我能信任他嗎?”
在小城鎮贊助足球錦標賽看上去是時間和金錢的雙重浪費,但它漸漸地在小心翼翼地彼此提防看護著漁場的村莊間建立起信任。接下來尼帕拉哈帶領一些漁民前往普爾莫角實地查看禁漁會給海洋生物帶來怎樣的影響。最終,經過數年的討論,幾個村莊決定嘗試保護海洋生物。每個村莊都辟出一小片區域,承諾五年之內不在該區域捕撈。那些區域都不大——最大的約有7.5平方公里——但卻是個開始。
“這就像開了個儲蓄賬戶。”何塞·曼紐爾·龍德羅說,這位35歲的漁民曾經見證了龍蝦和魚類數量的驟減。
為了監控保護情況,尼帕拉哈想出了個聰明的點子。每年它都會包下一艘調查船,和生物學學生、政府科學家以及來自各個社區的漁民沿著走廊進行一次距離為100公里的航行。
得知我要跟著他時,龍德羅翻了個白眼。我們在一個水下陡坡附近下了水。船上的許多漁民都曾在普爾莫角附近潛過水,但有幾個人告訴我他們并不覺得印象深刻。的確,這里有許多魚,但和走廊一帶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我看到了他們說的是什么意思。數不清的角落和大石頭是完美的棲息之所。龍德羅拿出一盒卷尺,拉出30米,帶著一個寫字夾板順著卷尺游,游過去時數魚類,回來時數無脊椎動物和其他動物。然后他坐下來數自己目力所及范圍之內的所有魚類。
總數有點令人失望——幾條孤零零的魚和幾只海膽。我們浮出水面后,龍德羅解釋說這片禁漁區很小,而且很新。在較大的禁漁區他見過生物多樣性在短短幾年內實現增長,從只有幾條羊魚到出現巨大的石斑魚、火魚和隆頭魚。從這里向北不遠,一個海洋保護區最近繁榮起來,社區已經決定擴大它的面積。“今年比我見過的過去幾年都好。”他說。“我看到它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有許多魚。”
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說,這種調查很重要。世界上五個最大的保護區是海洋公園,海洋生物在其中重新煥發生機。但怎樣的棲息地會產生最佳的生態效益?公園多大才能給周邊區域帶來改變?
走廊沿途的小保護區最適合來回答這些問題。但這種旅行還扮演著一個同樣重要的對外宣傳作用。在下加利福尼亞,正如同在墨西哥的大多數地方,人們對政府缺乏信任,許多人認為環保事業背后暗藏著不可見人的陰謀。但在走廊每個社區都能從與海洋生物學家一起工作的漁民那里聽到反饋。夜晚,在辛勞地游泳采集數據數日之后,漁民、科學家和政府雇員一同外出散步,一面交談一面大笑。龍德羅說,一從調查船上回來,社區里的人就拉著他問個不停。
“我擁有了不起的捕魚生涯。”一天傍晚他坐在船上說。“能當個漁民讓我很驕傲。社區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我們生活在這里很開心。”
我凝望著水面另一端美麗的海岸線,問他是否愿意讓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漁民。他躊躇片刻然后露出微笑。“不。我希望她成為一名海洋生物學家——去做我現在正在從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