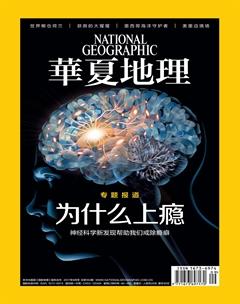世界糧倉荷蘭
弗蘭克·維維亞諾

荷蘭韋斯特蘭地區,大海般的溫室圍繞著一家農戶住宅。荷蘭人已成為農業革新的世界領導者和對抗饑荒新途徑的先驅。

隨著雞肉市場需求上升,荷蘭的企業正在開發使禽類產量最大化、同時保障人道飼養條件的技術。這座高科技雞舍能容納15萬只雞,備有從孵化到出欄的全程飼養設施。

韋斯特蘭是荷蘭的溫室之都,照明燈具呈現褶皺式的肌理,營造出某種不似人間的效果。這類農場可以人工控制內部氣候,實現全天候種植,不受天氣情況干擾。

壯觀的室內農場提供了種植生菜和其他綠葉菜的最佳條件。這座溫室的種植面積有9公頃,單位面積的生菜產量是露天菜田的4倍,并把對農藥的需求降低了97%。

在用發光二極管人工照明的條件下,番茄怎樣才長得最好——光應該從上面照還是從側面照,還是兩者結合?植物科學家亨克·卡爾克曼正在布萊斯韋克的“德爾菲改良中心”尋求答案。學者與企業家的聯合是荷蘭創新的一個關鍵驅動力。
荷蘭境內,距比利時國界不遠的一塊土豆田里,荷蘭農戶雅各布·范登博爾內坐鎮于一架巨型收割機的駕駛室,面前布滿儀表的操縱臺華麗程度不輸科幻電影里的星艦。
駕駛室離地3米,他高高在上地監控著兩架無人裝置——在田里游走的無人駕駛拖拉機和空中的四槳直升機——它們提供土壤化學結構、水成分、營養和生長情況的詳盡數據,測量每一株作物的進度,細致到它結的每一個土豆。這就是所謂“精確農耕”,生產力強大,有范登博爾內的收獲為證:全球馬鈴薯平均產量約為每公頃20噸,而范登博爾內能穩穩拿到每公頃47噸以上的成績。
如果考慮到收支表另一端的投入,這樣的高產就更顯得厲害了。將近20年前,荷蘭人舉國齊心地投入到可持續農業中,當時的口號是“耗半數資源,產兩倍糧食”。2000年以來,范登博爾內和其他許多荷蘭農戶已大大降低了關鍵作物的水資源依賴,最多的可達90%。他們幾乎完全取消了溫室種植中的殺蟲劑使用。2009年以來,荷蘭的禽畜養殖者也減少了抗生素用量,可低至原來的40%。
還有一個值得驚奇的因素:荷蘭是一個疆土狹小、人口密集的國家,每平方公里人口數超過500。長期以來被視為發展大規模農業所必需的種種資源,它幾乎一種都沒有。然而以經濟價值計算,它是全球第二大糧食出口國,僅次于美國,而后者的領土面積是它的270倍。荷蘭人到底是怎么辦到的?
從空中看,荷蘭的地貌與其他主要產糧國迥異——由密集種植的小塊田地堆砌而成,其中大多數以農耕產業的標準來看都微不足道,還緊挨著熙熙攘攘的城市和郊區。在該國的主要農事區,不論土豆田、溫室還是養豬場,幾乎沒有一處的視野內看不到摩天大樓、制造業廠房或城市區。荷蘭超過一半的陸地被用于農田和栽培設施。
看上去好似巨大鏡面的建筑連成片,在城郊排布,太陽照在上面會閃爍,夜幕降臨后又從內部發出奇特的光。它們是壯觀的溫室群,有的一座就可覆蓋70公頃土地。
這些農場可以人工調控氣候條件,它們使這個距離北極圈只有1600公里的邊地小國成了一種溫帶蔬果——西紅柿的全球領先出產地。荷蘭也是世界第一的土豆、洋蔥出口國,按總價值計算的第二大蔬菜出口國。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蔬菜種子貿易出自荷蘭。
這些驚人數字背后居功至偉的智囊團集中在瓦格寧根大學及研究中心(WUR),位于阿姆斯特丹東南方80公里處。該學府被廣泛視為全球頂尖的農業研究機構,也是“糧谷”的關鍵節點——后者是一群陣容壯大的農業科技初創公司和實驗性農場,命名有意與加州硅谷暗合,而瓦格寧根融合學術與創業精神的領跑者位置,類似于斯坦福大學在硅谷的位置。
WUR植物科學專業大組的主任恩斯特·范登恩德正體現著“糧谷”的這種融合精神。他是享有盛名的學者,植物病理學領域的世界權威,外表卻有著夜店調酒師般的隨性舉止。他說:“我不僅僅是個大學系主任。半個我帶領著植物科學院系,另半個我主持著九家涉及商業項目研究的企業單位。”他認為只有這樣兼顧兩頭,“科學驅動力與市場驅動力串聯運作,才能迎接等在前方的挑戰”。
什么挑戰?他用宣告末日存亡般的嚴峻語氣說,地球必須“在今后40年里產出比過去8000年歷史上所有農戶的總收獲更多的糧食”。
這是因為,與今日的75億人相比,到2050年將有多達100億人以地球為家園。如果農業不能實現巨量的增產,配合水、化石燃料用量的大幅降低,可能就要有10億以上的人面臨饑餓——這是21世紀最緊迫的問題,而目光遠大的“糧谷”精英相信他們已找到了革新性的解決方案。范登恩德堅定地認為,避免災難性饑荒的必要手段是觸手可及的。他的樂觀源于從超過140個國家的上千個WUR研究項目得來的反饋,以及WUR與遍布六大洲的諸多政府、大學商定的正式合約:分享研究進展并協力將它們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