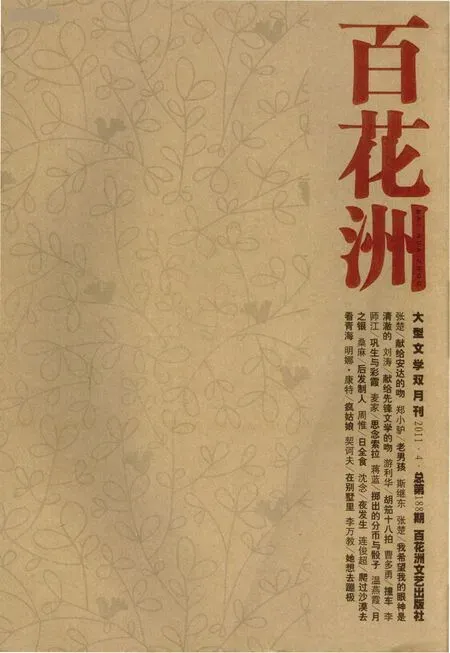與故人相逢(創作談)
黃昏,風雪,站臺,駛過的列車,憂傷的女人……這是李健演唱的《車站》,也似小說里的某個場景,沉郁的基調,像灰色站樓上漫灑的雪花。
老舊的窗欞墻壁是時代的象征,印證著歷史的年輪,大智門是漢口舊城垣的名字,1906年,京漢鐵路最南端的漢口火車站在此建成,為當時亞洲首屈一指的現代化車站。
京漢鐵路貫通南北,不僅促進了沿線經濟發展,也改變了武漢在近代中國經濟布局中的格局。武漢不再是長江流域中僅充當橫向傳導的角色,縱向的鐵路線在縮短了時間和距離的前提下,成百上千的運載力也有力地推動了漢口商業貿易的發展。“楚中第一繁盛處”的漢口,因水運和鐵路一雙翅膀開始騰飛,從此有了“東方芝加哥”的美譽。
寫小說的動機卻是偶然。長篇小說《傾城》完成之后,本打算寫點別的,也想到一個題目,收集了一些資料,但臨到下筆的時候,卻沒有一股力推動著往前走。還是素材單薄了些,沒有激起強烈的創作欲望,或者說,還沒到非寫不可的地步。
這時,寫漢口的心思又冒了出來。《傾城》寫的是1938年抗戰時期的漢口,寫得波瀾壯闊,激情似也用盡了,還有什么可寫的?但心里又在較勁,因對漢口沒有距離感。但要找到一個切入點,以充分展示那些遺忘的歷史,又避免重復以前的內容和套路,不給讀者產生疲憊感,實在有點難。
這番尋覓間,不想查閱資料時,掃到一張大智門車站的老照片上,頓覺一亮,仿佛遇見久別的故人,那些封存的往事,便細流一般汩汩往外冒。
兒時,常常隨大人來大智門車站迎送親人,印象中的車站路熱鬧而繁華,有年國慶隨祖母去京,便從大智門車站上車,燈火迷離的夜晚,川流不息的人,百貨公司,副食店,穿白大褂的營業員在花花綠綠糖果堆里忙個不停,站臺上簇簇的人影,火車啟動了,車窗外風吹麥浪般的揮手……一幕幕,像老舊的電影畫面浮現著。
歷史的火車穿過了一百年,經歷無數風雨的老車站終于到1991年光榮退休。當年的鐵軌已改成了馬路,那座顯赫的法式風格站樓作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依然孑立在日漸冷清的京漢街上,曾經的輝煌,美麗的風景,都已滄海桑田。
情感是彼此相連的線,寫小說便有了激情,思緒在往事中游移,進入到時間深處,白煙漫開,那些久遠的人和事,漸漸有了輪廓。
火車帶來了遷徙和改變,或是逃避饑荒和戰爭,或是為了尋找偶像和力量,或是為了掙錢養家,或是為了親人和愛情……這些逃避或追尋有主動也有被動,最終,它們都或多或少影響人生的方向,尤其是,當你生活在戰爭或者內心狂熱的年代里。
由此將小說設定在起伏動蕩的二三十年代,從大智門車站建成初期至日寇侵占一段歷史為時代背景,謝承遠、徐奕宏、劉黑生三個男人所經歷的成長與挫折,友誼與背叛,愛情與傷痛,最終他們規避個人的恩怨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次復仇行動。小說以謝承遠、徐奕宏與宋珠喜之間的情感糾葛構成主線,漸次展開故事情節,大智門車站猶如大舞臺,各樣人物在此粉墨登場,以表現鐵路開通對社會經濟產生的巨大效應,而時代的風云變幻又影響和改變這座車站及每個人的命運。
寫作過程的艱難卻始料未及。因年代久遠,相關資料匱乏,鐵路專業書籍甚少,可參閱的內容十分有限,又因鐵路方面熟知那段歷史者寥寥,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唯多次尋訪舊租界,從細枝末節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再動用邏輯和想象力進行創作。一年多的日子沉潛其中,回想那個艱難的過程,不堪回首,也難免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某種心緒。小說寫的是老漢口故事,人物的情感命運也與現實相關聯。火車站仿佛是一個時間的具象,迎來送往,悲歡離合,盡數滄桑,也備感蒼涼。那些過往,如見朝霞升起,亦看夕陽西下,遇見或別離,幸福或憂傷,是別人的,也是自己的。
車站有抵達,便有開啟。一部小說完成了,故事還在繼續,酸甜苦辣,總是人生的常態,歲月流轉,但愿心有所歸依,不失生活的希望,便是幸福的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