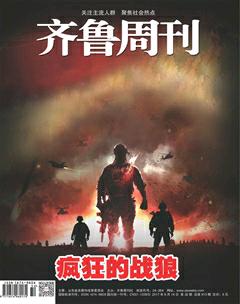民國時期的中日漁業戰
陳祥
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國民政府收到浙江、上海漁業群體的一堆請愿書。漁民們遭遇的難題迫在眉睫,日本輪船利用噸位大、航速快、設備新的優勢,在嵊泗列島海域大肆捕魚,將漁獲運到上海出售,這嚴重威脅到尚依靠傳統技術的中國漁民的生計,畢竟漁業資源有限。漁業群體希望政府出面與日本談判,保護本國漁民利益,洗刷漁業領域的國恥。
日本侵漁現象由來已久,但作為前現代政府的晚清不在乎現代漁業,治理失效的北洋政府則根本無力管理漁業,這一歷史頑疾留給了新建立的南京政府。適逢日本漁業擴張時期,北至白令海,南抵馬來群島,都遍布日本漁船,遑論不算太遙遠的中國沿海。
事實上,中國不乏有識之士注意到漁業危機。著名實業家張謇于1903年出訪日本,目睹了日本漁業和航運業的巨大進展,他回國后給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啟動古老中國的漁業改革。“海權漁界相為表里。海權在國,漁界在民。不明漁界,不足定海權。不伸海權,不足保漁界。互相維系,各國皆然。中國向無漁政,形勢渙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圖,必致漁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權因退讓而日蹙。”張謇的警告被一一兌現。
日本先進漁船如入無人之境
日本漁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現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國家的工業化、海軍擴張做有力支撐。1908年,日本才從英國購入第一艘金屬船體、蒸汽動力的漁船,屬于新興的拖網漁船。中國江浙沿海第一艘由機器驅動的漁船,誕生早于日本,可惜淪為形象工程,政府無力推廣使用。由張謇倡議組成的漁業總局,于1903年向德國訂購了一艘小型機輪和相應漁具,取名“福海”號。前期由于實際作業時間少,每年虧損,直至辛亥革命后調整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擴大漁場活動范圍、增加作業時間,它才發揮出機拖漁輪的威力。
新式捕撈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殘酷,它在近海能將冬季潛伏海底的魚群一網打盡,很容易導致漁業資源枯竭。這類新漁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傳統漁船操作者的不滿。政府為息事寧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漁船在近海作業,鼓勵它們去遠海,當然包括中國近海。
當時中國的漁船噸位小并且吃水淺,只能在近海活動。 1912年至1914年,為保護己國海域的生態,日本政府進一步擴大禁止新型漁船作業的海域,加速逼迫它們來到中國的東海和黃海。對于從事遠洋漁業以及去他國領海捕魚的企業,日本政府不惜給予財政補貼。1917年,日本規定全國只能有70艘拖網漁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須在200噸以上,航速至少11節,續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1924年,日本規定內海及黃海、東海海域之外的漁船不受70艘的限制,這等于變相鼓勵拖網漁船去南中國海。日本拖網漁船數量在1926年達到300多艘,在1937年達到1000余艘。
那時的關東州、青島、上海、臺灣和香港,成為日本漁船的后勤基地。出入中國領海的日本漁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縱容和保護。日本海軍不時派軍艦護漁,甚至直接向驅趕漁輪的中國軍艦挑釁、示威。為爭奪有限資源,占盡優勢的日本漁船不惜欺負中國漁船,最常見的手段就是破壞對方的網具。漁具一旦遭嚴重毀壞,中國漁船只能打道回府。最嚴重的情況,是日本漁輪撞沉弱小的中國木帆漁船,如1929年1月,“姬島丸”號漁船在溫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國漁船;1931年3月,該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國漁船。
《申報》在1931年3月8日記錄了日本漁船的野蠻狀,“又聞該日輪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魚,并且偷倒網艙之慣技,以至各釣船受害不淺,生計絕望。因日漁輪均裝有柴油引擎,俟釣船下網后魚已漲滿時,只須漁輪在船旁駛過,連魚帶網均為葉子所卷,因此船家損失頗巨。”
中國的反擊
“致我國沿海類(數)千百萬之漁民,均受其欺凌壓迫,以致漁場日縮,生計日窮,既乏相當漁業組織以謀抵抗,而政府又不為之后盾,含酸飲痛,莫可如何。”中國水產學會在1928年10月致電農礦部,“速令取締,取消其協約,停止其進行,否則我國東南領海最優美之處女漁場,必盡為日人所攫取。”
當日本先進漁船以中國漁民難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魚時,中國漁民只能通過民間自治的漁業團體向政府申訴委屈和憤怒。工商業發達的上海對此最敏感,海員總會、水產學校同學會、總商會、江浙漁業公會、漁輪業公會及各魚商團體,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實業等部門請愿。勢力雄大的上海總商會提出特別強烈的抗議,因為作為理事的鎮海人蕢延芳擁有8家漁行。
實業部長孔祥熙、部里的漁牧司官員皆堅定反對日本侵漁行為,實業部管轄著江浙漁業管理局。1931年4月,孔祥熙參加上海漁業改進宣傳會并作演講,他對漁業提出一整套減稅方案,倡議政府多介入漁業,保護漁民權益并提供種種支援。這套方案,之后被中國的漁業學者及官僚實踐和宣傳多年。
全世界當時對領海寬度尚無定論和共識,海軍力量最強的英國奉行3海里政策,許多國家遵循英國的做法,但也有不少國家反對。中國國民大會在1931年初想將領海延伸到12海里,遭到海軍部的反對,海軍警告此舉會在國際社會招惹來很多不必要的敵意。4月底,海軍部、外交部、內務部審議后宣布領海為3海里。但確定領海距離后,中國并不能阻止日本漁船進出,噸位大、吃水深的日本船通常在離海岸至少15海里外活動。困境中,孔祥熙想到了一個妙招,從關稅入手。
孔祥熙的辦法在1931年2月由國民大會通過,開始執行。首先,中國外交部通知日本,兩國尚未簽訂漁業協議,故日本漁船禁止入中國港口。接著,財政部通知海關,禁止日本漁船攜帶漁獲進入港口,除非是正規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關稅。孔祥熙還補上一條,禁止排水量100噸以下的小船來往于兩國港口,名義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實際是驅逐大批匯集在上海、小于100噸的日本漁船。3月底,中國政府免除了一切漁業稅和魚稅,這是中國反擊戰的輝煌時刻。
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議,同時還遭宋子文的強烈反對,宋子文嫌稅收有損失。又因為中國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態化執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軍大國,事實上執法時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漁危機總歸改善諸多。日本人可以找到許多變通的法子,例如將滿載漁獲的船開往日據的旅順和青島,裝入中國船的冷藏柜后轉去上海銷售,或船上借掛中國國旗,諸如此類的做法當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日本漁品的競爭力。故1932年“一·二八事變”期間,日本漁船借己方海軍撐腰,抓住窗口期,瘋狂在上海卸貨。endprint
不幸的是抗戰全面爆發,中國沿海主要港口首當其沖被占領。中國徹底無力抗拒日本的漁業侵略,以及背后的強大海軍。
戰爭中的漁業
大肆侵占中國沿海地區后,日本成立大批侵漁機構,在華東地區就有華中水產公司、東洋貿易公司、中支水產煉制公司、中國水產公司、帝國水物株式會社。日本在華北、華南也有許多侵漁機構。以成立于1938年11月的華中水產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它壟斷了上海的水產批發,并特許日本拖網漁船在附近作業。日本當局為壟斷漁業編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指責中國漁民運輸和經銷水產品的方法低效又浪費,褻瀆了寶貴的自然資源。事實上,上海所售水產的收入很大部分進入日本海軍囊中,海軍方面更是需要嚴控市場。
淪陷區漁民并未被禁止出海捕魚,只是需要獲得日偽當局的海關號簿。中國漁船若要在上海卸貨,只能固定賣給日偽的侵漁機構,如華中水產公司。不幸中的幸運,難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導致上海水產需求遠超戰前水準,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讓在舟山海域捕魚的中國漁民多少能克服戰爭帶來的苦難。
太平洋戰爭之前,能在中國漁業生意上與日本競爭的唯有西方列強。法國人看準商機,在1938年6月與上海水產市場的華人中間商合作建立中法漁業公司,專事滬上法租界的漁品銷售。為了搶貨源,這家新的合資公司豪爽地給舟山的漁民們貸款2萬元,與沈家門的水產捕撈業負責人合作,協商將漁品運到上海。這匹“黑馬”的背后不僅僅是法國,還有其他歐洲國家。
盡管日軍占領了中國大部分港口,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浙江沿海仍有很多地區處于中國政府掌控下。中國海軍在戰爭初期就損失殆盡,橫行無阻的日本海軍和混亂秩序催生的海盜,給國統區漁民帶來很多危險。例如,在臺州溫嶺縣,冬季帶魚漁汛到來,曾習慣季節性去舟山海域的漁船,出于風險衡量只能忍痛放棄出海。更有國家大義讓位給養家糊口的時候,1938年7月,上海的定海同鄉會代表漁商向寧波市政府求情,希望獲準讓漁獲從定海運往上海。戰時的物資封鎖是雙向的,國民政府一樣禁止物資流向淪陷區。
國統區的漁船出海時攜帶中國的海關號簿,但遇到日本軍艦時須把號簿藏起來或扔進海中,否則日本人會沒收、銷毀漁獲,或強制把船帶到上海,強制把漁獲出售給日方的營銷機構。而當漁船來到尚未淪陷的鎮海港時,需要接受軍隊和海關的檢查,上繳給地方漁會1到5元,船然后才能獲準去寧波賣貨。寧波淪陷后,漁船需要獲得日偽的證件,否則遭重罰甚至生命危險。
抗戰勝利后統計,中國沿海地區在戰時共損失漁船幾萬艘。以浙江地區為例,1937年前約有26000艘漁船活躍在浙江海域,隨后到來的戰火毀滅15000艘。損失方式包括日軍在海上擊沉漁船、日軍焚毀當地漁船、海盜掠奪和毀壞漁船、漁船因長期無法出海而年久失修,等等。中國漁船在舟山海域的漁獲量在1936年是93000噸,至1947年僅剩12000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