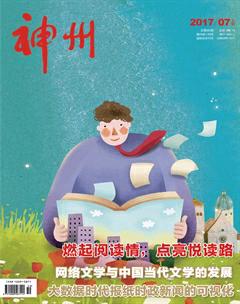淺談盛唐山水詩審美主體的新變
閆海凌
摘要:山水詩這一題材作為中國詩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唐代詩人的筆下呈現出與前代既一脈相承,又頗多革新的美學風貌。在盛唐山水詩中,作為審美主體的詩人在創作實踐中對儒釋道思想進行了新的選擇和構建,其對審美客體的觀照態度也有所新變。
關鍵詞:山水詩;盛唐;審美主體;審美客體;新變
以詩歌模山范水的傳統上可追溯至《詩經》、《楚辭》等作品,到東漢末年建安期間出現了第一首真正意義上完整的山水詩——曹操的《觀滄海》。此后,山水詩在晉宋陶淵明和大小謝手中獲得新生,并于盛唐發展至極致。此時山水詩的繁榮體現在多個方面:大家輩出且名作流傳甚多,并呈現出多元審美形態;詩歌題材空前擴大,展示出紛繁多彩的地域特色;吟詠山水的情感內涵進一步擴大,詩境廣博,意蘊悠長。
一、主體創作中對儒釋道思想的構建
相比晉宋山水詩中對老莊思想的大量吸收,在開放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唐代詩人受到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共同影響,在詩作中所呈現出的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更為多元。其中多以儒家思想為主,釋道二家為輔:
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維《少年行》)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孟浩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李白《駕去溫泉后贈楊山人》)
盛唐氣概的各個方面自然而然地激發起詩人們歌頌、報效國家的雄心。一代名相和文壇領袖張九齡和一生憂國憂民心系蒼生的杜甫自然不必多說,其他的盛唐山水詩人們,如王維、孟浩然、儲光羲、裴迪、常建等,或向往建功立業一展宏圖,或始終無人賞識壯志難酬,或飽經官場沉浮最終歸隱山林,總歸是或多或少地懷著政治抱負,對功名充滿熱情和向往,渴望立言立名于后世。這便是儒家入世精神在詩人處世價值觀念中的反映。
盛唐山水詩中也帶有相當濃厚的佛道色彩,以王維的詩作為代表。王維的山水詩作以一“靜”字貫穿始終,這顯然符合禪宗精心順其以求人生暢達的旨義。“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一個“獨”字和一個“幽”字,描繪出環境的清靜;彈琴長嘯襯托出作者心境的恬靜;無人相知卻又明月作伴,更是升華了空明靜謐的意境。忘情于幽靜的自然山水,陶冶其心智性情,悟得人生的曠然,這便是以佛家道義觀照人生,并將其映射于詩作之中的體現。
事實上,老莊之道所崇尚的“自然”、“無為”和佛釋的“空”、“寂”思想,很多情況下是作為知識分子在仕途失意、壯志難酬的境遇之下的備選項而存在的,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派遣苦悶、自我安慰的作用。雖然我們常說王維奉佛、李白崇道,但那只是詩人個體的人生價值取向及其在詩文中的個性化體現,而此二人亦常懷匡時濟世的儒家之心,所以在盛唐山水詩中,釋道思想并不占據主要地位。即使是詩人們后來選擇隱退,也符合孔子“用則行,舍則藏”、“待賈而沽”、“獨善其身”的理念。對祖國河山的熱愛和歌頌以及民族自豪感成為了盛唐山水詩中的重要情感因素,與其他題材詩歌一樣,這是大唐盛世在文學中的磬音,也包含著詩人們致君堯舜、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和抱負。
二、審美主客體之間關系的新變
(一)從模山范水到同情共性
山水田園詩發展到盛唐,審美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新變首先體現在從冷靜客觀地模山范水到熱情地將個人情志發散于目之所視、耳之所聞,山水物象不再是靜態的、有距離的,而成為了與詩人同情共性的靈動之體。在謝靈運的代表作《登池上樓》中,作者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而縱情于山水之間,把政治抱負轉換為對山水的迷戀和吟詠,故在此詩中前半部分都在抒發自己苦悶的心緒。在觀賞山水時,作者“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岑”,保持著與景物并峙對立的狀態,對景物進行窮形盡相的描摹。如千古名句“池塘生青草,園柳變鳴禽”,清新自然,極富生機。謝靈運的山水詩有極強的畫面感,雖然還未完全革除玄言詩遺風,存在著有句無篇的缺弊,卻邁出了革新之路的第一步。而同樣是寫景,在李白詩中就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渡遠荊門外,從來楚國游。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渡荊門送別》)
此詩作于詩人出蜀之際。群山、江河、明月、云彩都給人飛躍的動感,畫面奇妙繽紛,境界澄澈開闊。故鄉水萬里相送,隱含著作者對家鄉的一絲絲牽念不舍,更多的是出鄉關、建功業的豪情壯志。而即使是經歷了人生的坎坷風雨、大起大落,李白也不曾改變其曠達瀟灑的個性: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
同樣是排遣被貶謫之后的愁苦憤懣之情,李白詩中自然山水卻是飄逸靈動的,流露出樂觀逍遙的精神,自然山水之靈與詩人之靈達到了渾然一體的境界。李白的山水詩橫向擴展了盛唐山水詩的抒情容量,為其增加了一份飄逸雄渾、驚心動魄的壯美色彩。他對自然山水的熱愛是根植于他對萬物生命本身的熱愛中的,這種熱愛并不因其政治上的失落而減少,反而是仕途失意進一步觸發了他對山水的迷戀。“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作者在凝視山川時,所感受到的是人和自然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的情愫。“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作者總能在孤獨中體會到自然的陪伴和安慰,因此詩中即使有孤寂和苦悶,其抒情濃度和力度也總是有所控制的。
(二)從躲禍避亂到陶情養性
盛唐詩人的筆下很少真正流露出由官場失意而產生的頹廢、消極的情感,即使苦悶于政治抱負無法施展也不曾因此對人生價值產生質疑,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潛藏著一種樂觀向上的進取精神。盛唐詩人即使舍棄了廟堂之高選擇了江湖之遠,也是因為他們秉持著用行舍藏的儒家處世方法。和陶淵明有所不同,即使唐代很多詩人都對陶淵明表示敬佩,卻鮮有人下定決定像陶淵明那樣真正退守田園,將“隱退”作為目的本身。于唐代詩人如孟浩然來說,退隱只是他們再度出仕前的蟄伏,讓自己暫時地從“塵網”中解脫出來,讓疲憊的心靈得到片刻的安寧。這種心態的轉變自然與當時社會政治環境息息相關。與晉宋文人相比,盛唐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更加繁榮和穩定,因此對世事無常、人生苦短沒有那么深刻的體會,也沒有形成如此強烈的“避禍”意識。他們投身山水不像晉宋文人那樣希冀遠離朝廷保全性命;其訴求更多地體現在親近自然以陶冶性情、完善人格和放松心情。寄情山水的不同目的和對自然的不同訴求,是審美主客體之間關系變化的另一體現。endprint
(三)從景中情趣到景外哲理
盛唐山水詩中還體現出一種對景物內在意蘊和的探索。如孟浩然的名篇《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這首小詩一大特色便在于言近旨遠,韻味無窮。作者從酣暢閑適的“春眠”中醒來,朦朧恍惚中聽得鳥語陣陣,自然詩人心情愉悅,胸懷舒展。回想起前夜里有風雨之聲,不知道春花又落了多少。此刻即使有淡淡的傷感,也被壓縮成一縷輕云,風吹即散。本詩的整體意蘊是平和閑適、自然沖淡的。“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像與鳥的對話,更是作者于對自己人生哲思的抒發。“風雨聲”和“花落”在這里象征著時間的自然流逝,花開花落、春去春來都被作者以一種平靜坦然的態度對待,這也是作者順其自然、以豁達平靜的心態面對有限人生的體現。由此,風雨和落花都沾染了別樣的生機,作者也在對景物的觀照中升華了對人生的體悟哲思。
王維有名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這也可以看做盛唐山水詩的新變所在。各種名山大川和秀美田園在紙上渲染開來,或是懸泉瀑布,或是清榮峻茂,或是野花幽香,或是嘉木繁蔭。四時之景,四方之境,皆流于詩人筆端。其中類似于“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如此直觀地將主體“我”代入的并不多見,更多的是描寫和抒情的主人公隱藏在畫面之外,他不在“空山”之中,可是詩作中卻處處透露著其主觀情志。從與山水景物保持著一定距離的“觀景人”,到萬物皆著我之色彩、與山水共情共性的“造景人”;從窮形盡相地描摹景物,到以情觀景、融情于景并偏重于主觀情感的抒發;從投身自然以避禍自保,到寄情山水以修養身心陶冶性情;從滿足于自然景物的外在形態,到注重挖掘其內涵意蘊,并進一步對人生哲理進行探討,這便是盛唐山水詩對前代晉宋山水詩的革新。加之詩論的進一步發展和詩人在創作中的有意實踐,凡此種種,共同促成了盛唐山水詩的大繁榮面貌。這是盛唐山水詩的獨特魅力和新成就,也是大唐盛世的風貌氣概對文學的饋贈。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2]王凱.自然的神韻——道家精神與山水田園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高樹森.元嘉之雄與盛唐詩仙——謝靈運與李白山水詩之比較[J].蘇州大學學報,1986(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