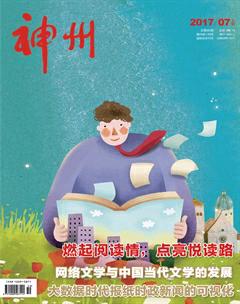融合中西·塑墨野逸——淺析袁曉岑作品的文脈根源和藝術氣韻
摘要:袁曉岑先生是中國近現(xiàn)代極具特色的藝術家,不僅在雕塑和國畫上擁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統(tǒng)一,更是在中西藝術的結合上融會貫通,自成一家。本文主要通過對袁曉岑先生藝術作品文脈根源的梳理和藝術氣韻的探究,試圖對袁曉岑的藝術可以有更為深入的認知。文脈的梳理主要通過三個部分的呈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源、山野生活的體驗、西方藝術的影響,內外結合梳理出一條全面的文脈根源線索。
關鍵詞:袁曉岑;中西融合;文脈根源;野逸氣韻
藝術的生發(fā)總有一個根源性的存在,這種根源往往來自于自身的文化系統(tǒng),價值體系,從這一點生根發(fā)芽,開枝散葉,形成獨特的藝術語言和擁有明晰文化脈絡的藝術,事實上這是一種自我身份的確立和認同。追根溯源,袁曉岑先生的藝術也是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自我文化身份的確立和審美價值體系的建構過程。
首先來說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的學習讓袁曉岑先生得以在深厚的文化土地之上生長出自己獨特的藝術。唐朝張璪曾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袁先生對于藝術的學習最開始其實是把自然萬物當做自己的師長,置身其中,被萬物生命的靈動氣息所感染,在很小的時候就產(chǎn)生了對于繪畫和雕塑的藝術激情,于是自發(fā)的用泥土捏制小馬,用炭木作畫于土墻之上,并受到師長同學的欣賞鼓勵,袁曉岑先生開始立志學習藝術。
如果自然萬物,山野動物給予袁曉岑的是對這個世界感知生命的啟蒙,那么尋找自身東方文脈根源是讓袁曉岑將自身的藝術感受納入到了一個更加豐富和完整的文化系統(tǒng)之中。東方的文明系統(tǒng)其實更多的是指向于概念性的抽象感,尤其是作為典型東方文明的中國,更是推崇哲學中道的追求。
中國傳統(tǒng)藝術經(jīng)過千百年的演化推移,事實上已經(jīng)像所有古國的文明一樣面臨自身發(fā)展的瓶頸和外來文化的挑戰(zhàn),到了近代隨著西學進入文化審美視野,繪畫在一批擁有革新精神的藝術家的引領下,適時改革以求得到長久的發(fā)展。其中嶺南畫派作為影響最大的一個畫派,對中西藝術的融合做了卓絕的貢獻,他們主張“折衷中外,融合古今”,順應時事,得以讓中國傳統(tǒng)藝術重煥生機。袁曉岑先生正是在接觸到嶺南畫派之后,畫風開始轉變。他曾在自傳中如是說:“對高奇峰、高劍父和陳樹人為代表的嶺南畫派開創(chuàng)的中西結合的道路予十分推崇并特別對這一畫派加以概括總結。予的想法得到了李先生的共鳴與鼓勵。”[1]
在此之后,袁曉岑先生更是得到了徐悲鴻先生的指點和鼓勵,1941年在云南大學映秋院在校長熊慶來的引薦下,袁曉岑相識徐悲鴻,從而打開了另一扇更為廣博的藝術視野的世界之窗,通過徐悲鴻,袁曉岑了解到了魯?shù)隆屠铩⒘_丹、蓬蓬等西方大師的作品,對袁曉岑以后雕塑的深厚造詣和精準的造型給予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袁曉岑先生的藝術文脈可以追溯傳統(tǒng),山野生活壞境,加之受到西學的影響,從而形成一種獨具一格的野性自由,文人逸致的藝術氣韻。
生于貴州鄉(xiāng)村的袁曉岑,從小感受著自然山野的生命萬象,事實上這是一種自然地啟蒙,古人常說師法自然,野逸的鄉(xiāng)村環(huán)境給予幼小的袁曉岑極大的震撼。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家有房屋數(shù)間,薄田數(shù)丘,自耕自食,但山林廣闊環(huán)境幽深,其時山花野卉四時不絕,飛禽走獸出沒其間”[2]另外,古滇王國代表性的青銅扣飾,原始野性的造型對袁曉岑先生的雕塑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作品《古滇青銅扣飾》里,野豬、豹子、蛇相互纏繞,撕咬,形成一種流動的雕塑造型,自由野性。
袁曉岑的藝術氣韻除了野性自由之外,更多的是文人逸致的詩意指向。袁先生曾求學云南大學文史系,打下了堅實的文史功底。他曾說:“以‘意境創(chuàng)造高雅詩意之境界;取雕塑概括凝煉、造型結構準確之長;表達神韻與美。乃予追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之藝術主導思想及手法。”[3]在《驢背詩思》、《懷素書蕉》、《舉杯邀月》等雕塑作品中,無論從文人題材的選擇還是雕塑手法的刻畫,都顯示出了典型的中國文人狀態(tài),在泥味的雕塑塑造里有著濃郁的詩情氣質。
在當代藝術繁復多樣,西方依舊掌控文化話語權的當下,作為有著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該何去何從,中國藝術家該如何自處,顯然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之中,我們自身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藝術脈絡是什么,在近代西方摧毀我們文化自信和標準這么多年之后,我們更應該重建我們的文化系統(tǒng),身份定位。袁曉岑先生以及與之同時期的大師們,早已在重構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天地,值此契機,回顧袁先生的藝術歷程,對當下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發(fā)展更是有著積極的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
[1]《自序——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袁曉岑;2004年3月于昆明翠湖先生坡
[2]《自序——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袁曉岑;2004年3月于昆明翠湖先生坡
[3]《自序——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袁曉岑;2004年3月于昆明翠湖先生坡
作者簡介:王偉(1990.10—)男,漢族,籍貫:甘肅秦安,云南藝術學院,美術學,在讀碩士,專業(yè):美術學,研究方向:中國當代表現(xiàn)與象征類繪畫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