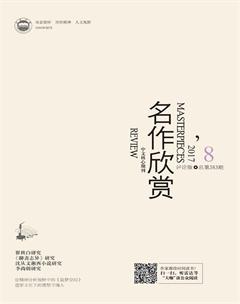論精神分析視野中的《盜夢空間》
摘 要:《盜夢空間》是精神分析理論在藝術領域的成功演繹。影片對人類的無意識進行大膽的開掘和想象。從精神分析角度入手,我們不僅可以從內容方面發現影片的無意識癥候,勘透主人公柯布的人格沖突,詮釋費雪的“俄狄浦斯情結”;而且可以從形式方面探索影片是如何體現這種無意識癥候的,即運用“夢的生產”理論闡釋影片中的象征和隱喻。
關鍵詞:夢 人格沖突 俄狄浦斯情結 象征
一、引言
電影史上有許多與夢境相關的經典電影,如《香草的天空》《穆赫蘭道》《野草莓》《盜夢空間》等。其中,諾蘭執導的《盜夢空間》備受矚目,電影以快節奏的情節敘述,炫目的特技效果以及對人類潛意識的執著探尋問鼎當年電影票房。《盜夢空間》不僅展現了人類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較量,呈現了人格正反兩面的沖突和斗爭,而且是以一種藝術的方式完美地呈現了個人無意識,是精神分析學在藝術領域的一次成功演繹。本文試圖通過人格沖突理論、俄狄浦斯情結以及“夢的生成”理論三個角度透視影片的文化內涵。
二、柯布的人格沖突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是瞬息萬變的,所謂的意識所處的狀態是非常短暫的,可能瞬間就成為潛伏的,也可能在某種條件下恢復為意識。這種潛伏的意識也被稱為無意識。弗洛伊德最大的貢獻就是發現了人類的無意識。他指出雖然通常狀態下人類思想表現為意識狀態,但實際上無意識才是整個心理結構的主體和靈魂,“我們發現……有非常之強有力的心理過程或觀念存在著,雖然它們自己并不是意識的,但卻能夠在心理生活中產生普通觀念所產生的一切結果(包括那些本身能夠變成意識的觀念所產生的結果)”{1}。無意識就像海面下的冰山,具有無窮的潛能。在弗洛伊德看來,一個人的心理結構可由意識、前意識和無意識三部分組成。“意識”是心理結構的外表,它建立在知覺的基礎之上。“我們把觀念在成為意識之前所處的狀態稱為壓抑。在分析工作中,我們堅持把實行壓抑和保持壓抑的力理解為抵抗”{2}。被壓抑的東西(the repressed)是無意識的原型。弗洛伊德又把它分為兩種:一種是潛伏的但能成為有意識的,也被稱為前意識,另一種是被壓抑的但不能通過通常的方法使之成為有意識的,這種稱為無意識。前者只是描述意義上而非動力學意義上的無意識,后者屬于那種被壓抑的動力學上的無意識。前意識比無意識更接近意識。這樣,前意識就成為連接意識和無意識的紐帶。在前意識的連接下,意識會被壓抑而成為無意識,而無意識可以通過相應于該物的詞表象而追溯為意識。這樣,人們的心理結構就成為一個可以連通的整體。其中,無意識是心理結構的基礎和人類活動的內驅力,它決定著人的全部有意識的生活,甚至個人和整個民族的命運。
無意識既然沉潛在心靈深層,人們怎樣才能感知并理解它的內容呢?弗洛伊德指出“夢為我們提供了接近無意識的主要但卻并不是唯一的途徑”{3}。人們可以由夢入手發掘無意識,只有在意識松懈的時候,無意識才能自由活動并表現自身。當人們睡著時,意識的“檢查功能”失效時,無意識才活躍起來。弗洛伊德試圖通過對夢的解析來發現人心底的人格沖突。而要真正讀懂一個人的夢并非易事。因為,人的夢要經過“二次生產”,通過化妝、轉移、置換等一系列修飾之后才會表現出來。對普通人而言,人們會不自覺地掩飾自己的欲望。“在夜晚,我們也產生了一些我們羞于表達的愿望;我們自己要隱瞞這些愿望,于是它們受到了抑制,被推進了無意識之中。這種受抑制的愿望和它們的衍生物,只被允許以一種很歪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夜間的夢和白日夢一樣,是愿望的實現。”{4}我們必須從“顯意”去尋找“隱意”,這正是夢的詮釋的過程。而只有當我們能讀懂夢的象征、隱喻之后,才能勘透一個人的原始欲望。在弗洛伊德看來,被壓抑的內容就是人的原始欲望——性欲。
電影《盜夢空間》的情節就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學基礎上,影片圍繞著一個商業陰謀展開。費雪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帝國,作為這個能源帝國的競爭對手,日本的商人齋藤想利用“盜夢”的手段盜取對方商業機密,解散能源帝國。齋藤找到著名的筑夢師柯布。柯布是高科技的商業間諜,他的團隊可以利用超強鎮定劑,在催眠的狀態下,侵入人的夢,盜取對方的商業機密。齋藤以回到孩子們身邊為誘餌,成功地俘獲了柯布的心,使他同意了這個大膽的計劃。在齋藤的安排下,柯布試圖在羅伯特·費雪的腦海中植入一個意念:解散父親所建立的商業帝國。在雅莉亞德、亞瑟、伊姆斯、尤瑟夫和齋藤的協助下,在夢中夢的構筑中,這一商業計劃成功實施。
影片中意念的植入正是運用了弗洛伊德的三重心理結構學說,其中無意識的心理內容可以轉化為前意識而成為意識。弗洛伊德認為只有當對抗力量消失,壓抑被解除時,由詞語殘余,通過視覺記憶、聽覺記憶,無意識可以追溯為意識。電影通過一種藝術的方式,把一個人由夢到醒的過程喻示從無意識轉化為意識的過程。所以,當羅伯特·費雪從夢境回歸到現實時,無意識喚醒為意識,他決定找回自己,實現父親的遺愿,即解散原有的能源帝國。同樣,柯布心中揮之不去的是妻子的幻影。正是柯布在妻子心靈中植入“我們的世界不是真實的”這一意念。當妻子從夢中醒來時,無法分清幻想和現實,走上了死亡之路。柯布對妻子的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他一直很內疚,無法解脫。茉兒從夢到醒的過程,正是從無意識喚醒為意識的過程。而“我們的世界不是真實的”這一意念也由無意識經前意識而成為意識,并最終促成了茉兒的死亡。而人的本能欲望,一些羞于表達的欲望被壓抑后沉入心靈的底層,轉化為無意識。無意識以夢的方式達到呈現。柯布的夢境是有層次的。當與雅莉亞德共享夢境時,他的夢境中有一層是和茉兒構筑的二人世界,有一層是孩子玩沙堆的背影呈現。可以看出,柯布把對妻子的無盡思念和對孩子的想念都壓抑在心底。而在他夢境的最深一層,是在結婚紀念日茉兒臥軌自殺的場景。可見,他在努力壓抑無意中殺死妻子的事實。這些觀念沉睡在心靈深層,以夢的方式達到釋放。
被壓抑的內容隸屬于人的“本我”,意識隸屬于人的“自我”。被壓抑內容與意識的較量就轉化為“本我”與“自我”的人格沖突。“本我”是“我們本性中非人格的以及隸屬于自然法則的東西”{5},受快樂原則的支配,在整個人格心理中處于支配地位,其核心就是人的原始性欲。“自我”受現實原則的支配,表現為“用外部世界的影響對本我和它的趨向施加壓力,努力用現實原則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支配地位的快樂原則”{6}。“本我”與“自我”之間構成沖突。這種人格沖突在主人公柯布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現。柯布的夢中一再出現茉兒的幻影。而且夢境越深,茉兒的破壞力就越強。柯布的“本我”表現為他對茉兒的性欲以及他努力壓抑的無意中殺死茉兒的犯罪事實。影片中,茉兒正是柯布性欲的象征。后來,茉兒死了,柯布只能憑借記憶構筑一種夢境,他把茉兒囚禁在夢境中,以此來滿足與茉兒白頭偕老的愿望。柯布的“自我”表現為對茉兒的性欲的壓抑和殺死茉兒犯罪事實的壓抑。通過壓抑,柯布試圖把殺死茉兒的犯罪事實不僅從意識中排斥出去,而且從其他效應和活動的形式中排斥出去。在自我的控制下,柯布是能控制茉兒不出現在意識中的,但他無法阻擋茉兒出現在他的夢境中。一旦進入夢中,茉兒的幻影就會出現并干擾整個計劃。而這恰恰是柯布人格沖突的一種外化。而柯布夢中縈繞的兩個孩子的身影,更是他無法實現的父愛的一種替代性的滿足。茉兒在臨死前留給警察的一封信,使柯布成為殺人嫌疑犯。因此,柯布無法回到孩子的身邊。當他意識清醒時,還能控制自己對孩子的思念,一旦意識活動松懈時,兩個孩子的身影就會出現在他的夢境中。
影片完美地展現了柯布心靈救贖的整個過程。與其說是柯布幫助齋藤實現商業計劃,不如說是齋藤幫助柯布找到了回家的路。
三、費雪的“俄狄浦斯情結”
弗洛伊德在《釋夢》一書中分析“父母死亡的夢”時,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他指出夢是未達成愿望的一種替代性的滿足。父母死亡的夢,代表兒童無意識中真的希望父母中有一方死亡。男孩通常希望父親死亡,因為他依戀母親,并對父親具有敵意,他認為是父親占有了母親。而女孩通常依戀父親,并對母親具有敵意,女孩通常希望能與父親生育一個孩子。這樣,弗洛伊德發現了兒童性欲望的存在。“他一直在和內心里想要父親離開的愿望做斗爭。將父親視為與其爭奪母親好感的競爭對手,他那正在萌發的性欲望的含糊預示正是指向其母親的。”{7}這種男孩對母親依戀、對父親仇恨的情結,被稱為俄狄浦斯情結。弗洛伊德結合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深入研究。他指出這部悲劇的震撼性在于,把人們深埋在潛意識當中的“弒父娶母”的欲望展現出來,而這種欲望是人類自身難以控制的,就像阿波羅的預言一般預示著人類的命運。“我們早就注定第一個性沖動的對象是我們自己的母親,而第一個仇恨的對象就是自己的父親,同時我們的夢也會使我們相信這種說法。”{8}所以,俄狄浦斯情結體現了人類的原始欲望。
弗洛伊德指出,雖然個人具有俄狄浦斯情結,但又必須克服俄狄浦斯情結,否則,就成為精神官能癥患者。那么,如何克服俄狄浦斯情結呢?弗洛伊德指出,兒童可以把對父親的仇恨轉移到其他動物身上。在《圖騰和禁忌》一書中,弗洛伊德指出患有動物恐懼癥的兒童正是把對父親的恐懼和仇恨轉移到動物身上的結果。“一個小男孩身上產生的對其父親的仇恨源自于對其母親的爭奪,這個仇恨不可能達到對其心理的無限控制的程度;這種仇恨不得不與他原來所建立起來的對父親的愛和敬佩這類情感做斗爭。孩子通過將其心里的這種敵意和畏懼情感轉移到其父親的替代者身上的方式,來使自己從對父親的愛恨兩方面之矛盾性情感態度中產生的沖突中解脫出來。然而,這種移植作用,并不能終止這種沖突,它不可能在愛與恨這兩種情感之間實現一種明確的分離。相反,這種沖突在他與移置對象的關系中再現出來,上述矛盾性情感擴展到它的身上。”{9}通過這種方式,兒童可以從俄狄浦斯情結中解脫出來,成為一個正常的兒童。弗洛伊德指出,俄狄浦斯情結終將被克服,就像兒童乳牙脫落一樣,是一種原始欲望的克服。在俄狄浦斯情結中,我們可以看到兒童對父親既恐懼又仇恨的心理,恐懼是指一種閹割恐懼:男孩害怕自己的生殖器消失。而仇恨是因為父親占有了母親,父親具有大的生殖器,兒童希望自己也具有大的生殖器并最終取代父親。此外,兒童對父親也具有愛意。這樣,兒童對父親就產生了既愛又恨的雙重情感。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轉移機制”和“認同機制”的作用下,男孩對父親的愛意會壓倒仇恨。這樣,即使是在父親死后,男孩在懺悔的情緒中依然遵從父親生前的意旨,就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
影片中,在羅伯特·費雪心靈深處有一個“小風車”,這個“小風車”承載了父親的濃濃愛意。而羅伯特·費雪與父親的隔膜一直存在。羅伯特深深地記得:在他十一歲母親過世時,父親的冷漠;就是在父親臨死前,父親也不想多見羅伯特·費雪,不想把內心告知羅伯特·費雪。羅伯特·費雪一直無法理解父親對自己的態度,以及父親最終的遺囑和商業帝國的去向。而柯布團隊正是利用了父子間既愛又恨的心理成功地實現了植夢計劃。影片中,柯布團隊構筑了一個三層夢境,試圖利用費雪父子的沖突與沖突的化解來控制費雪的意念。第一層夢境是在雨中的城市街區,羅伯特·費雪人格的投影人物與柯布團隊隊員進行了猛烈的激戰。伊姆斯化身為布朗寧叔叔,通過苦肉計,試圖盜取老費雪床頭保險柜的密碼。在第二層夢境中,柯布團隊啟用了“查理計劃”,柯布暗示費雪本人正在被人們盜夢,以此使費雪開始懷疑自己的無意識,通過無意識投射出的布朗寧暗示費雪:父親希望他解散商業帝國,費雪不配擁有父親的成就。在第三層夢境中,在雪山上,柯布團隊隊員與費雪的人格投影繼續在戰斗。費雪試圖去打開保險箱,去尋找父親的最后遺囑。最終費雪打開保險箱,看到最后遺囑、風車,費雪第一次真正明白了父親的良苦用心——父親希望他能開辟自己的一片天地,父與子和解。費雪被水沖回到岸邊時,對布朗寧說:“父親希望我找回自己,不要為他而活,我決定去做。”這意味著小費雪會遵照父親的遺囑,解散整個商業帝國。齋藤的商業計劃成功地實現了。在影片中,費雪父子的沖突與沖突的化解,正體現“俄狄浦斯情結”與“俄狄浦斯情結”的克服。
俄狄浦斯情結在宗教、道德、藝術和社會心理方面都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價值。藝術中,這種“弒父情結”成為一種原型,在一代一代的作品中重現。每當這一原型出現,都會給觀眾以心靈的震撼。
四、陀螺·風車·保險箱
如果說本文的前兩節是從內容的角度分析《盜夢空間》的精神分析內涵的話,這一節我們從形式的角度挖掘影片中的精神分析內涵。前者“像考察生活中的無意識癥候一樣考察藝術中的無意識癥候”{10},后者關注藝術作品的形式,即影片的無意識癥候是如何表現和揭示的。
弗洛伊德在《作家與白日夢》一文中指出:文學作品是作家的白日夢,是作家未完成愿望的一種替代性滿足。白日夢雖然和夜晚的夢不同,但也體現了人們一種深層次的欲望。而這種欲望通常是羞于啟齒的,必須經過一定的修飾、軟化之后才能被別人接受。通常,人們通過“壓縮”和“移置”的方式,把夢的“顯意”和“隱意”區分開來。我們看到的是夢的“顯意”,再由“顯意”的詮釋中發現夢的“隱意”,從而勘透人的無意識心理內涵。所以說文學作品不是夢的反映,而是夢的加工。弗洛伊德對夢的解釋使我們能夠把文學作品看成一種“生產”,而非一個“反映”。與夢一樣,作家把一些原材料如“語言、其他文學文本和感受世界的方式”等運用某些技巧改造成文學作品。改造文學原材料的技巧就是各種文學手段。正如我們可以去分析、破解和分解夢文本一樣,我們也可以分析文學作品本身。我們可以揭示文學文本生產的種種過程,關注作品中的種種重復、種種省略、種種歪曲的內容,正是這些“癥候”為接近無意識內容提供了通道。因此,“通過敘事中那些看起來似乎是種種回避、種種情感矛盾和種種緊張之點的地方——那些沒有得以說出的話,那些被說得異常頻繁的話,語言的種種重復和種種滑動——文學批評就能揭穿層層二次修正,從而揭露潛文本的某些情況……”{11}對于電影而言,觀眾可以分析電影中反復出現的意象,發掘導演想說出而未說出的話,尋找電影意象背后的潛在意蘊。
電影《盜夢空間》,作為一種藝術生產,正是諾蘭的一個“白日夢”。影片中柯布的人格沖突,費雪的俄狄浦斯情結都是經過藝術處理后才展現出來的。整個影片充滿象征和隱喻。其中,影片頻繁出現“陀螺”“風車”和“保險箱”等意象。每一個意象背后都有一個潛文本,需要我們一一予以揭示。其中,影片視“陀螺”為一個圖騰,筑夢師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圖騰,這樣他們才能分清夢與醒。柯布的圖騰為陀螺。陀螺旋轉時證明是在夢中,陀螺停下來時意味著從夢中醒來。正是憑借陀螺,柯布才不至于迷失自己。每次陀螺出現的時候,也能幫觀眾分清夢與醒,陀螺的旋轉與停止成為夢與醒的界限。在茉兒的保險箱中,陀螺由靜止到旋轉的過程意味著柯布在茉兒的潛意識中植入了一個意念,顛倒了現實與虛幻。“植夢”的概念得到了一種藝術的呈現。而在影片的結尾,那個高速旋轉的陀螺似乎暗示這仍是在夢中,觀眾疑惑柯布回家的情節是夢還是醒時,整個影片戛然而止,給觀眾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
“風車”是老費雪父愛的象征,它出現在老費雪臥室床頭的照片中,小費雪十一歲的記憶中,以及老費雪的心靈深處。小費雪對父親既愛又恨的情感沖突在影片中多有表現。而當保險箱打開時,一個手工風車映入我們的眼簾時,小費雪和觀眾都被感動了。悔恨、感動和領悟都在小費雪的心靈中碰撞,小費雪徹底戰勝了俄狄浦斯情結,實現了人格的升華。
“保險箱”,帶密碼的保險箱,是人類無意識的象征。無意識往往沉淀在人類心靈深處,人們在正常的狀態下是無法察覺的。只有在夢、口誤和玩笑等活動中,無意識才會含蓄地呈現。而無意識的內容也需要人們詮釋才能突破二次修正,一層一層揭穿。影片中出現茉兒的保險箱,象征茉兒的無意識。茉兒把自己的記憶鎖進保險箱,她不愿意回到現實,她想和柯布永遠生活在他們構筑的世界中。柯布為了拯救茉兒,才在她的心靈植入“我們生活的世界不是真實的”這一意念,最終把茉兒推向了死亡之路。老費雪病床前的保險箱象征了老費雪的無意識,保險箱中陳放著一個手工風車、一份最后遺囑,暗示了老費雪的深沉父愛。當保險柜打開時,父與子的隔膜瞬間消逝,“俄狄浦斯情結”最終被克服。保險箱成為人類無意識的一種藝術化的呈現。
五、結語
《綜藝》評價:“《盜夢空間》是一部很聰明的電影,豐富的細節、錯綜復雜的敘事,將觀眾帶入一個潛意識的迷宮。諾蘭創造了一個超現實主義的驚悚世界,有點類似于榮格學說,在真實與非真實的多重層面上對觀者構成了挑戰。快速剪接和敏捷敘事把超現實的世界表現得酣暢淋漓,將虛擬影像技術呈現人腦的意識做到了登峰造極。”{12}影片被界定為科幻動作片,其中對人類無意識的開掘和表現是科幻片的內核。與其說電影與榮格學說類似,不如說它與弗洛伊德學說更貼近。《盜夢空間》是精神分析學在藝術中的成功演繹。
{1}{2}{5}{6}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林塵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頁,第199頁,第212頁,第213頁。
{3}{10}{11} 〔英〕特雷·伊格爾頓:《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頁,第186頁,第182頁。
{4}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
{7}{9}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趙立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頁,第156頁。
{8}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夢的解析》,彭潤金譯,廣東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2} 參見百度百科盜夢空間,2014年10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789436.htm?fr=aladdin
基金項目:2014年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西方后現代藝術的哲學性研究”的中期成果
作 者:張鑫,文學博士,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美學、藝術哲學。
編 輯:張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