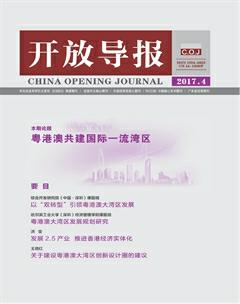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研究
[摘要] 粵港澳大灣區(qū)規(guī)劃是廣東積極投身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歷史機(jī)遇。未來應(yīng)加快沿海城市帶發(fā)展,以港深為核、珠江為軸、沿海為帶,形成“T”字型空間結(jié)構(gòu),發(fā)展包括五大城市圈等23座城市,構(gòu)成“一核一軸一帶五圈”的空間結(jié)構(gòu)。堅(jiān)持發(fā)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中央政府的統(tǒng)籌作用。以開放推動(dòng)轉(zhuǎn)型升級,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qū)對內(nèi)經(jīng)濟(jì)輻射功能與對外國際化水平。
[關(guān)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 一核一軸一帶五圈 “T”字型空間結(jié)構(gòu)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7)04-0013-07
一、灣區(qū)經(jīng)濟(jì)與粵港澳大灣區(qū)的戰(zhàn)略地位
灣區(qū)經(jīng)濟(jì)是世界經(jīng)濟(jì)的主體,是國際競爭的制高點(diǎn)。過去近70年,全球貿(mào)易出口貨物增長了 33倍,價(jià)值量增長了 155倍。沿海大都市在全球貿(mào)易中的地位愈發(fā)凸顯。優(yōu)越的地理區(qū)位、繁榮的港口經(jīng)濟(jì)、強(qiáng)大的海上運(yùn)輸能力、高密度的對外貿(mào)易、大規(guī)模的制造能力、超強(qiáng)的金融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使沿海港口城市集合構(gòu)成的灣區(qū)經(jīng)濟(jì)逐漸成為全球經(jīng)濟(jì)的主體。灣區(qū)經(jīng)濟(jì)依港而生,沿灣而興,港城互動(dòng),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全球 60%的經(jīng)濟(jì)總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 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yè)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 100公里的地區(qū)。世界著名灣區(qū)具有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qiáng)大的集聚外溢功能、發(fā)達(dá)的國際交流網(wǎng)絡(luò)等突出特點(diǎn),是世界 500強(qiáng)、創(chuàng)新公司、研發(fā)資源和專利密集區(qū),是國家競爭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代表,是推動(dòng)國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科學(xué)技術(shù)變革的先鋒。
粵港澳大灣區(qū)擁有得天獨(dú)厚的區(qū)位優(yōu)勢,與南海依灣相連,與東南亞隔海相望,是世界貿(mào)易的主要海運(yùn)通道,亞歐經(jīng)濟(jì)貿(mào)易銜接的核心點(diǎn),居國際金融和貿(mào)易核心地位,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jīng)之路、一帶一路的戰(zhàn)略咽喉重地,東向可聯(lián)通海西經(jīng)濟(jì)區(qū)、西拓可攜手廣西—東盟合作區(qū),是最具發(fā)展空間和增長潛力的世界級經(jīng)濟(jì)區(qū)域。粵港澳大灣區(qū)具有改革開放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先行優(yōu)勢,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高,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較完善,國際經(jīng)濟(jì)貿(mào)易聯(lián)系十分密切,在全球產(chǎn)業(yè)分工鏈條中形成了持續(xù)上升的能力,是我國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排頭兵。
二、粵港澳大灣區(qū)規(guī)劃的
空間范圍與發(fā)展條件
粵港澳大灣區(qū)規(guī)劃是我國第一部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跨行政區(qū)規(guī)劃①,是以華南沿海灣區(qū)優(yōu)越自然地理區(qū)位和既有城市群為依托的城市群規(guī)劃。建設(shè)粵港澳大灣區(qū),是廣東主動(dòng)承擔(dān)國家使命,積極投身一帶一路建設(shè),發(fā)揮重要樞紐作用的歷史機(jī)遇,是廣東加快發(fā)展,構(gòu)建改革開放新格局的重大契機(jī)。其空間范圍應(yīng)包括:位于珠江口河海相間中心位置的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澳門特別行政區(qū)、深圳、珠海,東起潮汕的汕頭、揭陽、汕尾、潮州,西至粵西的湛江、茂名、陽江的沿海地帶,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廣州、中山、江門、東莞、惠州、佛山以及位于灣區(qū)經(jīng)濟(jì)腹地和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的清遠(yuǎn)、韶關(guān)、河源、梅州、肇慶、云浮等 23座城市。國土面積 18.08萬平方公里,2016 年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 10.37 萬億元,總?cè)丝?1.2 億,分別約占全國的1.9%、13.9%、8.5%。初步形成了以港深為核心,珠江三角洲2區(qū)9市為主體的城市群。
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以香港和廣州兩個(gè)城市為起點(diǎn),初步成長為擁有近 6000 萬城市人口,城鎮(zhèn)化率達(dá)到 86%的世界級城市群。以約占全國 1%的面積,5%的人口,吸引了全國1/5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創(chuàng)造了占全國1/10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世界金融危機(jī)以來的經(jīng)濟(jì)平均增速仍保持 10%。
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qū)核心城市,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yè)務(wù)的樞紐,國際資產(chǎn)管理中心,是內(nèi)地與世界連接的“超級聯(lián)系人”,內(nèi)地跨境貿(mào)易、投融資和商務(wù)服務(wù)的國際化平臺(tái)。要發(fā)揮以香港帶動(dòng)沿海,沿海帶動(dòng)內(nèi)陸,逐級推動(dòng)、輻射帶動(dòng)灣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作用。借鑒國際著名灣區(qū)的成功發(fā)展經(jīng)驗(yàn),就要積極推進(jìn)港深合作,完成從行政區(qū)劃的多核心城市,走向市場機(jī)制決定的單核心城市轉(zhuǎn)變,發(fā)展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世界級灣區(qū)城市群,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qū)在世界經(jīng)濟(jì)中的地位。
深圳從 40 年前一個(gè)閉塞落后小漁村,一躍為全球重要的創(chuàng)新中心城市。港澳回歸祖國后,經(jīng)濟(jì)穩(wěn)定持續(xù)發(fā)展,粵港澳的關(guān)系進(jìn)入一個(gè)全新的歷史時(shí)期。CEPA新協(xié)議簽訂、廣東自貿(mào)試驗(yàn)區(qū)(南沙、前海和橫琴)正式運(yùn)行、一帶一路建設(shè)等多項(xiàng)措施落實(shí),粵港澳大灣區(qū)經(jīng)濟(jì)在持續(xù)推進(jìn)。港珠澳大橋、廣深港客運(yùn)專線等跨境重大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順利實(shí)施,粵港、深港間教育科學(xué)和產(chǎn)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合作不斷深化。粵港澳合力共建大灣區(qū)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
廣州是重要的全國經(jīng)濟(jì)中心城市,具有強(qiáng)有力的經(jīng)濟(jì)輻射與區(qū)域發(fā)展帶動(dòng)能力和物流集散功能,佛山、東莞、珠海、澳門等構(gòu)成灣區(qū)城市群的重要支撐;湛江、茂名、汕頭、揭陽等市是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群發(fā)展的重要增長極,是灣區(qū)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jīng)過近 40 年的快速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粵港澳大灣區(qū)初步形成了規(guī)模分布合理的多層次城市體系。其中,港深是灣區(qū)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yùn)樞紐和國際貿(mào)易窗口,是粵港澳大灣區(qū)的中央國際都會(huì)區(qū),也是中國創(chuàng)新能力最強(qiáng)、知名國際大學(xué)最多、城市活力國際影響力最高的城市區(qū),人口規(guī)模和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分別約占粵港澳大灣區(qū)的 16%和 36%。全球數(shù)字通信創(chuàng)新集群排名僅次于全球第一的東京—橫濱地區(qū);港深交易所總市值超過 6.5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三;擁有 2016年 QS全球排名前 100大學(xué) 4所;擁有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國際集裝箱樞紐港,集裝箱吞吐量位列全球第一,約占全球遠(yuǎn)洋集裝箱總運(yùn)量的 1/5。
當(dāng)前,粵港澳大灣區(qū)經(jīng)濟(jì)面臨雙重轉(zhuǎn)型壓力。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yōu)勢,高度重視香港的國際地位,充分發(fā)揮香港的作用,提高香港在大灣區(qū)建設(shè)發(fā)展中的核心地位,全面升華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間的經(jīng)濟(jì)合作水平,以更寬廣的視野、更強(qiáng)的國家使命感,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統(tǒng)籌規(guī)劃,對破解粵港澳大灣區(qū)面對的雙重轉(zhuǎn)型難題具有重大意義。
三、打造灣區(qū)特征突出的 T型城市群
推進(jìn)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群建設(shè),必須堅(jiān)持世界標(biāo)準(zhǔn),瞄準(zhǔn)國際標(biāo)桿,借鑒國際一流灣區(qū)的成功經(jīng)驗(yàn),充分發(fā)揮要素集聚和空間溢出效應(yīng),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和規(guī)模分布。未來應(yīng)加快沿海城市帶的發(fā)展,形成以港深為核、以沿海為帶、以珠江為為軸的“ T ”字型空間結(jié)構(gòu),建設(shè)相互協(xié)調(diào)、共同發(fā)展的五大城市圈—湛茂陽城市圈、澳珠中江城市圈、港深莞惠城市圈、廣佛肇城市圈和潮汕城市圈,構(gòu)成“一核一軸一帶五圈”的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群空間結(jié)構(gòu)。按照點(diǎn)、線、面逐步擴(kuò)展的方式,構(gòu)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灣區(qū)經(jīng)濟(jì)和城市布局,充分發(fā)揮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dòng)作用,培育形成多級多類發(fā)展軸線,多層次網(wǎng)絡(luò)化空間格局。
1. 著力建設(shè)多層次城市等級體系,打造傘形網(wǎng)狀城市規(guī)模層級結(jié)構(gòu)。堅(jiān)持政府引導(dǎo)與市場主導(dǎo)相結(jié)合,推動(dòng)大、中、小城市在空間上有序分布,促進(jìn)人口和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在地理上有效集聚,實(shí)現(xiàn)不同類型資源在不同空間上優(yōu)化配置,形成層級有序、分工合理、協(xié)同發(fā)展、聯(lián)系密切的傘形網(wǎng)狀城市層級體系,提高大灣區(qū)城市群的國際競爭力。
2. 明確等級清晰的城市功能定位。區(qū)分不同類型城市職責(zé),鼓勵(lì)核心大城市打造面向未來的全球城市,成為全球城市文明創(chuàng)新的倡導(dǎo)者,全球科技創(chuàng)新和智能制造的引領(lǐng)者;推動(dòng)大城市打造現(xiàn)代化、國際化城市,建設(shè)國家創(chuàng)新城市、國際制造名城;引導(dǎo)中小城市建設(shè)區(qū)域中心,成為現(xiàn)代生態(tài)城市、地方特色城市。
3. 推動(dòng)層次合理的城市產(chǎn)業(yè)分工。注重城市產(chǎn)業(yè)專業(yè)化分工,加快核心大城市發(fā)展科技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建設(shè)世界級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資源配置中心;推動(dòng)大城市發(fā)展創(chuàng)新服務(wù)業(yè)、科技制造業(yè),建設(shè)特色鮮明的世界級高端制造業(yè)集群;引導(dǎo)中小城市建設(shè)區(qū)域商貿(mào)中心、物資集散中心和先進(jìn)制造中心。遵循灣區(qū)城市群一般演進(jìn)規(guī)律,打造“以港深國際大都會(huì)為引擎、五大城市圈為支撐”的粵港澳大灣區(qū)傘形網(wǎng)狀城市群。加快五大城市圈之間互聯(lián)互通。高度重視城市圈之間重大基礎(chǔ)設(shè)施的高效銜接,超前布局連接五大城市圈的新一代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有序轉(zhuǎn)移與有效集聚,引導(dǎo)五大城市圈之間人流、資金流、信息流自由暢通,推動(dòng)各個(gè)城市圈的密切互動(dòng)、錯(cuò)位協(xié)同、有效競爭。
4. 建設(shè)功能清晰、分工合理的核、軸、帶。按照打造世界級灣區(qū)核心城市要求,加快提升港深核心競爭力和綜合服務(wù)功能,充分發(fā)揮港深輻射帶動(dòng)和示范引領(lǐng)作用,推動(dòng)非核心功能疏解,推進(jìn)珠海、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協(xié)同發(fā)展,引領(lǐng)城市群一體化發(fā)展。推動(dòng)沿海灣區(qū)城市高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加大國際貿(mào)易、國際投資的沿海優(yōu)勢,著力發(fā)揮東部、西部沿海城市的地緣優(yōu)勢,加強(qiáng)以汕頭、湛江為中心的東西部港口城市建設(shè),大力發(fā)展以港深為核心的沿海灣區(qū)城市帶,推動(dòng)沿海灣區(qū)城市帶高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輻射帶動(dòng)灣區(qū)內(nèi)陸城市經(jīng)濟(jì)全面發(fā)展。強(qiáng)化廣州作為全國經(jīng)濟(jì)中心城市,升華廣州經(jīng)濟(jì)、文化、教育、區(qū)域交通樞紐地位,對于帶動(dòng)粵港澳大灣區(qū)周邊內(nèi)陸地區(qū)的發(fā)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要提升佛山的綜合服務(wù)功能,承接、傳遞區(qū)域輻射帶動(dòng)力。加快重型裝備制造業(yè)、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和物流業(yè)的發(fā)展,改善城市圈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加快外圍組團(tuán)的環(huán)境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共同維護(hù)區(qū)域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人居環(huán)境載體。
5. 提升城市空間利用效率。粵港澳大灣區(qū)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形成了通訊電子信息產(chǎn)業(yè)、新能源汽車、無人機(jī)、機(jī)器人等新興產(chǎn)業(yè)集群,以及石油化工、服裝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飲料等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集群。但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不足、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過度集中在中低端環(huán)節(jié),各地過度競爭、同質(zhì)化現(xiàn)象仍然突出。根據(jù)資源環(huán)境承載能力,提升空間利用效率,優(yōu)化粵港澳大灣區(qū)國土空間開發(fā)格局,應(yīng)科學(xué)確定城市邊界、最小生態(tài)安全距離和空間結(jié)構(gòu),統(tǒng)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人口空間分布、陸海資源利用、生態(tài)建設(shè)和環(huán)境保護(hù)、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和對內(nèi)對外開放。應(yīng)從提升區(qū)域整體競爭力出發(fā),處理沿海沿江城市與腹地城市、中心城市與中小城市的關(guān)系,明確城市功能定位,強(qiáng)化錯(cuò)位發(fā)展,形成優(yōu)勢互補(bǔ)、各具特色的協(xié)同發(fā)展格局。
四、提升粵港澳大灣區(qū)競爭力的政策措施
1. 推動(dòng)粵港澳大灣區(qū)人口的合理分布。強(qiáng)化產(chǎn)業(yè)升級和功能疏解是粵港澳大灣區(qū)人口合理分布的“兩大抓手”,可穩(wěn)定粵港澳大灣區(qū)軸線上超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密度,扭轉(zhuǎn)人口過度向粵港澳大灣區(qū)軸線集中的現(xiàn)狀,綜合運(yùn)用土地供給、土地價(jià)格及城市功能調(diào)整等手段,推動(dòng)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產(chǎn)業(yè)向高空間收益、高創(chuàng)新收益的數(shù)字產(chǎn)業(yè)等領(lǐng)域升級。增強(qiáng)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心城區(qū)的創(chuàng)新服務(wù)功能,提升城市空間效率,建設(shè)發(fā)達(dá)的通勤交通體系;提高東西部沿海城市帶的人口密度,2025 年城鎮(zhèn)常住人口密度應(yīng)接近2010 年珠江三角洲軸的水平。產(chǎn)業(yè)集聚帶動(dòng)人口集聚,發(fā)揮東西部沿海城市區(qū)位優(yōu)勢,發(fā)展大型臨港經(jīng)濟(jì)、海洋經(jīng)濟(jì)和特色產(chǎn)業(yè)。通過加大產(chǎn)業(yè)擴(kuò)散效應(yīng),形成新的產(chǎn)業(yè)集聚空間,推動(dòng)超大城市大規(guī)模制造業(yè)向東西部城市群擴(kuò)散,提升都市群整體空間效率。加大鋼鐵、石油化工、造船等產(chǎn)業(yè)向東西部沿海地區(qū)擴(kuò)散。以湛茂陽、潮汕兩大城市圈為重點(diǎn),加快東西部沿海城市帶一體化;促進(jìn)城市擴(kuò)容提質(zhì),加快布局教育、醫(yī)療和養(yǎng)老等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塑造山海相應(yīng)、自然共融的城市環(huán)境,吸引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深入貫徹習(xí)近平總書記關(guān)于“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講話,切實(shí)保障粵港澳大灣區(qū)北部腹地的生態(tài)屏障功能,保持低人口密度的發(fā)展格局,北部地區(qū)以構(gòu)建生態(tài)文明先行區(qū)為目標(biāo),構(gòu)建粵港澳大灣區(qū)北部環(huán)形生態(tài)屏障。
2. 推動(dòng)實(shí)施創(chuàng)新發(fā)展戰(zhàn)略。發(fā)揮粵港澳大灣區(qū)在科技產(chǎn)業(yè)、金融服務(wù)業(yè)、航運(yùn)物流業(yè)和制造業(yè)的核心優(yōu)勢,打造從創(chuàng)新源頭至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的分工合理、體系完備的產(chǎn)業(yè)鏈,提高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速度,增強(qiáng)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質(zhì)量。建設(shè)以港深為創(chuàng)新核心,輻射全灣區(qū)的內(nèi)聚外合的開放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形成創(chuàng)新要素聚集、科技產(chǎn)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新生態(tài)成熟的世界級科技灣區(qū)。港深共建全球領(lǐng)先的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要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充分發(fā)揮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特殊優(yōu)勢,加快港深科技金融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加速創(chuàng)新鏈、產(chǎn)業(yè)鏈和資本鏈的有效合作。建立空間相聯(lián)、產(chǎn)業(yè)相關(guān)的開放型區(qū)域創(chuàng)新體系,加強(qiáng)粵港澳科技創(chuàng)新合作,深入推進(jìn)粵港澳大灣區(qū)科技創(chuàng)新走廊、深港創(chuàng)新圈建設(shè),制定粵港澳科技合作發(fā)展計(jì)劃。讓香港在國際化的稅制、法制以及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等方面的獨(dú)特優(yōu)勢,與灣區(qū)內(nèi)產(chǎn)業(yè)配套完善的優(yōu)勢充分對接,匯聚世界級創(chuàng)新人才和創(chuàng)新資源,形成全球高端科技匯集地、全球產(chǎn)業(yè)革命重要策源地。
3. 推動(dòng)粵港澳大灣區(qū)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加快建設(shè)港深世界級金融中心,全面提升廣州區(qū)域金融中心競爭力,著力培育若干金融節(jié)點(diǎn)城市,逐步形成層次分明、專業(yè)分工、協(xié)調(diào)有序的粵港澳金融中心體系,積極推動(dòng)粵港澳大灣區(qū)形成比肩紐約灣區(qū)、倫敦灣區(qū)的金融領(lǐng)域全球競爭力。強(qiáng)化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交易中心地位,完善以港深為核心的金融科技產(chǎn)業(yè)鏈條,探索港深債券交易平臺(tái)、IPO市場互聯(lián)互通,推動(dòng)港深共建世界級融資中心和創(chuàng)投中心。
4. 推動(dòng)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空間集聚。推動(dòng)信息技術(shù)基礎(chǔ)創(chuàng)新,打造信息基礎(chǔ)產(chǎn)業(yè)新優(yōu)勢。建設(shè)石墨烯、碳納米管等前沿技術(shù)創(chuàng)新載體,推動(dòng)軟件定義網(wǎng)絡(luò)(SDN)、網(wǎng)絡(luò)功能虛擬化(NFV)等未來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試驗(yàn)驗(yàn)證和應(yīng)用示范。發(fā)展跨界融合的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群,積極構(gòu)建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產(chǎn)業(yè)集群。超前布局互聯(lián)互通的大灣區(qū)新一代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拓展安全有序的網(wǎng)絡(luò)空間,推進(jìn)信息產(chǎn)業(yè)化、產(chǎn)業(yè)智能化、城市智慧化,逐步建成粵港澳大灣區(qū)世界級智慧城市群。開展產(chǎn)業(yè)區(qū)域分工協(xié)作,形成產(chǎn)業(yè)鏈延長和產(chǎn)業(yè)互補(bǔ)、融合的發(fā)展格局。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建設(shè)不同層次、不同領(lǐng)域的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在珠江東岸打造一批具有全球領(lǐng)先水平的電子信息產(chǎn)業(yè)集群。加快建設(shè)珠江西岸世界級先進(jìn)裝備制造產(chǎn)業(yè)帶。打造東西部沿海新型產(chǎn)業(yè)帶。建設(shè)以核電與天然氣為主體的清潔能源基地,提升以進(jìn)口原油為支撐的精細(xì)化工產(chǎn)業(yè)集群,打造以進(jìn)口鐵礦石為基礎(chǔ)的精品鋼材產(chǎn)業(yè)園區(qū),形成獨(dú)具特色、競爭力強(qiáng)的大規(guī)模臨港經(jīng)濟(jì)帶、現(xiàn)代化物資集散中心。以潮汕城市圈為依托,打造汕頭區(qū)域交通樞紐、科技中心和商貿(mào)物流中心,打造潮州重要臨港產(chǎn)業(yè)基地、特色經(jīng)濟(jì)示范區(qū),打造揭陽區(qū)域航空物流基地、重要石化能源基地,打造汕尾濱海旅游集聚地、省級電子信息產(chǎn)業(yè)基地。以湛茂陽城市圈為依托,建設(shè)湛江全國海洋經(jīng)濟(jì)示范市、重化產(chǎn)業(yè)基地,建設(shè)茂名區(qū)域重要交通樞紐、世界級石化產(chǎn)業(yè)基地、重要能源物流基地。
5. 推動(dòng)創(chuàng)新中心與制造基地密切合作。鼓勵(lì)核心新興產(chǎn)業(yè)關(guān)鍵技術(shù)跨地域合作創(chuàng)新,建設(shè)若干具有強(qiáng)大帶動(dòng)力的創(chuàng)新型城市和區(qū)域創(chuàng)新中心,增強(qiáng)制造業(yè)設(shè)計(jì)、制造、材料、質(zhì)量體系的綜合競爭力,形成從創(chuàng)新源頭到產(chǎn)品設(shè)計(jì)、生產(chǎn)的全產(chǎn)業(yè)鏈競爭優(yōu)勢。支持灣區(qū)內(nèi)各市積極參與國家自創(chuàng)區(qū)建設(shè)并創(chuàng)建創(chuàng)新型城市。實(shí)行“兩推動(dòng)”策略,推動(dòng)總部—研發(fā)—制造全產(chǎn)業(yè)鏈在粵港澳大灣區(qū)集聚;推動(dòng)總部、研究開發(fā)和制造過程,按照城市發(fā)展水平和產(chǎn)業(yè)特征進(jìn)行差異化配置。提升大灣區(qū)內(nèi)部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密度”和“濃度”,加強(qiáng)港深莞數(shù)字技術(shù)與產(chǎn)業(yè)合作,切實(shí)發(fā)揮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的驅(qū)動(dòng)作用,將數(shù)字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促進(jìn)深港金融科技中心、數(shù)字技術(shù)中心、生物技術(shù)研發(fā)中心建設(shè),形成創(chuàng)新能力強(qiáng)、產(chǎn)業(yè)分工合理、體系完備的世界級創(chuàng)新城市群。推進(jìn)珠江兩岸制造業(yè)錯(cuò)位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積極構(gòu)建粵港澳、粵閩、粵桂瓊?cè)蠛Q蠼?jīng)濟(jì)合作圈。以“六灣區(qū)一半島”為單元,重點(diǎn)建設(shè)一批集中集約用海區(qū)、海洋產(chǎn)業(yè)集聚區(qū)和濱海經(jīng)濟(jì)新區(qū),推動(dòng)海陸空間統(tǒng)籌利用試點(diǎn),構(gòu)建海洋經(jīng)濟(jì)新格局。
6. 推動(dòng)珠江軸與沿海帶之間的交通均衡。建立疏密有序高效便捷的灣區(qū)交通體系。由單一城市交通中樞向多元、多向、多樞紐,軸與帶城市直聯(lián)直通網(wǎng)絡(luò)體系轉(zhuǎn)變,提升沿海城市帶的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加快沿海城市跨江通道建設(shè)。改變沿海城市帶交通基礎(chǔ)建設(shè)嚴(yán)重滯后的局面。目前,珠江三角洲軸線城市單位面積的交通運(yùn)輸能力是東西部沿海城市的 8倍。珠江三角洲軸線城市的鐵路密度是沿海城市帶鐵路密度的 2.8倍;高等級路和高速公路運(yùn)輸能力是沿海城市帶的2倍。
要強(qiáng)化基礎(chǔ)設(shè)施對粵港澳大灣區(qū)城市群協(xié)同發(fā)展的基礎(chǔ)性作用,超前建設(shè)東西部城市圈的城際鐵路,提高高速鐵路的通達(dá)性,到 2030 年應(yīng)當(dāng)基本消除東西部沿海城市與粵港澳大灣區(qū)軸線城市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水平差距。截至 2015 年,珠江三角洲城市軸的公路總長度 78334公里,2005~2020年珠江三角洲城市軸公路計(jì)劃修建長度為 1780.6公里,2020年底計(jì)劃總長度達(dá) 80114公里,公路密度預(yù)計(jì)將達(dá)到 1.95千米/平方公里;粵港澳大灣區(qū)東西部沿海地區(qū)城市公路總長度為 68961公里,2009~2020年共計(jì)劃修建公路 508.7公里,東西沿海公路密度預(yù)計(jì)達(dá) 1.474 公里/平方公里設(shè)施覆蓋范圍,遠(yuǎn)低于珠江三角洲軸線城市公路基礎(chǔ)設(shè)施計(jì)劃建設(shè)數(shù)量。
要著力加快粵港澳地區(qū)沿海港口群建設(shè),優(yōu)先發(fā)展沿海港口,優(yōu)化提升內(nèi)河港口,形成以沿海港口為主體,內(nèi)河港口為補(bǔ)充的多樣化、多層次、多功能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世界級港口群。發(fā)揮沿海港口群對內(nèi)輻射的功能;構(gòu)建以沿海主要港口為核心的國際貨物運(yùn)輸通道和以空港為核心的快速國際物流集疏運(yùn)網(wǎng)絡(luò),發(fā)揮東西部港口與鐵路結(jié)合的交通運(yùn)輸網(wǎng)對腹地經(jīng)濟(jì)的帶動(dòng)作用,形成沿海港口對腹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支撐和促進(jìn)臨港工業(yè)發(fā)展的能力。
要著力提升港深交通樞紐地位,建設(shè)以汕頭、汕尾、湛江、陽江等沿海地區(qū)為港口運(yùn)輸與鐵路運(yùn)輸?shù)倪B接樞紐;建立東部港口與潮汕地區(qū)及贛閩聯(lián)通的鐵路網(wǎng),建立東部潮汕港口群對灣區(qū)北部腹地城市以及桂黔地區(qū)的高密度輻射鐵路網(wǎng)。重點(diǎn)推進(jìn)深圳至茂名鐵路、梅州至潮汕鐵路、合浦至湛江鐵路、贛州至深圳客運(yùn)專線、廣州至汕尾客運(yùn)專線、汕尾至汕頭鐵路(兼顧城際)、龍川至龍巖客運(yùn)專線、湛江至海口鐵路擴(kuò)能工程、張家界經(jīng)湛江至海口旅游高鐵等項(xiàng)目建設(shè)。完善經(jīng)粵東西至周邊省(區(qū))高速鐵路通道建設(shè),形成東聯(lián)海峽西岸、溝通長三角,西通桂黔、輻射大西南,北達(dá)湘贛、連接中原地區(qū)的“五縱二橫”高速鐵路骨干網(wǎng)絡(luò)。
五、推進(jìn)觀念轉(zhuǎn)變,深化改革,擴(kuò)大開放
1. 轉(zhuǎn)變觀念。建設(shè)粵港澳大灣區(qū)就是要從傳統(tǒng)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獨(dú)立城市形態(tài)向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的城市群轉(zhuǎn)變,要打破畫地為牢行政分割,資源過度集中,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異顯著的空間格局,充分發(fā)揮城市間的動(dòng)態(tài)比較優(yōu)勢,形成各具特色,相互關(guān)聯(lián),科技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能力強(qiáng),交易成本低、金融實(shí)力強(qiáng)大的全產(chǎn)業(yè)鏈國際競爭優(yōu)勢。從傳統(tǒng)金融中心、服務(wù)中心、制造中心向多元復(fù)合型的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轉(zhuǎn)變。按照城市規(guī)模與發(fā)展水平,依照比較優(yōu)勢向“總部經(jīng)濟(jì)+金融中心+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高端制造業(yè)中心”、“總部運(yùn)營中心+研發(fā)中心+制造中心”等多種復(fù)合創(chuàng)新模式轉(zhuǎn)變。
2. 深化改革。堅(jiān)持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中央政府規(guī)劃統(tǒng)籌作用,充分發(fā)揮改革試驗(yàn)田作用,增創(chuàng)改革新優(yōu)勢,優(yōu)化公共資源配置,推進(jìn)統(tǒng)籌城鄉(xiāng)、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跨行政區(qū)的綜合改革試驗(yàn)區(qū)建設(shè),創(chuàng)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科學(xué)發(fā)展新體制,率先建成比較完善的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以港深大都市區(qū)建設(shè)帶動(dòng)粵港澳大灣區(qū)經(jīng)濟(jì)合作;支持深圳大力建設(sh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yàn)區(qū);支持珠海在政府職能分層管理改革、社會(huì)管理制度創(chuàng)新等方面取得新進(jìn)展;支持汕頭經(jīng)濟(jì)特區(qū)擴(kuò)大至全市范圍,在對外合作、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的體制機(jī)制創(chuàng)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著力推進(jìn)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地區(qū)金融科技創(chuàng)新先行先試。強(qiáng)化港深在推動(dòng)灣區(qū)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中的核心作用,保持港深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著力提升大灣區(qū)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與產(chǎn)業(yè)競爭力。
3. 擴(kuò)大開放。提升粵港澳大灣區(qū)經(jīng)濟(jì)國際化水平,以開放推動(dòng)轉(zhuǎn)型升級,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核心,加強(qiáng)區(qū)域合作,優(yōu)化利用外資結(jié)構(gòu),提高“走出去”水平。構(gòu)建規(guī)范化、國際化的營商環(huán)境,推動(dòng)全面開放、深度開放、科學(xué)開放,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lǐng)域、高水平的開放型經(jīng)濟(jì)新格局。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國兩制”、政策空間優(yōu)勢,以港深為主體,創(chuàng)造出最具活力,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創(chuàng)新機(jī)制,將落馬洲打造成為全球最著名的創(chuàng)新基地之一。
4. 全面提升對內(nèi)輻射功能。全面推進(jìn)粵港澳大灣區(qū)、珠江—西江經(jīng)濟(jì)帶、粵桂黔滇高鐵經(jīng)濟(jì)帶、瓊州海峽經(jīng)濟(jì)帶和東江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帶等跨區(qū)域合作,強(qiáng)化對內(nèi)輻射功能,深化粵港澳、粵閩、粵桂瓊等海洋經(jīng)濟(jì)合作圈的協(xié)同發(fā)展。充分發(fā)揮各類合作平臺(tái)在促進(jìn)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中的積極作用,大力推進(jìn)廣州泛珠合作園區(qū)、粵桂黔高鐵經(jīng)濟(jì)帶合作試驗(yàn)區(qū)建設(shè),支持粵桂合作特別試驗(yàn)區(qū)、閩粵經(jīng)濟(jì)合作區(qū)、北部灣臨海產(chǎn)業(yè)園、湘贛開放合作試驗(yàn)區(qū)等跨省區(qū)合作平臺(tái)發(fā)展,形成粵港澳大灣區(qū)與周邊內(nèi)陸省區(qū)合作發(fā)展、聯(lián)運(yùn)發(fā)展的新格局。
[參考文獻(xiàn)]
[1] Anderson, G. and Ge, Y. (2005).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5 (6), 756-776.
[2] Bertinellia, L. and Black, D. (2004).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6 (1), 80-96.
[3] Berger, T. and Frey, C. B. (2015). Di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shift the fortunes of U.S. cities? Technology shocks and the geography of new job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57, 38-45.
[4] Boustan, L. P., Bunten, D., and Hearey, O. (2013).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2000 [R]. NBER Working Papers 1904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5] Chatterji, A., Glaeser, E. L., Kerr, W. R. (2013).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0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6] Chauvin, J. P., Glaeser, E., Ma, Y. and Tobio, K. (2016).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urbaniza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Cities in Brazil,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00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7] Davis, D. R. and Dingel, J. I. (2012).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ities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060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8] Davis, D. R. and Dingel, J. I. (2013). A spatial knowledge economy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818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9] Delgado, M., Porter, M. E. and Stern, S. (2014). Clusters, converge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Research Policy, 43 (10), 1785-1799.
[10] Desmeta, K. and Rappaport, J. (2015). The settl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800–2000: The long transition towards Gibrats law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98, 50-68.
[11] Diamond, R. (2016).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3), 479-524.
[12] Duranton, G., Henderson J. V. and Strange W. (2015).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5A [C]. North Holland (Elsevi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13] Ellison, G. and Glaeser, E. L. (1997).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dartboard approach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5), 890-927.
[14] Glaeser, E. L. and Gottlieb, J. D. (2009). The Wealth of Citie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 (4), 983-1028.
[15] Glaeser, E. L. and Resseger, M. G. (2010).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skill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0 (1), 221–244.
[16] Gyourko, J., Mayer, C., and Sinai, T. (2013). Superstar citie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 (4), 167-99.
[17] Glaeser, E. L., Ponzetto, G. A. M. and Tobio, K. (2011). Cities, Skills, and Regional Change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693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8] Huang, K. G.-L. andGeng, X. (2017). Institutional regime shift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of firms in China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8 (2), 355-377.
[19] Jaworski, T. and Kitchens, C. T. (2016). National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ppalachian Highways [R].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20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 Kerr, W. R. and Kominers, S. D. (2015). Agglomerative forces and cluster shape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 (4), 877-899.
(其余參考文獻(xiàn)略)
Abstract: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planning is Guangdong government seiz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getting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city zone, so as to form a “T”-shape spatial structure with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s the core, the Pearl River as the axis, and the coastal cities as the belt,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23 cities in five City Clusters. As a result, a spatial structure of “A Core, An Axis, A Belt, and Five City Clusters” with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ch was established and should be consolidated. It is advocated that the following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ha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y through opening up, so as to enhance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economic radiation function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
Keywords:Planning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Core, An Axis, A Belt, and Five City Clusters; “T”-shape Special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17-07-26 責(zé)任編輯:余 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