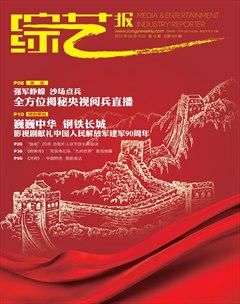影城院線新課題
趙軍
城鎮化對于影城建設的要求是放大社交場所的功能,即增加影城的社交屬性,這一點是當下影城管理的新課題,也是院線建設的新課題。
有些事情有錢可以搞定,比如蓋一座商城,修一條高速公路;再比如電影院,現在蒙資本厚愛有如雨后春筍般興建。但很多事情需要“有錢的”聽聽“有見識的”。近年來影城數量的增幅有增無減,投資者和管理者都希望大市場能與自己手上的銀幕增幅同步。但市場的同步不僅是行業能否拍出好影片所能決定的,我們必須把整個產業看作一個大的系統。
經過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電影產業享有的進化信息已經從巨量涌入變成了緩量加持。新的說法是電影產業進入了“新常態”。應該看到,中國電影產業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并非完全靠源源不斷的佳作促成。“爛片”的高票房也是一些人所樂見其成的,況且孰為“爛片”完全見仁見智。
電影產業的高速發展是受多元因素影響的生成過程。首先是中國的城鎮化速度。沒有2000年到2010年的城鎮化高速發展帶來的巨量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電影市場。2001年電影《我的兄弟姐妹》憑2400萬元票房就站上當年國產電影的亞軍寶座。現在,一部好電影過億已是常態。這是時代的力量。
就電影院的建設而言,并非如“雨后春筍”般增長就能解決城鎮化的需求。城鎮化對于影城建設的要求是放大社交場所的功能,即增加影城的社交屬性,這一點是當下影城管理的新課題,也是院線建設的新課題。
其次是社會觀念已經改變了的“90后世界”。90后只是時代概念,我們都是“90后”,因為有著同樣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城鎮化人口暴漲進入平緩態后,它所帶來的新世界觀也同樣進入“新常態”。這個世界觀不是別的,正是認同世界沒有所謂“中心”。這是互聯網時代的世界觀,因為網絡世界不存在中心,只在乎你在哪個節點上,或者說在哪個“結點”上。
電影產業界對于這個時代的轉變并沒有做好準備。基因跟不上,一切跟不上。我們的理論界對互聯網世界的觀念變革并未表現出敏感,大多數人幾乎不關注90后的網站和App。一些評論界的自媒體可能反應較迅速,但仍局限在很古典地進行“分析”“歸納”“綜合”,只停留于觀點的切入和充當現實的“解釋先生”。而90后的表達是“喜歡”,這是我們未必懂的。
再次是新世界應用市場的開發。中國電影產業的高速發展原因之一是在城市的新文明背景下,新人類找到了電影院作為社交場所(應用市場),或者說,我們順天應人地創造了可以為新文明新人類所用的社交天地。影城正是這個“新世界”的應用市場。電影發行則是為影片開掘應用市場的再發明和再創造,沒有這個開發,我們也許永遠都停留在“好片”“爛片”的爭執當中。
這里不爭論什么是好片什么是爛片,這些都要經受市場和時間的檢驗,都要每一家發行公司和每一條院線及每一座影城自己去體會。如果你有信心做好應用市場的開發,那么真正有價值的是你——“發行”和“影城院線”,而不是“影片”。影片每一部就是那一部,不可以復制,而你可以復制,因此,你代表市場,你代表商業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