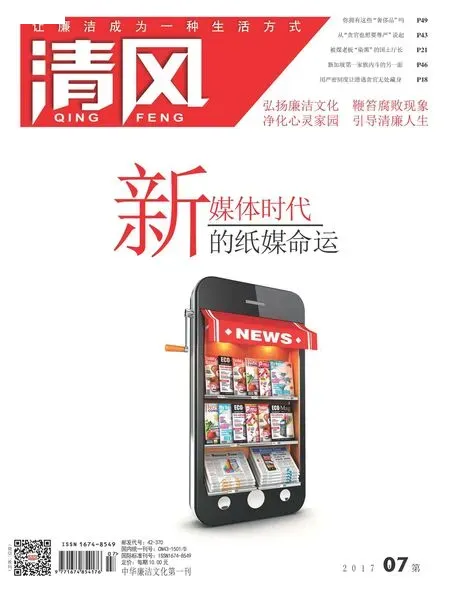用嚴密制度讓潛逃貪官無處藏身
——本刊專訪二十國集團(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新林
采訪_本刊記者 化定興(發自北京海淀)
用嚴密制度讓潛逃貪官無處藏身
——本刊專訪二十國集團(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新林
采訪_本刊記者 化定興(發自北京海淀)

彭新林
腐敗分子外逃以及大量腐敗資金外流,除了助長腐敗的囂張氣焰,也會沖擊資產流入國的經濟金融秩序,損害其人民利益和國家形象,損害其法治尊嚴和反腐敗成效。攜手打擊跨國(境)腐敗,加強反腐敗追逃追贓國際合作,不僅是我國反腐敗工作的現實需要,也是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訴求。那么,追逃追贓目前存在哪些難點?應該如何破局?就這個話題,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二十國集團(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新林(以下簡稱“彭”)。
腐敗分子有“撈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心態
記:在當今全球化時代,腐敗已成為困擾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世界性難題,且越來越呈現出跨國(境)發展趨勢,腐敗分子外逃出境會造成什么危害?
彭:腐敗分子出逃境外通常有一定主動性和計劃性,大多是抱持“撈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心態,往往在出逃前縝密謀劃,有意識地向境外轉移非法獲得的資產,或者安排配偶子女出國,一有“風吹草動”,立馬逃之夭夭。腐敗分子外逃的國家相對較為集中,主要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西方發達國家。腐敗分子選擇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作為“避罪天堂”,除了向往優越的生活條件外,主要是這些國家尚未與我國簽訂引渡、刑事司法協助等條約,使得他們出逃后較易逃脫法律制裁。
腐敗分子外逃出境尤其是攜款潛逃,具有嚴重的危害性。首先,其阻礙國家對腐敗分子的刑事追訴,增加了懲治腐敗犯罪的難度和成本,影響反腐敗斗爭的成效。其次,腐敗分子頻頻成功外逃,若不能加以有效制裁,勢必會對國內潛在的腐敗分子起到負向激勵的作用,降低司法威懾力,損害國家的法制尊嚴和司法權威。再次,會對國家安全利益造成潛在威脅。有些外逃的腐敗分子,由于之前掌握國家有關領域重要機密內容,他們外逃后,容易被境外敵對勢力收買拉攏,對我國政治、軍事、經濟安全造成潛在威脅。最后,也會沖擊逃入國的金融市場秩序。腐敗分子出逃前必定會想方設法向境外轉移非法資產,而巨額非法資金的涌入,勢必會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和不穩定因素。
正是如此,做好反腐敗境外追逃工作,將腐敗分子緝捕回國,讓其接受法律制裁,就十分必要。這是新形勢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的客觀需要,有利于消除腐敗分子妄圖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更好地維護我國司法主權和國家利益,增強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反腐敗境外追逃追贓既是我國反腐敗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必須要抓好的重大任務,關系到國家形象和人民利益,關系到法治尊嚴和反腐敗成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深刻地指出:“要加大境外追逃追贓力度,推動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多邊框架下的國際合作,實施重大專項行動,把懲治腐敗的天羅地網撒向全球,讓已經潛逃的無處藏身,讓企圖外逃的丟掉幻想。”

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在北京設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出席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要破解境外追逃的法律障礙
記:既然腐敗分子外逃出境危害如此之大,那么有沒有有效的追逃方式?
彭:境外追逃的主要方式,除了引渡,還有引渡的常規和非常規的替代措施,以此解決無雙邊引渡條約情況下的追逃問題。引渡的常規替代措施有遣返、勸返、境外刑事訴訟等方式。這些常規的替代措施都是在有關國家法律制度的框架內適用的,得到了各國的普遍認可。引渡的非常規替代措施如綁架、誘騙等方式,即“某些可據以繞過引渡的法律障礙或困難進而實現將在逃人員境外捉拿歸案之目的的手段”。這些非常規的替代措施,由于有侵犯相關國家的主權和個人人權之虞,正當性上存在較大爭議,只在極少數特定情況下才使用。回視國內,從近年來反腐敗境外追逃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已初步形成了引渡、遣返、勸返和異地刑事追訴等多種追逃方式并存、相互補充、重點突出的境外追逃方式體系,已成功地將一批外逃的腐敗分子緝捕歸案,效果比較明顯。
引渡是反腐敗境外追逃的基本方式。在國際法上,國家沒有引渡人犯的義務,除非它根據條約承擔了這種義務。在沒有條約的約束下,國家是否向他國引渡人犯,則取決于多種因素。截至目前,我國已與40余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包括澳大利亞、法國、韓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加入含有司法協助、引渡等內容的30多項多邊公約,這為我國打擊犯罪,與相關國家開展引渡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
而所謂遣返,是指通過吊銷有關人員的合法旅行證件、證明有關人員犯有嚴重罪行等手段,設法使該人不能在躲藏地國家獲得合法的居留地位或者剝奪已獲得的居留地位,從而達到將其遣送回國的目的。由于不同國家在法律制度、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差異,國家之間未必均有引渡條約或者可能簽訂引渡條約,故而在反腐敗國際合作的大背景下,更需尋求其他引渡替代措施,以達到與引渡相同的結果。遣返就是這樣一種重要的替代措施。
然而,根據有關國際公約和某些國家移民法的規定,在兩種情況下不得遣返:一是被遣返回國后可能因種族、宗教、政治見解等原因受到迫害;二是被遣返回國后可能遭受酷刑或刑訊逼供。正是如此,遣返要想取得引渡的效果,則不僅需要積極配合逃入國對腐敗分子違反該國移民法規定的認定,為該國提供腐敗分子違法犯罪線索、安排相關證人前往出庭作證,或者協助逃入國司法機關到我國取證等司法協助,而且還需要贏得逃入國對我國刑事訴訟活動的理解和認可,使其信任我國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對人權的充分保障。而這些要么程序繁雜、周期過長,要么在短期內難以改變,故而勢必會影響遣返的效果。
所以,我認為,要加快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有關規定的銜接,破解境外追逃的法律障礙;探索組建一支境外追逃追贓的專門隊伍;加強主管機關境外追逃的技術力量;繼續深化司法改革,樹立司法公正形象;通過這些方式改進我國境外追逃工作。
境外追贓須多措并舉
記:追逃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追贓,大量腐敗資產轉移至境外對我國危險太大。
彭:是的。在當前國內高壓反腐的態勢下,一些腐敗分子猶如“驚弓之鳥”,想方設法向境外轉移腐敗資產。如有的秘密取得國外永久居民身份,通過地下錢莊等渠道將腐敗資產轉移境外;有的通過在境外購房、開公司、投資、炒股等方式,將腐敗資產“合法”轉移到境外;有的將子女等近親屬送往國外學習、定居,里應外合,共同洗錢;還有的讓行賄人直接將賄賂款存入在境外開設的賬戶。
大量腐敗資產轉移境外,對我國經濟、政治、法治以及國家形象都具有嚴重的危害。其一,腐敗分子非法獲得并轉移至境外的腐敗資產,往往是來源于企事業單位的國有資產或者通過權錢交易所得,這一方面會直接給國家財產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損失,另一方面也會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消解或者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企業和市場的交易成本,嚴重影響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其二,無形中會形成負面激勵和示范,勢必刺激潛在的一些腐敗分子鋌而走險,形成惡性循環,惡化政治生態,而且也會損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其三,腐敗資產轉移境外也嚴重影響腐敗案件的查處,大大提高司法成本,降低司法威懾力,進而會直接削弱國家反腐倡廉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整體效果。
記:那么據您的研究,破解我國反腐敗境外追贓有哪些好的建議?
彭:做好新形勢下我國反腐敗境外追贓工作,需要綜合施策、多措并舉。
第一,境外追贓與境外追逃雙管齊下,以追逃促追贓,形成境外追贓追逃的整體合力。既要大力開展分享和返還腐敗資產的國際合作,摧毀腐敗分子在境外生存的物質基礎,擠壓其生存空間,迫使其歸國,又要高度重視境外追逃工作,綜合運用引渡、遣返、勸返、異地追訴等手段,把追逃作為追回資產的重要支撐點、發力點。若能實現成功追逃,追贓就相對比較容易,能更好地掌握追贓的主動權,既可在追逃的同時要求資金流入國返還資產,也可要求腐敗分子配合將資產轉回國內,以實現追逃促追贓的效果。
第二,確立“優勢證據”的違法資產證明標準,充分激活“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在資產追回上的功能。“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是一種對物的相對獨立的特別程序,具有民事訴訟的確權性質,違法資產的證明標準不宜過高,確立為“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才更科學、合理和現實。這樣可大大降低應用該程序追繳外流腐敗資產的難度。當然,在充分運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追回腐敗資產的同時,也要大力踐行資產追回的其他方式。
第三,確立承認、執行外國刑事沒收裁決的制度,從而可根據互惠和對等原則,要求外國認可我國法院作出的刑事沒收裁決。確立承認和執行外國刑事沒收裁決的制度,這從長遠來看,是有利于我國追回外流腐敗資產的。事實上,2001年,我國與烏克蘭締結的《中烏移管被判刑人條約》就規定了相互承認和執行刑事裁決的內容,這完全可以為《刑事訴訟法》采納吸收。“予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我國一旦確立承認和執行外國刑事沒收裁決的制度,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該外國按照互惠和對等原則認可我國法院作出的刑事沒收裁決。
第四,建立務實合理的資產分享機制,最大限度地追回外流腐敗資產。相比于堅持全部追回但實踐困難的追贓模式,資產分享其實是一個更為務實、明智的選擇,而且為諸多國際公約所確認,亦在許多國家的實踐中得到廣泛采納。建議我國采取務實追贓的辦法,及時確立腐敗資產分享機制,推動反腐敗境外追贓合作不斷深化發展。當然,要科學設定資產分享的條件、方式、比例和范圍,以充分發揮該機制在資產追回上的正向功效。
第五,刑事裁決中靈活處理“沒收財產”事項,沒收外流腐敗資產適用《刑法》中“特別沒收”規定,以此紓解境外追贓配合難的困境。對于嚴重貪腐犯罪,根據《刑法》有關規定,在適用主刑的同時是要并處沒收財產的。域外絕大多數國家司法機關所承認的“沒收財產”,是在沒收“違法所得、收益和犯罪工具”范圍之內的,更多類似于《刑法》第64條規定的“犯罪所得之物、所有之物的處理(特別沒收)”,以及《刑事訴訟法》確立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中的“沒收財產”。無論是“特別沒收”還是“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中的沒收財產,都是與犯罪或者案件有關的涉案財產。鑒于此,對于腐敗分子死亡、逃匿境外的情況,追繳其腐敗資產,直接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作出刑事沒收裁決即可。對于腐敗分子被緝捕歸國的情況,可以在刑事裁決中靈活處理,將對外流腐敗資產的沒收與對腐敗分子經濟制裁的懲罰性沒收分列,對外流腐敗資產適用“特別沒收”規定并予注明,以與外國對“沒收財產”范圍的要求保持一致,這一項“沒收財產”可要求外國司法機關承認和執行。至于對腐敗分子的懲罰性沒收財產刑,我國可不提出司法協助請求,這樣有助于紓解境外追贓配合難的困境。
第六,以建設性的方式管控分歧,敦促資產流入國履行返還資產的條約義務,推進追贓務實合作。誠然,各國國情不同,開展反腐敗追贓合作的需求、重點和主張也不盡一致,難免會存在分歧。一方面,國際社會在堅持平等互利、求同存異的原則下,要尊重彼此在反腐敗追贓合作領域的核心利益,尤其是要努力克服法律制度方面的差異,找到雙方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我國應充分發揮“領頭羊”的作用,積極推進我國與資產流入國開展分享與返回被追繳資產的務實合作,敦促資產流入國切實履行公約、協定義務和承諾,進一步明確、細化雙方反腐敗追贓合作的措施和路徑,探索資產追回的靈活框架,盡力提高合作實效。

個人簡介》》
彭新林: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二十國集團(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