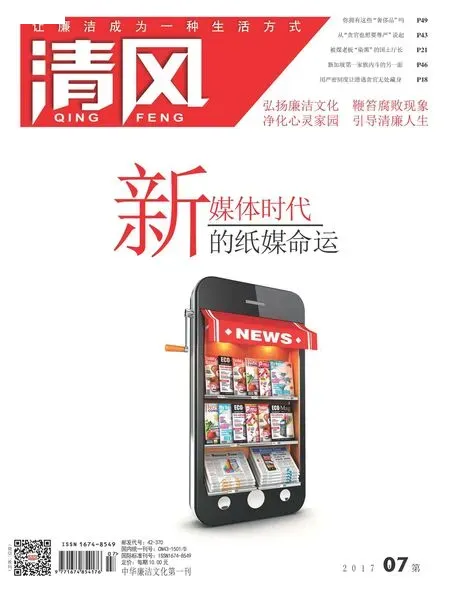從“貪官也想要尊嚴”說起
文_張桂輝(福建廈門)
從“貪官也想要尊嚴”說起
文_張桂輝(福建廈門)

王國強在《永遠在路上》中感嘆外逃生活
“很多歸案的外逃貪官,均表示逃亡的生活沒有尊嚴。”這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新近所發《揭秘外逃貪官亡命天涯的海外生活》一文中的一句話。筆者個人理解,其中的潛臺詞是:“貪官也想要尊嚴。”
尊嚴,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擁有應有的權利,并且這些權利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尊重。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有許多關于尊嚴的名言、格言。我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現代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那句——“對人來說,最最重要的東西是尊嚴。”貪官也是人。貪官需要尊嚴也好、需要尊嚴也罷,都是情有可原、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人生在世,怎樣才能活得有尊嚴,如何才能維護好尊嚴。很多貪官落馬前,尤其是手中有權、一呼百應,身邊有人、前呼后擁的時候,未必一清二楚,更未用心呵護。
負罪潛逃,何來尊嚴?可是,不少貪官卻明知故犯。遼寧省鳳城市原市委書記王國強,2012年4月24日潛逃到了美國。在美國兩年多時間里,夫妻倆“五不敢”:有護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醫,與國內親人不敢聯絡,與美國的同學和朋友不敢聯系,就連同在美國的女兒也不敢告知,更談不上見面了。在潛逃期間,王國強心臟病發作,只好在路邊的小椅子上半坐半躺,硬撐著、掙扎著。其妻則以淚洗面,因心情抑郁,脖子變大了,眼球變硬了,但不敢去看醫生。王國強感嘆:“兩年零八個月,說起來是那么的短,但對我來講就像過了28年一樣。”試問,如此這般,尊嚴何在?還有比王國強更慘的。湖南省長沙市國土局原局長左天柱逃往美國,幾百萬贓款揮霍一空后,基本不會外語的他,找不到比較體面的工作,只能靠給殯儀館背尸體勉強謀生。
有句成語叫“數典忘祖”。外逃的貪官,非但不要祖國了,有的連祖宗都不要了。《水滸傳》第二十七回:“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可嘆,有的貪官不但改名換姓,而且連爹媽的遺傳都不要,巴不得來個名副其實的改頭換面。如分別擔任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陳滿雄和陳秋園夫婦,1995年,其卷款外逃到泰國清邁后,買來泰國籍身份證,分別更名為蘇·他春和威帕·頌齋。陳滿雄還做了一次徹底的整容手術,連皮膚都進行了漂白。被捕前的一段日子,陳氏夫婦行動極為詭秘,連到市場購物也選在夜間。被捕后,平日春風得意的陳滿雄當場昏倒。
清朝大臣,理學家張伯行《禁止饋送檄》中寫道:“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張伯行官至禮部尚書,以清廉剛直留下美名。清朝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文學家曾國藩則說:“衣冠之族,以清白遺世為本,務要恬穆省事,凡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與之相接。”
二者表述各異,大意基本相同。都是倡導清廉,都在告誡官員。是呀,貪者一文不值,不宜相接,尊嚴何在?曾國藩言行一致,示人以廉。咸豐十一年(1861),他五十大壽,對曾國藩尊敬有加的湘軍霆字營統領鮑超,登門祝壽,禮物多為貴重物品。曾國藩只象征性收下一頂小帽,其余貴重禮物,全部“完璧歸趙”。是年十月初九,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余則全璧耳。”曾國藩的所作所為,既維系了袍澤之情,又守住了自身清廉。何其廉明、多么明智。
“有錢能使鬼推磨”。不錯,有些外國的身份證等,可以用金錢購買。可是,人生的尊嚴,靠金錢是買不來、保不住的。有道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奉勸為官者,為了履職平安、為了人格尊嚴,還是未雨綢繆,自覺做到謹慎用權、秉公辦事,始終保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態,這樣,才能贏得尊嚴、守住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