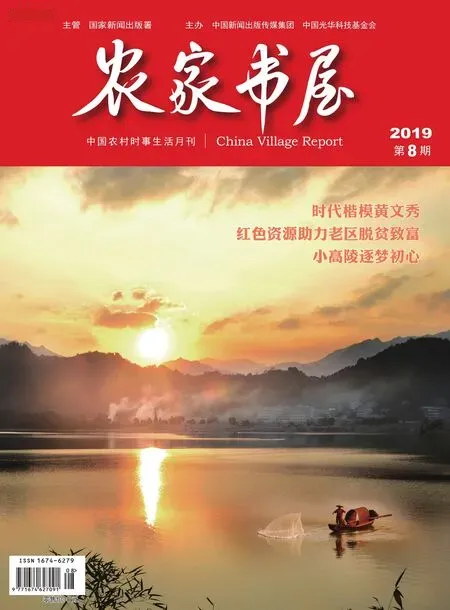中國鄉村復興之路
巧合
《滿川田紀事》作者汪冬蓮,有近二十年中央媒體工作經驗,他對于中國鄉村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其可能的解決路徑的記錄與探討,更多是基于多年媒體工作經歷訓練出來的本能與敏感性。因此雖然這本書并非是一本學術論著,但汪冬蓮在書中所提出的諸多命題,卻完全有可能給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學者,提供可能的議程命題和豐富的一手素材。
在加快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此書刻畫了一個中部普通村莊的一群小人物的命運,他們有堅守、有奮進、有寂滅、有突圍……彌散又聚合,飄蕩又歸根;不甘隨波逐流但又無力掌控,歷史性地翻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數億幾乎從不發聲的群體之中。本書作者跳脫出傳統的敘事視角,為小人物發聲,使得一個村莊的人物群像竟是數億農民的縮影。該書流露出的底層視角和人文關懷,啟發我們對城市化和現代化做更進一步的思考,還是“我們從何處來、身在何處、往何處去”。作者以安徽歙縣下屬的滿川田村為樣本,擷取代表性的三四十戶農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反映近四十年來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脈絡和生存現狀。通過書中的文字,能夠強烈感受到作者對農村的深厚感情,對農村未來發展、農業生產現狀的深切擔憂。這樣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即便像安徽黃山的農村,那么鐘靈毓秀的一方水土,也因化肥、農藥的過量使用而傷痕累累,徽文化的遺產同樣存在著大量消失的隱憂。
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提出了農村目前存在的大量問題的解決之道,拋磚引玉,我們期待著夢想照進現實的那一天。每一個根在農村或關注農村的人,都能直觀地感受到當下農村的巨變。
作者在書中記錄的八例成功從農村轉入都市生活的案例中,幾乎每一位當事人都經受過比較好的教育;而相對應的是,那些沒有經受較好教育,或者從中國教育體系當中被淘汰下來的農民,則直接面臨出門打工,還是在家做光棍的尷尬命運抉擇。教育對于農民都市化進程的顯著影響,在書中的幾十個案例當中不言自明。
又如,作者通過自己敏銳細致的觀察,發現當今農產品質量的日益下滑,跟農民對于農業生產的敷衍了事、投入日益減少有著直接關系,而這一現象的發生原因,又是源自農民在從事工業、服務業等非農產業上獲得的經濟回報,要遠遠高于農業。因此,不解決農產品收購價格低下和農業收入微薄的問題,就沒有辦法真正改善和提升農產品質量。這樣的觀察和分析是非常到位的。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20世紀后20年至21世紀前20年,是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向現代的工業化、城鎮化社會的裂變時期。毫不夸張地說,整個社會在這40年中發生的嬗變,超過以往5000年。”在這樣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里,中國鄉村發生了哪些變化,其未來的發展出路又在哪里,相信閱讀這本書,能讓讀者在上述問題的思考上,找到些許線索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