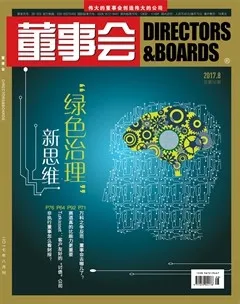國企不能為“表率”不顧程序、法規(guī)
高明華
十八屆四中全會(huì)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特別指出要加強(qiáng)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立法;《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指導(dǎo)意見》則指出,國有企業(yè)要成為自覺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表率,首次將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提升到改革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企業(yè)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重要性和現(xiàn)實(shí)緊迫性。
根據(jù)現(xiàn)代公司治理理論,企業(yè)有著眾多的利益相關(guān)者,包括投資者、高管、員工、債權(quán)人、供應(yīng)商、客戶、社區(qū)居民等,他們均為企業(yè)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因此,企業(yè)有責(zé)任維護(hù)利益相關(guān)者的利益,保證他們的利益不被損害。從投資者角度,企業(yè)賺了錢就應(yīng)該分紅,這是鼓勵(lì)投資者理性投資、減少資本市場非正常波動(dòng)的重要方面;從高管角度,高管薪酬應(yīng)與其業(yè)績相吻合,這是激發(fā)高管創(chuàng)新的動(dòng)力基礎(chǔ);從員工角度,企業(yè)應(yīng)保證員工收入隨著企業(yè)利潤的增長而增長,而且要關(guān)心員工的身心健康,這是員工持續(xù)貢獻(xiàn)其專用性資產(chǎn)的保證;從債權(quán)人角度,企業(yè)應(yīng)按期還本付息,從供應(yīng)商角度,企業(yè)應(yīng)保證資金的供應(yīng)充分,這兩者是企業(yè)誠信的重要體現(xiàn);從客戶角度,企業(yè)應(yīng)保證產(chǎn)品的質(zhì)量和安全,這是企業(yè)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本條件;從社會(huì)公眾角度,企業(yè)要盡其所能為社會(huì)做出貢獻(xiàn),如依法交稅、捐贈(zèng)慈善事業(yè)、保護(hù)環(huán)境等。
從廣義角度,上述企業(yè)對利益相關(guān)者的回報(bào),都可以視為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但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義務(wù)性質(zhì)的社會(huì)責(zé)任,如嚴(yán)禁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提供高質(zhì)量的、安全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等;二是非義務(wù)性質(zhì)的社會(huì)責(zé)任,如賑災(zāi)捐款捐物、資助教育事業(yè)等。前者是強(qiáng)制性的;后者是自愿性的(也可以稱之為狹義的社會(huì)責(zé)任)。
對于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不存在區(qū)別,因?yàn)檫@是法律義務(wù),不因企業(yè)性質(zhì)而不同;對于非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對競商業(yè)類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政府不能強(qiáng)行附加給企業(yè),應(yīng)由企業(yè)自主決定,如有必要強(qiáng)制安排,政府必須給予足額補(bǔ)償,當(dāng)然這種補(bǔ)償不一定是現(xiàn)金,也可以是其他方式,如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等。
企業(yè)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是一種成本支出,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社會(huì)責(zé)任與企業(yè)發(fā)展存在沖突?并不盡然。從長期看,企業(yè)發(fā)展與社會(huì)責(zé)任是一致的,但短期看,則可能出現(xiàn)不一致。如果企業(yè)發(fā)展是建立在損害社會(huì)公眾和員工利益基礎(chǔ)上,如環(huán)境污染、員工工作環(huán)境無安全保障設(shè)施等,盡管企業(yè)利潤提升了,但這種提升難以維持長久,從長期看,并不利于企業(yè)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因此,企業(yè)應(yīng)立足于企業(yè)的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實(shí)現(xiàn)企業(yè)發(fā)展與社會(huì)責(zé)任的統(tǒng)一。
對于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要加強(qiáng)立法,還要曝光,建立黑名單,違反者要處罰,而且處罰力度要足夠大,即法律要具有威懾力,包括民事處罰、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三種處罰要并行。同時(shí),要賦予公眾更多的監(jiān)督權(quán),要通過完整和及時(shí)的信息披露,加強(qiáng)和鼓勵(lì)公眾監(jiān)督,比如企業(yè)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是否是高質(zhì)量的和安全的,應(yīng)有顧客滿意度的數(shù)據(jù)。而且,政府要把公眾監(jiān)督的結(jié)果及時(shí)反映到懲罰成本上。通過法律和公眾監(jiān)督,使企業(yè)背離強(qiáng)制性社會(huì)責(zé)任義務(wù)的收益遠(yuǎn)小于成本,從而促使其依法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
對于非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要鼓勵(lì),要宣傳,但不適宜立法給予強(qiáng)制,因?yàn)樗鼘儆诘赖路懂牎F鋵?shí),對于非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企業(yè)通常都會(huì)自我宣傳。比如,企業(yè)進(jìn)行了慈善捐款,通過宣傳會(huì)產(chǎn)生廣告效應(yīng),能夠向大眾傳遞企業(yè)擁有較強(qiáng)競爭力的信息,從而會(huì)得到更多的供應(yīng)商和客戶的信賴。無疑,承擔(dān)非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盡管付出了成本,但通過廣告效應(yīng),是能夠帶來更多利潤的。對這種非義務(wù)性社會(huì)責(zé)任,政府也可以在宣傳上發(fā)揮助推作用,要樹立典型,使企業(yè)不僅自愿承擔(dān)非義務(wù)性社會(huì)責(zé)任,而且愿意承擔(dān)更多的非義務(wù)性社會(huì)責(zé)任。
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非義務(wù)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企業(yè)在做出決策時(shí),也必須依法依規(guī),不能想當(dāng)然地由某個(gè)人或某個(gè)出資人單方面決定。通常,對于公司制企業(yè),非義務(wù)性社會(huì)責(zé)任達(dá)到一定額度,必須經(jīng)由董事會(huì)討論決定;再達(dá)到更高額度則必須由股東大會(huì)決定(適合于設(shè)立股東大會(huì)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責(zé)任公司)。具體額度限制的規(guī)定由公司章程來規(guī)定,而公司章程必須由股東大會(huì)來決定。
針對國有企業(yè),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都是義務(wù)性的,既然是義務(wù),就必須依法履行;對于商業(yè)類國有企業(yè),不能以“國有企業(yè)要成為自覺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表率”為名,讓國有企業(yè)承擔(dān)超過其自愿承擔(dān)的更多的非義務(wù)性社會(huì)責(zé)任,承擔(dān)與否,承擔(dān)多少,都必須經(jīng)由董事會(huì)或股東大會(huì)來決策,不能為了“表率”而不顧程序和法律規(guī)則。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xué)公司治理與企業(yè)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