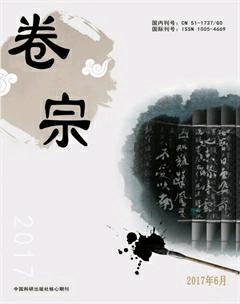博物館文化資源的活化
孫菁
精神經(jīng)濟(jì)時(shí)代下,在大眾的生活中,非物質(zhì)消費(fèi)開始漸漸變成主導(dǎo)消費(fèi),物質(zhì)產(chǎn)品儼然變成了精神消費(fèi)的載體。大眾的文化消費(fèi)不停的膨脹,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愈來愈強(qiáng)。博物館作為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家族中的重要一員,也開始逐步釋放它獨(dú)有的光。現(xiàn)如今,博物館的基本職能已經(jīng)轉(zhuǎn)變,從之前的展示和保存藏品逐漸延伸至教育和娛樂領(lǐng)域。承擔(dān)更多的社會(huì)責(zé)任,博物館就不得不面臨經(jīng)營成本上升、經(jīng)費(fèi)捉襟見肘等一系列問題。除去政府撥款以外,博物館勢必要尋求其他路徑實(shí)現(xiàn)收入,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開發(fā)就是其中一種思路。諸多博物館的實(shí)踐向我們證明,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不僅能夠帶來可觀的經(jīng)濟(jì)效益,還能使博物館內(nèi)的文化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實(shí)現(xiàn)資源“活化”。
1 從“紀(jì)念品”到“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早在很久以前,我國的博物館內(nèi)就有“紀(jì)念品”出售,但當(dāng)時(shí)由于產(chǎn)品種類單一、設(shè)計(jì)缺乏新意,基本上是游客們“過而不入”的參觀盲區(qū)。在歐美國家,許多名館打開腦洞,開始利用館內(nèi)的珍貴文化資源開發(fā)產(chǎn)品進(jìn)行售賣。他們與優(yōu)秀設(shè)計(jì)師聯(lián)手,提取館內(nèi)文化資源的藝術(shù)元素并將其注入產(chǎn)品之中,注重新潮設(shè)計(jì)與文化本性品格的融合,同時(shí)提供舒適體貼的購物體驗(yàn),吸引了大量游客。因此博物館商店也被冠上 “最后一個(gè)展廳”的美譽(yù)。現(xiàn)如今,不論是美國大都會(huì)、法國盧浮宮、西班牙普拉多這樣的著名博物館,還是像德國貝多芬紀(jì)念館、瑞典東方博物館等小型博物館,其開發(fā)銷售的文化產(chǎn)品都琳瑯滿目。
2015年3月,我國出臺(tái)的《博物館條例》中首次明確支持博物館與文化創(chuàng)意、旅游等產(chǎn)業(yè)相結(jié)合,開發(fā)衍生產(chǎn)品,增強(qiáng)博物館的發(fā)展能力[1]。這一條例促使國內(nèi)博物館開始轉(zhuǎn)變運(yùn)營理念。博物館之間不再糾結(jié)于比拼文物的“硬實(shí)力”,而是將競爭的天平向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的“軟實(shí)力”傾斜。
博物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不同于之前的“紀(jì)念品”,與后者相比,前者具有了更多的內(nèi)涵。它不僅僅是明信片、擺件,而是以博物館獨(dú)特的文化資源作為設(shè)計(jì)基礎(chǔ),并被設(shè)計(jì)者注入更多文化內(nèi)涵的一類商品。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最有代表性的有兩類,一類是實(shí)體產(chǎn)品,除了日常用品的開發(fā)和典藏復(fù)制品,博物館有針對(duì)性開發(fā)的一些咖啡館、茶吧等文化空間也應(yīng)算入其中;另一類是利用新媒體、數(shù)字化技術(shù)產(chǎn)生的,帶有互動(dòng)體驗(yàn)色彩的產(chǎn)品,例如博物館拍攝的紀(jì)錄片及APP應(yīng)用等。承載著“活化博物館文化資源”使命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要想從“最后一個(gè)展廳”真正走向大眾的日常生活,需要滿足三個(gè)基本條件:一是不可缺少的情感和溫度,找到連接大眾的紐帶,能夠吸引參觀者的注意力;二是方便批量生產(chǎn),滿足大量觀眾的需求;三是產(chǎn)品設(shè)計(jì)應(yīng)以博物館中的文化資源為基礎(chǔ),將博物館中的文化資源轉(zhuǎn)化為具有商業(yè)價(jià)值的設(shè)計(jì)。這就需要設(shè)計(jì)者們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設(shè)計(jì)前,先將博物館內(nèi)可供利用的文化資源整理清楚。
2 博物館可供利用的文化資源
“一個(gè)博物館的建立,通常是以一個(gè)地區(qū)的地域文化為背景,依靠遺址或有意義的歷史建筑而設(shè)立,并在此基礎(chǔ)上保護(hù)、收藏和展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藏品。” [2]因此,對(duì)博物館的文化資源做梳理,我們可以從藏品、遺址建筑和地域文化這三方面著手。
2.1 藏品文化資源
博物館中的藏品,對(duì)博物館來說是資產(chǎn),也是其賴以存在的基礎(chǔ)和意義。盡管我國法律規(guī)定博物館的館藏文物是不能當(dāng)作商品任意去市場上進(jìn)行買賣交易的,但博物館館藏文物中含有的文化價(jià)值可以經(jīng)過合理的產(chǎn)業(yè)運(yùn)作,使其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效益,它完全可以作為博物館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資源。
以位于紐約第五大道的大都會(huì)博物館為例,它共收藏有300萬件藝術(shù)收藏品,包括許多出眾的古典藝術(shù)品、古埃及藝術(shù)品、幾乎所有歐洲大師的油畫及大量美國視覺藝術(shù)和現(xiàn)代藝術(shù)作品[3]。在保證文物安全無損壞的前提下,大都會(huì)博物館利用館內(nèi)藏品資源開發(fā)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數(shù)量多達(dá)2萬多種,年銷售額高達(dá)4至5億美金,占整個(gè)博物館全部收入的80%,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經(jīng)濟(jì)效益[4]。在對(duì)館內(nèi)藏品文化資源的利用上,大都會(huì)博物館匠心獨(dú)運(yùn),心思極巧,例如依照館內(nèi)珍藏的名畫中人物所戴的項(xiàng)鏈樣式,就能開發(fā)出一個(gè)女性飾品系列,吸引了無數(shù)到此參觀的女性的眼球。
2.2 建筑及遺址文化資源
依靠遺址建立或直接在有歷史意義的建筑內(nèi)設(shè)立的博物館比較常見。在我國很多遺址保護(hù)園區(qū)中,常常設(shè)有展示出土文物的博物館,如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北京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陜西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等。而在有歷史意義的建筑內(nèi)直接設(shè)立博物館,需要建筑本身足夠突出且有足夠的容納空間,一般如宮殿、寺廟等。北京故宮博物院即是如此,除了內(nèi)部的館藏珍品足夠引人奪目,故宮博物院更重要的意義是它承載了中國傳統(tǒng)的建筑文化和宮廷文化這些文化瑰寶。人們前來游覽,不僅是被展出的各類珍貴文物所吸引,更具吸引力的是它打著歷史烙印的建筑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義,還有引起人們遐想的皇室生活。遺址和建筑不僅作為文物保護(hù)、展示和宣傳的空間,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象征,它可因其文化特殊性成為當(dāng)?shù)氐男蜗竺浒奈幕瘍r(jià)值注定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可移動(dòng)的文化資源。
2.3 地域文化資源
在博物館藏品的收集過程中,尤其是對(duì)于一些中小型的博物館來說,在此地區(qū)的地域文化形成發(fā)展中有一定價(jià)值的文化遺存,都可以作為地域文化的代表,被收入到博物館中。地域文化集中體現(xiàn)了一個(gè)地域的文化特征,也是這個(gè)地區(qū)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根本所在,它也是一種天然的文化資源。但是,地域文化作為博物館發(fā)展的一個(gè)大的文化環(huán)境,本身是一個(gè)較為虛化的概念,我們并不能直接看到和接觸到。這個(gè)虛化的概念里包含的文化精華與養(yǎng)分,需要通過遺址建筑和館藏文物作為載體傳達(dá)給參觀者。很多地區(qū)的博物館開發(fā)出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毫無生命力且不受大眾待見,很大原因在于設(shè)計(jì)者只盲目套用一些俗爛的文化符號(hào)或者照搬其他地區(qū)的產(chǎn)品,忽視了自身博物館內(nèi)充滿地域個(gè)性的文化資源。
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正式進(jìn)入設(shè)計(jì)階段前,設(shè)計(jì)者要做的第一個(gè)工作就是進(jìn)行廣泛的資料搜集工作,并對(duì)搜集到的文化資源進(jìn)行整理和分析,拓寬搜集渠道,要避免在某一方面過度搜集以限制住思維的發(fā)散性,這樣才能更好地挖掘博物館的文化內(nèi)涵,凸顯其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特性和優(yōu)勢。但我們也必須明白一點(diǎn),那就是許多文化資源并不適合開發(fā)成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所以,要注意對(duì)可利用的文化資源進(jìn)行選擇。
3 文化資源轉(zhuǎn)化為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上文中我們說到,在進(jìn)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開發(fā)設(shè)計(jì)之前,設(shè)計(jì)者們需要對(duì)博物館的文化資源進(jìn)行廣泛搜集。尤其要注意對(duì)大眾非常喜愛且容易接受的文化資源,以及最能代表博物館文化特殊性、個(gè)性鮮明的文化資源的搜索。在資料廣泛搜集的基礎(chǔ)上,設(shè)計(jì)者們要注意從眾多文化資源當(dāng)中,挖掘出可利用的資源。
對(duì)于地域文化資源來說,其蘊(yùn)含的本地區(qū)獨(dú)有的文化要素要格外重視。博物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是文化要素和產(chǎn)品的結(jié)合,產(chǎn)品滿足的是人們物質(zhì)層面的需求,而文化要素滿足人們精神層面的需求。每一件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蘊(yùn)含的文化要素,都應(yīng)該有著地域文化的獨(dú)特胎記,而不應(yīng)該是雷同的、毫無差異性的。對(duì)于藏品文化資源,藏品可利用的形式要素有很重要的作用。形式要素主要是指產(chǎn)品的色彩、材質(zhì)、造型、工藝、紋飾圖案等[5],它代表著參觀者對(duì)于產(chǎn)品最直觀的印象。不同類型的藏品,可提取的形式要素都有不同,例如玉器石器類的藏品,可提取其造型和材質(zhì)要素;織繡類藏品,可提取其色彩、紋飾要素;名人遺物類藏品,可從其意蘊(yùn)要素入手;書法繪畫類藏品,其造型與意蘊(yùn)都可成為提取的要素。臺(tái)北故宮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毛公鼎燭臺(tái)”,就是提取其代表性藏品“毛公鼎”的造型元素,以玻璃制作,讓原作稍顯笨重的青銅器變得淡雅靈巧。對(duì)于歷史建筑、遺址類的文化資源,博物館建筑的造型元素是常常能夠用到的。很多博物館抽取其有特色和辨識(shí)度的建筑造型元素(有時(shí)整體有時(shí)局部),直接把它復(fù)制到帆布包、行李牌、冰箱貼等日常生活用品上,使這些用品能兼具實(shí)用性、審美性和文化內(nèi)涵,從而能夠更容易走進(jìn)大眾的生活。
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產(chǎn)品的轉(zhuǎn)化過程,始終貫穿著設(shè)計(jì)者對(duì)可利用資源的搜集工作,設(shè)計(jì)者需要時(shí)時(shí)對(duì)資料進(jìn)行補(bǔ)充和更新。從已經(jīng)搜集到的資料中,設(shè)計(jì)者需要尋找到能傳達(dá)博物館文化意蘊(yùn)的“主題”關(guān)鍵詞,并對(duì)關(guān)鍵詞進(jìn)行全面的分析,包括故事情感、文化內(nèi)涵,到外在的類別、形狀、顏色、整體或局部造型,通過分析進(jìn)一步確定出“創(chuàng)作主題”,并根據(jù)這一主題對(duì)創(chuàng)作元素進(jìn)行提煉和篩選,設(shè)計(jì)出相應(yīng)的文化元素符號(hào)。
接下來,文化元素將以各種合理的方式被轉(zhuǎn)化為文化產(chǎn)品。設(shè)汁者首先需要對(duì)文化元素符號(hào)進(jìn)行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加工,對(duì)文化元素和產(chǎn)品之間的演繹方式,以及風(fēng)格、材質(zhì)、功能等方面進(jìn)行設(shè)定。人們在看到一個(gè)新事物的時(shí)候,往往會(huì)根據(jù)其直觀表象進(jìn)行視覺上的取舍,而設(shè)計(jì)者可根據(jù)參觀者的表象思維,將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加工后的文化元素直接復(fù)制到產(chǎn)品上;還可將文化元素以圖騰化的形式與產(chǎn)品結(jié)合,賦予產(chǎn)品一定的文化內(nèi)涵和寓意,以一種具象的形式語言來表達(dá)博物館抽象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頂戴花翎官帽傘”,利用“花翎”這個(gè)帶有官場文化色彩的圖騰,將其與“傘”結(jié)合,整把傘撐開后宛如戴了一頂官帽,十分有趣。在對(duì)文化元素和產(chǎn)品之間的演繹方式設(shè)定完成之后,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將其呈現(xiàn)出來,設(shè)計(jì)者可以通過二維或三維的方式形成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草案。之后,設(shè)計(jì)者還需要不斷進(jìn)行產(chǎn)品的評(píng)估以及傾聽意見的反饋,在設(shè)計(jì)的各個(gè)細(xì)節(jié),包括顏色、造型、材質(zhì)、模型的制作等方面進(jìn)行精確處理,使其具備足夠的商業(yè)吸引力,最終形成獨(dú)一無二的博物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參考文獻(xiàn)
[1]王玨,姜瀟,孫麗萍,白林.《博物館條例》開始實(shí)施:讓博物館有看頭有魅力[OL].2015-03-23.http://www.jyb.cn/china/gnxw/201503/t20150323_616671.html.
[2]吳思思.博物館商品的開發(fā)—博物館文化資源的挖掘[D].廣東工業(yè)大學(xué),2012.
[3]360百科.大都會(huì)藝術(shù)博物館[OL].http://baike.so.com/doc/5797213-6010008.html
[4]林炎旦.《文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國際經(jīng)典論述》[M].臺(tái)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10.
[5]張堯.基于博物館文化資源的創(chuàng)意產(chǎn)品開發(fā)設(shè)計(jì)研究[D].蘇州大學(xué),2015.注:此文為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計(jì)劃項(xiàng)目“基于博物館文化資源的創(chuàng)意產(chǎn)品開發(fā)研究”(KYLX16_134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