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何映宇
這兩個職業有著共同點,他們都是直接面對人的,面對人的病痛。醫生,面對的是肉體的病痛;作家,則面對人性的病痛。
“機器的未來已來,人類的盡頭還未盡,不應該只把自己當作應用的器物,不應該局限于器物中某些應用。讓我們在君子不器的理念下,在未來已來的今天,活得越來越有人樣。”
這是馮唐在中信出版集團“文學驅動社會”沙龍暨“中信文學元動力作家”頒獎盛典上發言的結束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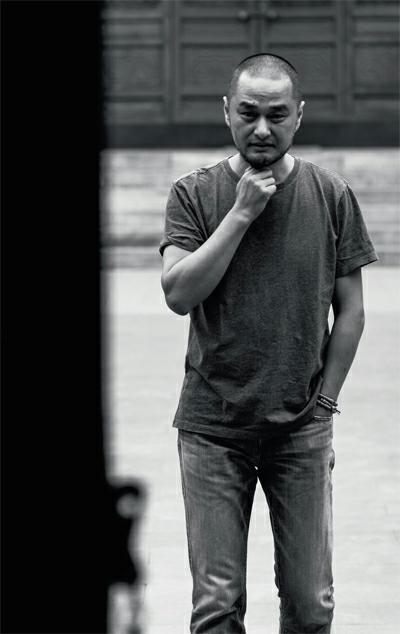
忽如一夜春風來,人工智能成為了最熱門的話題,這邊廂楊瀾跨界出了本新書《人工智能真的來了》,那邊廂馮唐的全新小說集《搜神記》,也在尋找人類與阿法狗抗衡的勇氣與力量。
談到為什么要寫這本書時,馮唐說:“這個世界的慈悲和智慧,掌握在少數被稱為神的人手中,他們善于技也精于藝,亦正亦邪。我要搜到這些人,和他們來一場精神、技藝的斗法,考驗他們的性情與技藝。那些觸動并贏得我的人,我要給他們寫一部小說,書名就叫《搜神記》。”
馮唐的名字出自《滕王閣序》,說的是這樣一個典故:漢代的馮唐思維敏捷、孝順父母且忠于職守,雖歷經漢文帝、漢景帝和漢武帝三朝,卻一直只擔任一個初級侍衛郎官。盡管漢文帝都曾經問計于馮唐,但是也改變不了馮唐的仕途背運。至武帝時,有人舉薦了他,可是他己九十多歲,不能再做官了。
當代小說家馮唐顯然不是漢代的馮唐。他1990年-1998年就讀于協和醫科大學,獲臨床醫學博士,婦科腫瘤專業,美國工商管理碩士。2011年10月,又當選為華潤醫療集團有限公司CEO。在小說方面,因“萬物生長三部曲”而被讀者熟知,他的小說受到一批文學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喜愛,也有不少人評價馮唐為當代文壇中的異類,在他的作品中經常是以一種充滿著物質性的口語方式在敘述,以一種綿密饒舌的喋喋不休給予寫作以豐富的構成。除了寫青年的成長,馮唐小說還有一個潛在的主人公:北京。他的文字中,有關北京的路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充滿著大大的拆字、汽水、防空洞、自行車的老北京;一個是被高樓大廈占據,面目全非的大都會。2011年12月12日,《人民文學》“未來20大家”TOP20評選,馮唐榮登榜首。
從醫、從商、從文,馮唐都堪稱人生贏家,他的創作歷程,還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作家,面對人性的病痛
《新民周刊》:原名張海鵬,怎么會用“馮唐”來做筆名的,有什么寓意?
馮唐:“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人生總是短暫的。所謂人生,就是從出生開始就走向死亡的一個過程。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一點,而在短暫的人生里,我又想做許多事情,比較貪心。所以取了這個筆名。
《新民周刊》:學的是醫科,我們知道魯迅、余華都是學醫出身的,你覺得學醫對你的文學創作有怎樣的影響?最初學醫是什么樣的契機?
馮唐:醫生好像很容易轉型為作家,契訶夫和毛姆也是醫生,寫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也是。我覺得這兩個職業有著共同點,他們都是直接面對人的,面對人的病痛。醫生,面對的是肉體的病痛;作家,則面對人性的病痛。另一方面,面對病痛,醫生和作家,其實都是無力的,沒有根治的良方,沒有十全大補丸。學醫的經歷,讓我了解了人的病痛以及人的無力。這也是我的寫作的主題。
至于我最初學醫,其實很簡單,高考完填志愿的時候,我老媽想要家里有個醫生,看病方便,于是給我填了“協和”。
《新民周刊》:從華潤集團戰略管理部總經理到中信資本,要負責公司的日常運作,應該是很忙的,怎么安排時間來寫作?
馮唐:我寫作都是零碎時間,在機場候機,在飛機上,在會議間隙,有空的時候,我有想法就寫一點。唯一的整塊時間,就是每年的年假,找個酒店,不出門,悶頭寫。《搜神記》就是用這些零碎時間和春節的年假寫出來的。
《新民周刊》:《歡喜》是你寫的第一本小說嗎?當時怎么會創作這本書的?
馮唐:寫《歡喜》的時候,我十六歲到十八歲,在十來歲的年齡寫十來歲的生活,于是就寫了《歡喜》。那時候,一是有時間,二是有感覺,觸覺敏銳,天是藍的云是白的女孩的頭發是香的,把它們統統寫下來,就是《歡喜》了。
不是自傳,也不是空穴來風
《新民周刊》:你說你的小說“不是自傳”,那么在你的小說中是不是有你朋友的影子?比如說《萬物生長》。
馮唐:小說是創作,但不是空穴來風;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塑造的,甲的鼻子,乙的嘴,丙的頭發,丁的胸,甲乙丙丁,是我認識的,有的是我的朋友、同學,有的是吸引我注意的路人。
《新民周刊》:自己身處商界,肯定知道很多內幕故事,以后有沒有可能寫一部和商界有關的小說?
馮唐:商界其實沒有那么多內幕,更多的還是數字,報表、估值之類。靠譜的商人,不相信內幕交易的。至于寫不寫商界小說,目前沒有這個打算,它不是我想寫的題目。
《新民周刊》:之前翻譯的泰戈爾《飛鳥集》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你對你翻譯詩歌的批評是否有話要說?自己是不是也特別喜歡讀詩和寫詩?
馮唐:《飛鳥集》的事情,已經過去一年了,該說的不該說的都說過了,還是那句話,交給時間去評判吧。
我是一個詩人,一直在寫詩,明年可能會出一本新詩集吧。
《新民周刊》:《春風十里不如你》正在熱播,這部電視劇改編自你的小說《北京,北京》,“北京”是你小說的一個關鍵詞,北京也是你的故鄉,北京是你的寫作之源。你一開始的寫作是否都是因為懷鄉?而香港這座城市是否就不能刺激你的寫作?
馮唐:不是“懷鄉”。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就在北京,自然以北京為主題。其實我不能理解的是,很多作家住在北京幾十年,一下筆就寫村里的小芳。
我在香港住過幾年,現在香港也是我的工作地。《搜神記》的第一篇,《二十來歲的你》,就是關于香港的小說,發生在香港的愛與欲。
《新民周刊》:有沒有參與編劇?對周冬雨、張一山的表演滿意嗎?
馮唐:沒有參與編劇。隔行如隔山。尊重專業,寫小說我是專業,編劇我不是,我沒有過問過。
我覺得周冬雨、張一山的表演非常棒,對他們的表現非常滿意。
人工智能,是不遠的未來
《新民周刊》:最新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搜神記》,《搜神記》來源于去年你的一檔脫口秀節目,怎么會做起脫口秀來了?
馮唐:我喜歡嘗試新鮮的東西,恰好騰訊發出邀請,又有點時間,一拍即合,于是我就去做了。做這檔節目,很好玩,也很辛苦,有收獲,這收獲,就是《搜神記》這本小說集。
《新民周刊》:又是怎么從《脫口秀》發展出7篇小說的?
馮唐:在做節目的最初,就有寫小說的想法。這檔節目,密集的制作,也讓我密集地提煉和思考單個人的特點,給了我寫作的IDEA。有了這個IDEA,有了可供我挖掘和延展的支點,接下來就是寫的過程了。
《新民周刊》:人工智能是今年特別熱的話題,你是怎么看人工智能的?
馮唐:人工智能,是不遠的未來,不管人類愿不愿意。可能不愿意的會占多數,因為很多人的工作要被取代。但這只是人工智能的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也會實現對人的解放。更多的人可以脫離工作的螺絲釘身份,去挖掘自己的潛能、智力和興奮點、愛好,去做更有創造力的事。
《新民周刊》:你曾經說:“我離佛千萬里,我離佛特別近。”什么時候開始接觸佛經的?像在《不二》中用到佛教的人物背景,是怎么考慮的?這樣寫的話有沒有引起爭議?
馮唐:中學的時候就開始接觸佛經了,我對佛教,尤其是禪宗,一直很有興趣。禪宗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印度佛教里是沒有的。禪宗講“呵佛罵祖”,馬祖道一、云門文偃、趙州從諗,他們對佛、對祖師的不敬更厲害。我的《不二》并沒有碰到什么問題。
《新民周刊》:現在的生活狀態是怎么樣的?在北京后海的四合院里是不是特別能讓你靜下心來寫作和思考?
馮唐:我現在不住在后海了。現在住在我從小長大的地方附近,只是那個地點、地名還在,樹、屋、人,都不一樣了。北京變化太快,我的變化太慢。
我的寫作,絕大多數時間不是坐在家里、書房里,而是在機場,在飛機上,在酒店。寫作的環境,對我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什么怎么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