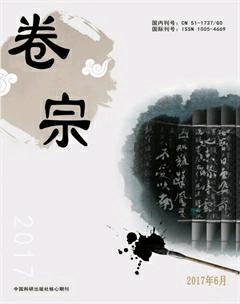淺談南宋時(shí)期建安余氏的刻書事業(yè)
摘 要:南宋時(shí)期的私家坊刻以福建建安余氏最為著名,而其中又以余仁仲萬卷堂最有代表性。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的書籍為宋本刻書中的佼佼者,一直為海內(nèi)外所珍藏。其中“九經(jīng)”在宋代即以善本聞名。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可知,對(duì)南宋建安余氏的刻書業(yè)研究有所涉獵的,有肖東發(fā)教授的《建陽余氏刻書考略》、林申清的《宋元兩代建陽余氏刻書述略》以及山人的《圖書出版世家——建陽余氏》。現(xiàn)在關(guān)于南宋福建地區(qū)的刻書業(yè)的研究多集中于麻沙本或者是建安余氏的刻書研究。
關(guān)鍵詞:南宋;建安余氏;刻書
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說道:“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余氏為最。”而在余氏刻書中,又以余仁仲萬卷堂的刻書最為出眾。余仁仲所主持刻印的大部分書籍在南宋時(shí)就已被稱為精品了。比較著名的有《尚書精義》、《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等。岳飛的孫子岳坷在刊刻“九經(jīng)”時(shí),參閱多種版本校對(duì),認(rèn)為“以興國(guó)于氏、建陽余氏本為最善”,這在當(dāng)時(shí)便已有“名牌產(chǎn)品”的聲譽(yù)了。
余仁仲在建陽開余氏刻書的先河,使建安余氏在以后到明朝中葉一直保持著長(zhǎng)盛不衰的刻書事業(yè)。這從清朝乾隆曾派人專門調(diào)查余氏刻書事跡,便可佐證。乾隆四十年(1775)給軍機(jī)處下的奏折如下“近日閱米芾墨跡,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因考之宋岳珂相臺(tái)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shí)即有‘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是其借業(yè)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刻書始自何年?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1]乾隆帝所閱的大多數(shù)宋版書中,大部分均有余氏所刻的堂名;但是到清朝的時(shí)候,建安余氏的刻書業(yè)已經(jīng)徹底衰落了,沒有任何影響了。所以乾隆對(duì)此才會(huì)感到陌生,并派專人去調(diào)查。把建安余氏刻書的發(fā)跡時(shí)間確定在南宋的余仁仲時(shí)期。后來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對(duì)此事加以描述,使得影響擴(kuò)大。此后學(xué)者在研究建安余氏的刻書業(yè)時(shí),大多數(shù)對(duì)此次調(diào)查都加以援引。
余仁仲所主持刻印的書之所以為世人所稱贊,這與他的身世經(jīng)歷是有很大的關(guān)聯(lián)的。據(jù)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宋建安余氏刻書》中寫到“余仁仲,建安人,在孝宗、光宗世,曾為國(guó)學(xué)進(jìn)士。[2]可見他是一個(gè)有一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文人。他以名士身份創(chuàng)辦萬卷堂刻書,主持刻書業(yè)務(wù),不求仕宦。將畢生所學(xué)和精力投身于刻書事業(yè)的行動(dòng)引起了人們對(duì)刻書業(yè)的重視,對(duì)當(dāng)時(shí)刻書業(yè)的發(fā)展起了直接的推動(dòng)作用,對(duì)建陽書業(yè)特別是余氏后代的刻書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以至世代相傳,使余氏成為建陽最著名的刻書世家。
建安余氏的刻書業(yè)能延綿數(shù)百年之久,除了余氏族人自身的努力之外,也與福建當(dāng)?shù)氐淖匀晃幕瘲l件有莫大的關(guān)系。在北宋時(shí),福建的經(jīng)濟(jì)就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到了南宋時(shí)期,因?yàn)樗问夷隙桑S之帶來了大批的能工巧匠以及有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大量人口,這無疑為已經(jīng)有很大發(fā)展的福建經(jīng)濟(jì)再注入一劑強(qiáng)心劑。所以到了宋孝宗時(shí)期,福建的經(jīng)濟(jì)已擠入全國(guó)發(fā)達(dá)行列。宋代福建山區(qū)的開發(fā)己經(jīng)向縱深的方向發(fā)展,沿海地區(qū)也進(jìn)行圍墾事業(yè),以擴(kuò)大耕地面積,農(nóng)作物的種植不只是僅限于糧食作物,經(jīng)濟(jì)作物也開始有人種植。這從一個(gè)側(cè)面說明了福建地區(qū)自然經(jīng)濟(jì)的發(fā)達(dá)。當(dāng)然在商業(yè)上,福建也是南宋時(shí)期最發(fā)的的地區(qū)之一。泉州在南宋時(shí)期已經(jīng)取代廣州成為中國(guó)對(duì)外的最大出海貿(mào)易港口。每天經(jīng)由福建泉州進(jìn)出口的貨物都非常之多,商業(yè)的發(fā)達(dá)同時(shí)也加快了當(dāng)?shù)氐奈锪髁魍ǎ@使得福建所刻印的書可以通過商賈遠(yuǎn)銷國(guó)內(nèi)外。
此外,福建地處亞熱帶地區(qū),氣候常年溫暖濕潤(rùn),有廣闊的山地和丘陵地區(qū),而這氣候和地形都非常適合竹子的生長(zhǎng)。所以最好的造紙的原料如毛竹,褚皮,藤等都十分的豐富,特別是竹類,更是種類奇多。福建的竹類資源具有種類多,分布廣等特點(diǎn)。可用于造紙的竹子也多達(dá)六種:有麻竹,苦竹,綿竹,粉竹,赤箭竹和笙竹等竹類。竹子資源廣布于山區(qū)各縣及各縣山區(qū)里,是當(dāng)?shù)孛癖娰囈陨娴囊环N主要資源。所以造紙業(yè)在福建也是相當(dāng)?shù)陌l(fā)達(dá),而且用竹子造的紙具有質(zhì)優(yōu)價(jià)美的特點(diǎn)。
所以福建地區(qū)印出的書籍必定會(huì)比其他地區(qū)更有價(jià)格上的優(yōu)勢(shì)。據(jù)《福建史稿》寫道:“麻沙本十,比浙本七還便宜,浙本七比江南五本還便宜”。[3]也就是說用同樣的價(jià)錢,在江南可以買一本書的話,在福建可以買兩本書了。這也就是為什么福建的坊刻業(yè)為何如此興盛發(fā)達(dá),麻沙本為何可以盛銷于世。
福建的坊刻業(yè)自南宋余氏開始刻書,一直到明朝都占據(jù)全國(guó)坊刻之首的寶座。這除了自然條件的優(yōu)越,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雄厚,政策的寬松外,文化事業(yè)的推進(jìn)發(fā)展也是福建刻書業(yè)發(fā)達(dá)的重要原因。前面說了靖康之變發(fā)生后,宋室南渡,把北方的先進(jìn)生產(chǎn)技術(shù)以及一大批士族大夫都帶到了南方。因?yàn)楦=ㄌ?hào)稱“東南山國(guó)”,四處都是丘陵,利于避難。所以福建就成了士大夫脫險(xiǎn)避難的好去處。隨著福建建州地區(qū)聚集了大批的士大夫,當(dāng)?shù)氐奈幕聵I(yè)也開始發(fā)展起來。閩學(xué)在南宋時(shí)期成為與洛學(xué)相抗衡的另一大學(xué)派。總多的學(xué)者在福建聚眾講學(xué),著書立說,闡發(fā)己論。正是因?yàn)殚}學(xué)的發(fā)達(dá),聚集的福建地區(qū)的學(xué)者都各執(zhí)己論,這才讓人不能正確的解釋何為閩學(xué)。因?yàn)槲幕姆睒s碰撞,各學(xué)者紛紛著書立說,有的甚至親自從事刻書業(yè);朱熹就曾經(jīng)親自刻印自己的著作。很顯然,余氏在有如此濃厚的文化氛圍內(nèi)從事刻書業(yè),且自身又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yǎng),這也就不難理解余氏刻書業(yè)可以執(zhí)福建坊刻業(yè)之牛耳了。
有了如此優(yōu)越的自然人文和經(jīng)濟(jì)條件,余氏的坊刻業(yè)在當(dāng)時(shí)也已經(jīng)有很大的規(guī)模,其刻印質(zhì)量也并非與麻沙本那樣粗陋不堪。宋葉夢(mèng)得的《石林燕語》卷八談及宋代版刻情況:“今天下之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4]這可以說明福建坊刻業(yè)最發(fā)達(dá),所刻書籍最受世人所喜愛。
南宋時(shí),建安余氏的刻書業(yè)是福建乃至全國(guó)最大的坊刻。余氏刻書又以余仁仲萬卷堂最為著名,他刻書頗豐。流傳至今且非常著名的還有十幾種之多,其中以所刻九經(jīng)本最善,在當(dāng)時(shí)就被當(dāng)作佳本了。除了余仁仲萬卷堂的刻書之外。余氏刻書還有余唐卿的明經(jīng)堂,宋寶裕癸丑(1254)刊許叔微撰寫的《類證普濟(jì)本草方》10卷及后集10卷,余彥國(guó)勵(lì)賢堂刊《新編類要圖注本草》42卷《序列》5卷《目錄》1卷。
余氏除了刊刻儒家經(jīng)典和醫(yī)學(xué)藥書之外,也刊刻士人應(yīng)舉所需之書。據(jù)肖東發(fā)教授考證:“僅建陽余氏所刻諸生用《四書》一類,就有集注、大全、精義、會(huì)解、講義、說范、圖解、句意、句訓(xùn)、名物考以及拙學(xué)素言、披云新說、夢(mèng)關(guān)醒意、萃談?wù)l(fā)、兜要妙解、天臺(tái)御覽、目錄定義等多種名日”余氏所刻的科舉用書,其釋例之詳細(xì),這從一個(gè)側(cè)面也說明了當(dāng)時(shí)福建地區(qū)是非常重視科舉的。也反映了建安余氏的刻書業(yè)為何如此發(fā)達(dá),畢竟又如此龐大的消費(fèi)群體啊。
建安余氏在的刻書業(yè)從余仁仲起正式發(fā)跡,并一直興盛之明中葉以后。余氏的刻書業(yè)能如此的長(zhǎng)盛不衰除了余仁仲開了個(gè)好頭之外,余氏家族的刻書風(fēng)氣及素養(yǎng),以及福建優(yōu)越的自然經(jīng)濟(jì)條件和濃厚的文化氛圍也是重要的條件之一。
參考文獻(xiàn)
[1]清《王先謙·續(xù)東華錄,乾隆卷八十一,別見》清高宗實(shí)錄卷九七五。
[2]民國(guó)·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民國(guó)郋園先生全書本。
[3]朱維干《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宋·葉夢(mèng)得《石林燕語》,中華書局,1997年版 ,第116頁。
作者簡(jiǎn)介
張遠(yuǎn)歡(1991-),男,廣西玉林人,碩士研究生,中國(guó)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