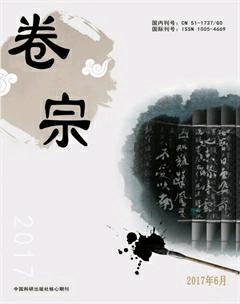勞動者嚴重失職認定的法律研究
張帆
摘 要:《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關(guān)于勞動者“嚴重失職”的規(guī)定,在適用時,會產(chǎn)生對“嚴重”的認定無所依據(jù),“重大”損害的參考缺乏標準。關(guān)于勞動者“嚴重失職”的認定,涉及到何種標準?嚴重程度?和由誰認定?三個問題,本文通過案例與地方性法規(guī)的研究來對該問題進行回答,并提出相對具體化的解決辦法。對于該三個問題的回答,可以說是對用人單位“嚴重失職”解約制度構(gòu)建的一種設(shè)想。
關(guān)鍵字:嚴重失職;嚴重性;重大損害;具體化
《勞動法》第二十五條和《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中均以“勞動者嚴重職,營私舞弊,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的”的表述規(guī)定了勞動者“嚴重失職”時,用人單位即可因此解除勞動合同。但存在缺陷的是其后并未對“嚴重失職”作出具體的規(guī)定,也沒有將“重大損害”進行具體的說明,這樣就會使得用人單位在適用時,對“嚴重”的認定無所依據(jù),“重大”損害的參考缺乏標準。關(guān)于勞動者“嚴重失職”的問題,因涉及到勞動者會造成被依法解約的法律后果,所以必須嚴格對待,不僅是上面提到的標準性問題,還涉及一系列相關(guān)問題,如:由誰認定?何種標準?嚴重性問題?
1 何種標準?
通常理解,失職行為一定是和職責(zé)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現(xiàn)實社會行業(yè)眾多,職責(zé)不同且差距較大,“嚴重失職”的標準在現(xiàn)實層面來看,要想在法律層面作出具體的規(guī)定是幾乎不可能的。實踐中,法院在認定時所參考的標準一般是勞動合同、規(guī)章制度和仲裁、法院的認定為主。但認定依據(jù)主要還是得靠用人單位內(nèi)部所確立的與員工崗位職責(zé)相關(guān)的規(guī)章制度,即企業(yè)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
勞動者“嚴重失職”的依據(jù)以用人單位規(guī)章制度為準,這是現(xiàn)實的,也是最合理的。但用人單位的規(guī)章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合理性,有些規(guī)章制度也不一定符合勞動法的立法目的,所以這就存在一個前期問題,即用人單位的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能夠成為認定勞動者“嚴重失職”標準所應(yīng)具備的條件問題。
2 “嚴重失職”的認定
勞動者“嚴重失職”通常是指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期內(nèi),未按照崗位職責(zé)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wù),違反忠于職守、維護用人單位利益等義務(wù),存在嚴重過失或者故意行為。但毋庸置疑,對于“嚴重失職”的認定來說,不單看勞動者的行為,還要結(jié)合行為后果來判斷 。只有“嚴重失職”和“重大損害“同時出現(xiàn)時,才會使用人單位享有即時解除權(quán)。但上文提到由于法律對此規(guī)定的非具體化,導(dǎo)致了對認定勞動者的行為,及行為程度達到“嚴重失職”存在不確定性,對“重大損害”的認定也存在無標準的情形。
(一)失職的嚴重性
“失職”是工作人員不認真負責(zé),未按照規(guī)定來履行自己的職務(wù),給用人單位或服務(wù)對象造成損失的行為。則“嚴重失職”意味著,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期間,對于約定的合同內(nèi)容,有未盡職守違反其本職義務(wù)的突出過失行為,并給用人單位造成相當(dāng)?shù)膿p失和不利后果。勞動者違反崗位職責(zé)的行為有一般和嚴重的區(qū)別,依據(jù)《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的規(guī)定,“嚴重失職”的描述則重在點明了情節(jié)的區(qū)別。但令人扼腕的是,后文卻未順承該規(guī)定,進一步界定一般和嚴重區(qū)別,或?qū)乐剡M行具體的展開性表述,由此導(dǎo)致實踐中出現(xiàn)因勞動者收入百元面值的假鈔而被解雇、因勞動者與客戶爭吵而被開除等五花八門的原因出現(xiàn)。上文已經(jīng)分析了用人單位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作為認定勞動者“嚴重失職”的合理性,但規(guī)章制度若未對嚴重失職的行為未做出明確規(guī)定,或不滿足上文所提到的三個條件時,即規(guī)章制度是勞動者在不知情、不了解自身職責(zé)的情況下制定的,那該規(guī)章制度顯然就不能作為法院審案的依據(jù)。這時候的嚴重性該如何認定?況且即便規(guī)章制度對“嚴重失職”有著具體的規(guī)定,但并不意味著其規(guī)定就是合理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對“嚴重失職”的“嚴重性”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二)損害的“重大性”
重大損害可以說與“嚴重失職”是一種結(jié)果和行為的關(guān)系,“重大損害”可以說是“嚴重失職”認定的必備條件,兩者對于用人單位依法解除勞動合同來說缺一不可。但什么樣的損害才是重大的呢?
解決該問題的方向只有兩個,即事前規(guī)定和事后評價。事前規(guī)定意味著勞動者在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時,就可以用現(xiàn)成的標準來衡量,而事后評價則無依據(jù),靠的是法院或其他主體予以認定。事前規(guī)定顯然是相對公正合理的,因為事前規(guī)定后,勞動者對標準的制定是可以協(xié)商的,對其行為后果是可以預(yù)期的,
3 由誰認定?
當(dāng)勞動者出現(xiàn)“嚴重失職”的情形時,肯定是用人單位首先對該行為進行了認定,并作出了決定,否則就不會產(chǎn)生因“嚴重失職”而解約的糾紛。這里就涉及一個認定主體的問題,即勞動者“嚴重失職”由誰說了算?
結(jié)合學(xué)者論述,目前針對該問題主要有三種觀點。觀點一認為,實踐中因《勞動合同法》并未指明認定權(quán)由誰行使,用人單位則理所當(dāng)然地自主認定勞動者“嚴重失職”的行為,同時輔以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作為依據(jù)。這種觀點評價起來就是用人單位既當(dāng)“運動員”又當(dāng)“裁判員”,認定結(jié)果肯定不易信服。觀點二認為,許多企業(yè)單方解除與勞動者的勞動合同,往往以《勞動合同法》規(guī)定為依據(jù), 但是,勞動者是否 “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的”,并不應(yīng)該只是單方說了算。該觀點明確質(zhì)疑了用人單位單方認定的合理性,表示應(yīng)由第三方介入。觀點三認為,重大損害的界定權(quán)首先是在用人單位,但并不說明用人單位可以隨意界定,用人單位的界定,比如損害本身很小,而將其界定為“重大損害”,這種情形應(yīng)該是很常見的,這就會違反“公平、合理”的原則,不能被采用,所以關(guān)于勞動者“嚴重失職”的認定,只能由仲裁機構(gòu)和法院予以認定。
總結(jié)起來看,關(guān)于勞動者“嚴重失職”的認定主體可以是用人單位,或者是用人單位與其他他第三方共同認定,或者就是只能依靠仲裁機構(gòu)和法院來認定。關(guān)于該問題筆者認為,用人單位是界定勞動者是否“嚴重失職”的第一認定主體,這是符合實際的,因為,只有用人單位作出“嚴重失職”的認定時,才會導(dǎo)致問題的開始,所以用人單位是勞動者“嚴重失職”認定的第一主體。如果用人單位作出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之后勞動者并未提出異議,未申請仲裁、提起訴訟,那就不會有糾紛的產(chǎn)生,用人單位是第一認定主體,同時也是最終認定主體。倘若勞動者有爭議,對此申請仲裁、提起訴訟,那這個時候用人單位的認定自然是要打個問號的,一切都應(yīng)以仲裁機構(gòu)、法院的認定為依據(jù)。所以產(chǎn)生爭議后的最終認定主體就是仲裁機構(gòu)、法院。
參考文獻
①王全興:《勞動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②徐海峰、徐以斌:《勞動法》第25條的法律內(nèi)涵及運用,中國勞動,2002年8月份,第34-36頁。
③正愛清:《完善我國勞動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和建議》,法學(xué)雜志,2007年第3期,第37頁。
④黎劍飛:《勞動合同解除的難與易》,法學(xué)家,2008年第二期,第23頁。
⑤鄭橋,姜穎.《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我國勞動關(guān)系的影響,新視野,2008年1月10日,第60-62頁。
⑥林娟:《用人單位“嚴重失職”解約制度的構(gòu)建》,福建江夏學(xué)院學(xué)報,2012年10月第二卷第五期。
⑦王霞、陳陣香:《勞動合同法立法技術(shù)缺陷及完善》,2014年7月,第38卷第4期。
⑧高艷:《對我國解雇行為程序規(guī)制內(nèi)容的探討》,2014年7月,第17-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