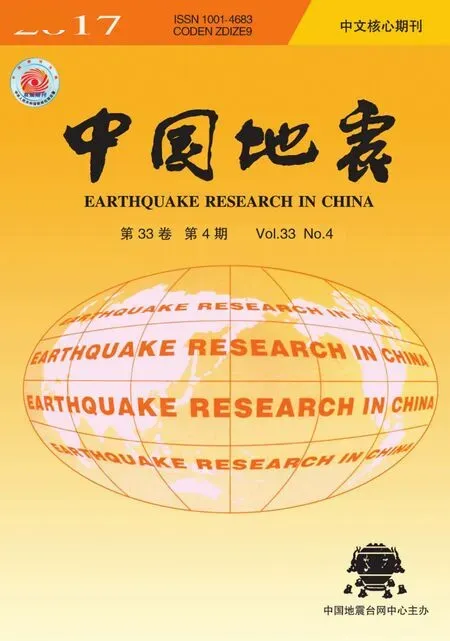九寨溝7.0級地震前地殼水平形變狀態與變化
楊博 梁洪寶 趙靜旸 占偉 楊國華
中國地震局第一監測中心,天津市河東區耐火路7號 300180
0 引言
2017年8月 8日四川九寨溝縣(33.14°N,103.7°E)發生MS7.0地震,震源深度 20km(http://www.csi.ac.cn),該地震發生在巴顏喀拉塊體東緣岷江斷裂、塔藏斷裂和虎牙斷裂附近,余震分布以NW向展布為優勢。歷史上在該區周邊(100km之內)多次發生6級以上地震,近期發生的震級最大地震為 1976年 8月 16、23日松潘-平武 2次 7.2級地震(http://www.csi.ac.cn)。這充分表明該區域為構造活動非常強烈的區域。由于近十幾年來中國大陸強震活動主要圍繞著巴顏喀拉塊體的邊界斷裂展開(陳長云等,2012a、2012b、2013;譚凱等,2011;王敏,2009;聞學澤等,2011;許才軍等,2009;徐錫偉等,2008b;楊國華等,2012、2015;張培震等,2009;趙靜等,2012),所以,九寨溝7.0級地震也是巴顏喀拉塊體邊界斷裂持續活動的產物。因此,了解發震區域及其周邊現今構造活動狀態及其動態變化,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與此次地震的發生是否存在某種關系,可豐富我們對該地震孕震機理和場兆的認識。本文利用1999~2015年區域流動GNSS復測資料以及多核函數法分時段進行地殼構造活動變形狀態及動態變化的描述,以期比較詳細地了解此次地震形變場的時空變化特征。
1 數據處理流程與方法簡述
在球面上獲得研究區運動場之后,可利用多核函數法進行運動場的數值解析

式中,dj為球面上2點間的大地線長度;(λj,φj)為核點位置坐標(以km為單位);C=(c1,c2,…,cnx)為系數陣;ST=(s1,s2,…,snx)為核函數陣。然后,利用式(1)分別對東向和北向進行網格化數值計算,并為它們實施濾波處理

式中,A=(a1,…,anx)、B=(b1,…,bnx)均為待定系數;(λi,φi)和di的含義同式(1)。
依據最小二乘法求解上述任意方向運動的待定系數。此時,經濾波后的水平運動的解析式為

在此基礎上,依據下式便可獲得有關的應變與旋轉量結果等。

式中,R為地球的平均半徑;sλ和sφ分別為經向和緯向的弧長;γmax(λ,φ)為最大剪切應變;εmax(λ,φ)為最大主應變;εmin(λ,φ)為最小主應變;ω(λ,φ)為旋轉量;εE(λ,φ)為 EW向應變;εN(λ,φ)為SN向應變;γEN(λ,φ)為EW向與SN向之間的剪應變。
2 水平形變場及其動態變化特征
至 2015年底,在研究區已進行了 8次全面觀測,分別為 1999、2001、2004、2007、2009、2011、2013、2015年。為了了解動態變化,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前后的動態變化,故所用資料分成4個時段進行處理,即 2007年以前、2009~2011、2011~2013、2013~2015年,2007前解算精度為 0.6,之后 3期結果解算精度為 1.0。數據處理時,首先利用 GAMIT/GLOBK/QOCA軟件獲得該時段ITRF參考框架下運動的“觀測結果”;在此基礎上,利用上述的處理流程與方法獲得核點步長為100km、網格點步長為25km的運動場濾波與解析結果以及相應的各種應變與形變場(楊博等,2010、2011;楊國華等,1995);為了利于觀察,最后,將ITRF框架下的運動場轉換為相對于四川盆地的運動場。4個時段的運動場結果如圖1所示。
圖1(a)為1999~2007年的水平運動場,也是汶川地震前的運動場。由圖1(a)可見,鮮水河以東龍門山以北的川西高原不論龍門山斷裂帶還是龍日壩斷裂帶(這里特指NE向構造段)幾乎都觀察不到明顯的擠壓性運動,即垂直于這2條斷裂帶方向上相對于四川盆地的運動幾乎為零,運動方向基本上平行于這2條斷裂帶,運動量由南向北逐漸變大,由西向東逐漸變小,整體表現為右旋變形運動。已有的研究表明,這一時段的運動是以龍日壩斷裂帶為中心的右旋變形運動(徐錫偉等,2008a),與圖1(a)所反映的結果一致,并且這種變形狀態通過九寨溝震區一直向東北方向延續。這就是說,我們看不到震源區NW向構造存在左旋形變的跡象,若按此結果,則判定發震斷裂應為NE向構造。但這是汶川地震前龍門山斷裂帶活動閉鎖條件下的結果。事實上,汶川地震以后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結果(圖1(b)~1(d))。雖然,這3個時段的結果為非完全常態下的運動結果,但體現了龍門山斷裂帶活動解鎖時的運動形式。因此,包含著常態運動的某些屬性。從性質上看,川西高原及其東部區域3個時段的運動結果是一致的;而量級則隨著時間的延續而變小。這是汶川地震震后粘滯性松弛型效應等所致。汶川地震震后的結果可歸納為,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不僅有右旋,而且逆沖擠壓活動更突出;龍日壩斷裂帶及周邊仍以右旋活動為主,但沒有沿著走向穿過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向NE向延續;相反,在該震源區NW向構造上我們觀察到了左旋構造變形。鑒于汶川地震前后的2種運動狀態,我們有理由認為,九寨溝地震的孕育與發生與汶川地震或者說與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有一定的關系。同時,我們也認識到,若周邊斷裂帶活動閉鎖時,僅以閉鎖前不全面的監測結果進行分析可能會出現偏差;此外,由于九寨溝地震發生在運動較弱但不是最弱的區域上,因此,也不能簡單地以運動量的大小來分析強震危險性。

圖1 四川東北區域 1999~2007年(a)、2009~2011年(b)、2011~2013年(c)和 2013~2015年(d)、水平運動

圖2 四川東北區域 1999~2007年(a)、2009~2011年(b)、2011~2013年(c)、2013~2015年(d)主應變方向及大小
圖2是以應變張量形式展現主應變大小和方向的空間分布狀態。由圖2可見,不論是汶川地震前還是之后,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及其周邊時段性構造變形的主壓方向基本上為EW向。這就是說,區域增量應力場作用的基本特征并沒有因為汶川地震而發生質的變化。汶川地震前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壓性主應變相對較弱,張性主應變相對更弱,幾乎難以識別(圖2(a));汶川地震之后張性主應變強于壓性主應變,但基本上分布于孕震區的西側,震源區及其東側未見明顯的張性應變,壓性應變仍具有優勢,但隨著震后時間的推移,東側的壓性應變逐步減弱(圖2(b)~2(d)),至2015年時比汶川地震前還弱。這說明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及其東側臨震前的應變積累可能飽和。總之,九寨溝地震震源區的主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又處于相對較弱的狀態;也顯現了臨震前較強地震的主應變可能較弱,汶川地震前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則最為典型(圖2(a))。

圖3 四川東北區域 1999~2007年(a)、2009~2011年(b)、2011~2013年(c)、2013~2015年(d)最大剪切應變率
最大剪切應變是反映地殼變形尤其是斷裂帶活動最直觀的形變參量。圖3(a)為1999~2007年的最大剪切應變率。由圖3(a)可見,除四川盆地最弱以外,其次為川西高原。在該區域最大剪切應變率的值域一般小于20×10-9/a。該區域比較典型的較高值條帶恰好是龍日壩斷裂帶及其NE向的延伸。這說明較高值條帶的出現是龍日壩斷裂帶右旋活動的結果,包括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并非是NW向的左旋活動的體現,這在圖1(a)中體現的非常清晰。應該說與此次九寨溝地震孕育沒有直接的關聯。汶川地震之后,川西高原的最大剪切應變明顯強于震前,2009~2011年時段最大,達 50×10-9/a(圖 3(b)),2013~2015年為30×10-9/a(圖3(d))。但就分布狀態而言,較大的剪切應變在川西高原上以 NW向更為優勢。這表明震后該區域左旋形變特征比較明顯,體現了NW向的構造活動比較活躍。汶川地震前不僅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空前閉鎖,而且正是由于該斷裂帶的閉鎖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巴彥喀拉塊體東邊界附近NW向斷裂的活動;隨著龍門山斷裂帶活動的解鎖,該處NW向斷裂的活動變得活躍,二者相輔相成。

圖4 四川東北區域 1999~2007年(a)、2009~2011年(b)、2011~2013年(c)、2013~2015年(d)水平旋轉率
水平旋轉率的差異變化實質上體現的是另一種形變,這里不妨稱為旋剪形變。如果在最大剪切應變難以辨別是左旋還是右旋構造活動所為時,旋剪變形則可直接給出標定。圖4為研究區4個時段旋剪變形的空間分布結果。其中,大于0時表示左旋旋剪形變;反之,表示右旋旋剪形變。由圖4(a)可知,川西高原1999~2007年旋剪形變基本特征為整體性的右旋剪切變形,龍日壩斷裂帶及東北區域旋剪形變較大,約為20×10-9/a。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及周邊區域沒有發現左旋剪切變形。這表明該區域NW向斷裂帶沒有活動的跡象,這種不活動并不一定意味著斷層活動已閉鎖,因龍門山斷裂帶活動是否閉鎖與該震源區斷層活動有一定的關系。汶川地震后2009~2011年的結果顯示,九寨溝地震震源區及岷江斷裂中南段等出現了顯著的左旋剪切變形,最大達55×10-9/a(圖4(b)),已遠大于鮮水河斷裂帶的左旋剪切形變。這就是說,龍門山斷裂帶解鎖后,岷江斷裂中南段、虎牙斷裂等的左旋活動得以恢復,并且強度超常。然而,塔藏斷裂帶并沒有表現出如此明顯的活動。2011以后雖然形變性質未發生變化,左旋活動仍呈NW向空間展布,但量級開始逐漸變小(圖4(c)、4(d)),2013~2015年該活動的最大值已經小于鮮水河斷裂區帶,震源區幾乎是左旋剪切形變最弱的部位。這樣的結果至少體現了震源區構造活動有一定的閉鎖性。

圖5 GNSS連續站三分量(NEU)時序變化
3 連續站的時序變化特征及同震位移
在九寨溝地震震中附近不同方位地域選擇了最近的4個GNSS連續觀測站,它們分別是西側的GSMA、北側的GSMX、東側的GSWD和南側的SCSP站。距震中最近的站為SCSP,距離約為70km,最遠的站為GSMA,約200余千米。為了更直觀顯現構造運動,我們對觀測值進行了非構造運動剔除和共模誤差削弱的處理,結果如圖5所示。由圖5可見,南向運動(圖 5(a))速度分別為 4.46、6.69、9.35、9.75mm/a,同樣表現為西北較小、東南較大的近 SN向張性形變特征,距震中最近的西南側SCSP和東側GSWD站間也同樣體現為左旋的形變性質。此外,還存在著南向的加速運動,其加速度分別為0.89、0.49、0.48、0.52mm/a2,這除說明區域形變已進入非完全線彈性階段以外,還說明左旋形變有所加速的趨勢性特征。東向運動的差異也較明顯(圖 5(b)),趨勢性運動速度分別為 40.71、37.26、34.64、40.31mm/a,也體現了近EW向“西大東小”的擠壓形變特征。然而,其運動具有減速的跡象,加速度分別為-0.10、-0.25、-0.09、-0.87mm/a2,與南向加速運動恰好相反,但程度不如南向。垂向運動的速度分別為 0.62、1.15、1.02、1.71mm/a,整體與差異變化均較弱小(圖 5(c)),但加速變化并非最弱,其值分別為 0.66、0.77、0.43、0.42mm/a2,距震中最近的 2個站(GSWU和 SCSP)最小。在以往大震震例研究中發現,震前震源區垂直形變是較弱的(楊國華等,1995),本文研究中亦看到了加速度較弱的現象,這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總結與驗證。由上可知,區域場的形變特征在連續站上得到了體現,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細微的變化在連續站上也獲得了體現,如加速變化等,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然而,我們卻沒有發現具有短期意義的“震兆現象”。同震位移表明,只有最近的SCSP站向南移動了約7.1mm,其他分量和其他測站均未出現可辨的同震變化。這說明地震同震影響的空間范圍較小。
4 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九寨溝7.0級地震之前,川西高原存在著2種性質不同的形變狀態。以汶川地震發生的時間為界,震前川西高原整體為NE向運動,其特征為“北大南小”“西大東小”,整體構造活動為以龍日壩斷裂帶為中心的NE向右旋活動,并不存在NW向左旋構造活動。這與該區域NW向斷裂帶活動性質不吻合。因此,我們認為這種形變狀態并非是一種常態,而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形變狀態,或者NW向斷裂活動整體閉鎖。事實上,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是閉鎖的。川西高原東部NW向斷裂活動與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有一定關系。因為龍門山斷裂帶若活動(逆沖活動),則有助于作為巴彥喀拉塊體東北緣(川西高原東部)NW向斷裂的左旋活動,否則會對該向斷裂左旋活動起抑制作用。當然,也不能排除九寨溝地震孕震區的活動已達到某種程度的閉鎖,否則,1次7級地震不太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孕育成熟。
此外,從地震活動的空間分布來看,之前所發生的較強地震均位于此次九寨溝地震的南側,并對應于左旋剪切形變的高值區,而此次地震則位于左旋剪切形變的低值區。汶川地震之后,隨著龍門山斷裂帶活動的解鎖,上述NW向斷裂即刻顯現了左旋旋剪形變,而且非常顯著。雖然汶川地震震后還包含著粘滯性松弛效應,但強度明顯弱于監測結果(楊博等,待刊)。這就進一步說明了二者活動間的關系確實是相輔相成的。震源機制解及余震分布表明為NW向破裂,這與震源區及周邊的左旋旋剪形變和同震位移也完全吻合,展現了該地震的構造活動背景。從地震活動關聯性的角度觀察,汶川地震之前,由于龍門山斷裂帶活動的閉鎖使NW向斷裂活動受到抑制,即抑制了該斷裂強震能量的較快積累,因此,強震發生的時間必然有所推遲;相反,汶川地震發生后又使得該NW向斷裂強震能量超常積累,由此也使得強震的發生會有所提前,二者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需要指出的是,若只有或只依賴于1999~2007年的監測結果,我們很可能會得出錯誤的認識。因此,全時空監測、全過程分析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