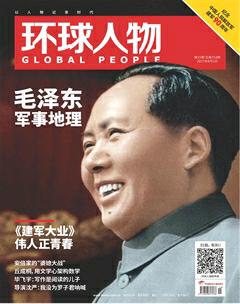山野電報 敵百萬軍
李靜濤



西柏坡、錦州、徐州
五律?喜聞捷報
一九四七年九月
中秋步運河上,聞西北野戰軍收復蟠龍作。
毛澤東
秋風度河上,大野入蒼穹。
佳令隨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鴻音絕,妻兒信未通。
滿宇頻翹望,凱歌奏邊城。
中國地圖給人的視覺效果,似乎東北離北京很近。但如果有過從北京坐火車去東北的經驗,就知道東北絕不像地圖上看起來那么好走。在沒有高鐵時,北京到哈爾濱的火車,特快也需十幾個小時,幾近從北京南下長江腹地的時間。所以冷兵器時代,“入關”“出關”是兵家大事,最典型的就是明朝末年,發生在山海關內外的數次激戰。
如果把中心坐標從北京換成西柏坡,距離則更遠。西柏坡到錦州的直線距離是700多公里,先汽車后高鐵,前后大約需要8個小時。這是在今天。近70年前,毛澤東人在西柏坡,指揮關外的千軍萬馬攻打錦州,繼而解放東北全境,時空距離之遠,真正是“決勝千里之外”了。
從西柏坡南下徐州,交通條件比北上便捷,500多公里,走高速4個多小時到達。當年,遼沈戰役11月2日結束,淮海戰役11月6日開始,毛澤東幾乎是無縫銜接,轉身向南看。徐州戰場撬動了整個淮河流域的解放,在國民黨那邊,就把這場戰爭叫“徐(州)蚌(埠)會戰”。
《環球人物》記者輾轉遼寧、河北、江蘇三省,在解放戰爭的幾個關鍵地點尋找當年的痕跡,重溫這段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輝煌往事。
西柏坡:一部電話,兩張地圖,三張桌子
今天的西柏坡村已非當年原址。“1958年,由于修建崗南水庫,原本在山腳下的中共中央舊址搬遷。上世紀70年代初,在距舊址500米、海拔高出57米的山腰進行了復原,名字還是西柏坡。”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講解員吳曉月指著不遠處的崗南水庫說道,“這里的文物都是原件,房屋布局也和原來一樣。不同的是毛澤東當初住的是土坯房,復原后是磚結構房子。”
以1947年那首《五律·喜聞捷報》為標志,國共戰場的局面開始朝著有利于中共的方向發展。自從主動撤離延安后,一直在陜北各地轉戰的毛澤東有了新打算——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更直接地掌握全國各個戰場的情況,以便指揮作戰。
其實,在國民黨胡宗南部占領延安后不久,劉少奇等人率領的中央工委就開始為中央尋找新落腳點。中央工委臨行前,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們就到白毛女的故鄉去吧。”劉少奇見到身在晉察冀的聶榮臻時,第一句話就是:“白毛女的故鄉在哪呢?”聶榮臻答:“就在河北平山縣啊。”因此,中央工委選定了平山縣西柏坡村落腳。當毛澤東最終決定中央東移時,目的地已很明確。
1948年3月21日,轉戰陜北一年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動身,告別了生活十余年的黃土高原,踏上了前往西柏坡的旅途。在如今的西柏坡紀念館中,有一張中共中央從陜北到西柏坡的路線圖。毛澤東東渡黃河,翻過呂梁山,在5月底來到了這個太行山腳下的小村莊。
“選擇西柏坡并非是毛澤東一時興起。”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宇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西柏坡地處河北省西部,距離東北、西北、華北、中原、華東等解放戰爭的主要戰場都不遠,居中指揮有優勢。另外,西柏坡地處山區,在抗戰和解放戰爭初期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利于保密和隱蔽,相對安全。”當時,在中央的院子附近還住著幾戶百姓,雖然天天和中央領導見面,但人人守口如瓶,中央在此的信息從未泄露。國民黨幾次派特務探聽毛澤東的具體位置,還轟炸過幾十里外的目標,就是不知道毛澤東住在西柏坡的農家小院。
毛澤東的住所是借用百姓的房子,院子里樹下的磨盤也沒搬走。毛澤東有時會搬把椅子在樹下乘涼。這個磨盤見證了他難得的休閑時光,更見證了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遇到難以決斷的問題,周恩來、朱德等人會到毛澤東的住所來商量。夏天屋里悶熱,他們就到樹下的磨盤邊,毛澤東推著碾,其他人在一旁邊幫忙邊討論。
與毛澤東居所相隔二三十米,便是中央軍委的作戰室——解放軍的指揮中樞,數百萬部隊的行動指令經由這里發出。這樣一個重要的場所,卻狹小簡陋得出人意料:土屋里只有一部電話,墻上掛著兩張地圖,其中一張還是用抗戰期間繳獲的多份日軍地圖拼接而成,三張桌子依次排開,分別是作戰科、情報科和戰史資料科的辦公桌。毛澤東曾無數次夾著香煙,站在地圖前思考解放軍下一步的作戰計劃。有感于這段往事,周恩來曾說:“我們這個指揮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我們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就是天天發電報,就把國民黨打敗了!”
據不完全統計,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澤東前后發出了400多封電報,指揮了24次大規模戰役,這其中就包括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直到今天,西柏坡的民歌里還有一句詞:磨盤上布下雄兵百萬,土屋里奏響勝利凱歌。”吳曉月說。
錦州:70多封電報督促林彪
早在1945年召開黨的七大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就預見到抗戰勝利后,如果內戰爆發,東北是國共兩黨爭奪的主要戰場。七大一結束,黨中央就往東北派遣部隊,許多高級干部也前往東北。與此同時,國民黨軍也不斷向東北增兵。因此,還在內戰全面爆發前,東北已經有了大規模軍事沖突。內戰開始后,東北戰場一直很激烈。
1948年夏,毛澤東抵達西柏坡后不久,敏銳地察覺到解放戰爭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開始考慮即將到來的大決戰。他選擇了形勢最好的東北戰場作為大決戰的起點。
“遼沈戰役是1948年9月正式開始的,但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了錦州之于整個東北戰場的重大意義。”陳宇說。對于錦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環球人物》記者頗有感觸:出山海關之后一路向東北,鐵路的東、南方向地勢平坦,直達海濱;向西、北方向望去,不遠處便能看到起伏的山脈。在錦州遼沈戰役紀念館,講解員指著東北地形圖說:“東北平原雖然廣闊,但只有渤海沿岸狹窄的平原地區能方便地通往山海關內,錦州就位于這一咽喉處。毛澤東意識到一旦攻下錦州,就是掐住了敵人的脖子,國民黨的幾十萬人馬就會被困死在東北。”endprint
1948年初,毛澤東就曾發電報給東北野戰軍司令林彪,以商量的口吻問:如果我軍控制錦州一帶,對于應付蔣軍撤退至山海關內是否更有利?林彪收到了電報,但心中另有打算。此時,東北野戰軍主力集中在吉林,林彪擔心南下攻打錦州,萬一敵人援軍一到,加上長春的十萬敵軍,很可能陷入被南北夾擊的困境。思慮再三,林彪請示中央后下達了先圍攻長春的命令。
林彪沒有想到,長春久攻不下。蔣介石看準時機,打通了沈陽到錦州的鐵路,一部分國民黨部隊撤回關內。聽到這個消息,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指揮所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大發脾氣:“林彪再不行動,沈陽、錦州的人都要溜掉了!”隨后,他給林彪發去電報,言辭中透出不滿:“在你們準備攻擊長春期間,我們即告知你們,不要將南進作戰的困難條件說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將自己限制起來,失去主動性。”但林彪還是沒有下定決心,在給中央軍委的回電里說,部隊南下錦州所需的糧食無法解決,出動時間“仍是無法肯定”。
毛澤東終于忍不下去了,給林彪發去了言辭犀利的電報:“關于你們大軍南下必須先期準備糧食一事,兩個月前亦已指示你們努力準備。兩個月以來,你們是否執行了這一指示,一字不提。現據來電,則似乎此項準備工作過去兩月全未進行,以致現在軍隊無糧不能前進。為使你們謹慎從事起見,特向你們指出如上。你們如果不同意這些指出,則望你們提出反駁。”接到電報后,林彪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次日,他回電委婉地解釋了糧食問題,并保證盡快行動,攻打錦州。
1948年9月,林彪終于率東北野戰軍主力向錦州附近的鐵路線發動進攻,準備切斷錦州和沈陽以及關內的聯系。蔣介石聞訊慌忙飛往北平、沈陽,調集軍隊馳援錦州。
得知國民黨大軍增援,林彪又動搖了,心想“預備了一桌菜,來了兩桌客人”。10月2日深夜,林彪寢食難安,口授了一封給中央的電報,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繼續攻打錦州,但困難多,沒有十足把握;第二,回師長春,把握很大。他表示:以上兩個方案,我們正在考慮中,并請軍委同時考慮與指示。很明顯,林彪傾向第二種方案。東北野戰軍政委羅榮桓考慮再三,認為林彪這樣做不妥,說服他撤回電報。不過,此時電報已然發出,羅榮桓又親自擬定一份電報,提出撤回前一份電報,增加錦州地區的作戰兵力。
次日清晨,毛澤東先收到了第一份電報,非常不安。他連用“不敢打”,給林彪回了一封語氣嚴厲的電報:“5月和7月間,長春之敵本來好打,你們不敢打。現在錦州部署業已完畢,你們又因一項并不很大的敵情變化,又不敢打錦州,又想回去打長春,這是很不妥當的。”兩個小時后,放心不下的毛澤東又發了一封電報,說明打錦州的好處。直到收到羅榮桓發來的第二封電報,他才松了一口氣:“你們決心攻打錦州,甚好甚慰。”
在毛澤東的督促下,林彪終于不再動搖,并將東北野戰軍的前線指揮部搬到了錦州西北僅20公里外的牤牛屯村。此后的情況眾所周知:10月14日,東北野戰軍只用了31個小時就攻下錦州;一個星期之后駐守長春的國民黨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率部起義,長春和平解放;11月上旬,沈陽、營口、葫蘆島等地相繼解放,遼沈戰役勝利結束。
關于遼沈戰役的這段歷史,人們有種說法:“槍炮打了不到兩個月,電報卻打了大半年。”戰役前后,毛澤東給林彪發了70多封電報,核心內容多是圍繞攻打錦州的問題。1963年羅榮桓去世,毛澤東有感于他在錦州戰役中發揮的作用,在悼念詩中還不忘寫道:“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
徐州:兩次調整判斷,再三協調將領
相較于錦州的依山傍海,徐州地區多為平原,京杭大運河從中穿過,隴海、京滬兩大鐵路干線相交于此,一直有“五省通衢”之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徐州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抗戰期間,中國軍隊也曾展開徐州會戰,與日軍血戰。而解放戰爭期間,徐州又多了層特殊意義:一旦攻下徐州,就能控制長江北岸,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上海就會暴露在解放軍的兵鋒之下。
就在遼沈戰役進行期間,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他給中央軍委去了一封電報,提出為了改善中原戰局并為將來南渡長江做準備,“建議進行淮海戰役”。粟裕對毛澤東說:“如果部隊攻克濟南后進行休整,自然有好處,但是容易失去作戰時機。秋天涼爽,適于作戰,而且敵人在丟了濟南后精神壓力很大,對我們有利。”
對于粟裕的建議,毛澤東深以為然,很快復電同意乘勝進行淮海戰役。他還提出了具體的作戰目標:殲滅駐守徐州東側的黃百韜兵團,奪取淮陰、淮安和海州,打通山東和蘇北的聯系。不難看出,在毛澤東的最初計劃中,淮海戰役的規模不算太大,但毛澤東時刻注意國民黨軍隊的行動,很快意識到如果進攻黃百韜兵團,國民黨勢必支援,淮海戰役的規模就會變大。
考慮到這些,毛澤東又給粟裕發去了一封電報:“這一戰役必比濟南戰役規模要大……因此,你們必須有相當時間使攻濟兵團獲得休整補充,并對全軍作戰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內,有充分之準備,方能開始行動。”這是淮海戰役前后,毛澤東第一次調整自己的戰略判斷。
基于淮海戰役規模可能變大的判斷,毛澤東考慮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聯合作戰。為此,他需要理順兩大野戰軍將領在指揮權上的關系。當時,陳毅在中原野戰軍任第一副司令員,但仍兼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是華東野戰軍的代理司令員。而此時中原野戰軍的司令員和政委分別是劉伯承、鄧小平。據曾任粟裕秘書的鞠開回憶說:“以往兩大野戰軍的作戰沒有具體的戰役協同,粟裕不好直接指揮中原野戰軍。”于是粟裕給毛澤東發了電報:“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毛澤東了解粟裕不重名的性格——1948年5月陳毅調往中原野戰軍工作時,粟裕就沒接受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的職務,堅持由陳毅繼續兼任。因此毛澤東同意了粟裕在指揮權上的意見。
1948年11月6日,解放軍向黃百韜兵團出擊,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戰役正式打響。5天后,黃百韜兵團在向徐州撤退的途中,被包圍在距徐州50多公里的小鎮碾莊。經過11天激烈戰斗,黃百韜兵團全部被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殲滅,毛澤東的戰前部署初步得到實現。國民黨徐州“剿總”司令劉峙多年后回憶說:“第七兵團(即黃百韜兵團)的覆滅,就已經決定了這場戰役的勝負。”endprint
此時,毛澤東再次捕捉到形勢的變化,也再次調整了戰略判斷。11月1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評論:“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陳宇評價說:“此役一取勝,淮海一線至南京等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基本一馬平川。這種作戰條件很有可能加速戰爭的結束。”
毛澤東在做出第二次戰略判斷調整后,很快想到了成立領導機構統一指揮淮海戰役。11月16日,他起草了關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線總前委的電報:“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
毛澤東對總前委的具體指揮和運作考慮得也很周全。當初,華中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合并組成華東野戰軍后,陳毅提出“軍事上多由粟裕下決心”,得到毛澤東的采納。鞠開說:“毛主席沒有要粟裕到劉、陳、鄧住地去開會,相反,要劉、陳、鄧到粟裕住地開會,討論成立總前委的問題。我認為,毛主席這樣辦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淮海戰役是粟裕建議舉行的,應該由粟裕來通盤考慮。二、粟裕擅長大兵團作戰。三、華中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合并的時候,已經明確講過,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淮海戰役指揮,當然還是應該由粟裕負責指揮。所以這個會應該到粟裕住的地方來開。”在陳宇看來,與其說這是毛澤東的“將將”之道,不如說是他知人善任。“人都有個性,毛澤東了解人性,知道每位將領的性格、長處,所以能協調好他們的關系,保證戰役的順利進行。”
此后近兩個月的時間里,解放軍相繼殲滅了國民黨黃維、邱清泉等兵團,生擒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淮海戰役大獲全勝。毛澤東深知勝利來之不易,在稱贊前線指戰員時說道:“淮海戰役打得好,好比一鍋夾生飯,還沒完全煮熟,硬是被你們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短短4個月,在毛澤東足不出西柏坡的指揮下,解放軍的兵鋒橫掃長江以北的中國。“有了遼沈和淮海兩大戰役的基礎,平津戰役很快也勝利結束,解放戰爭大局已定。”陳宇說道。此后的渡江戰役,畢其功于一役,南京總統府的旗幟永遠地落下了。毛澤東的指揮部,也由西柏坡這個“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移向了北平城。
自1927年秋收起義投身建軍起,毛澤東22年的率軍征戰終告勝利。那一刻,他想的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仿佛是一種預見——迎接新政權的,將是又一場滄桑征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