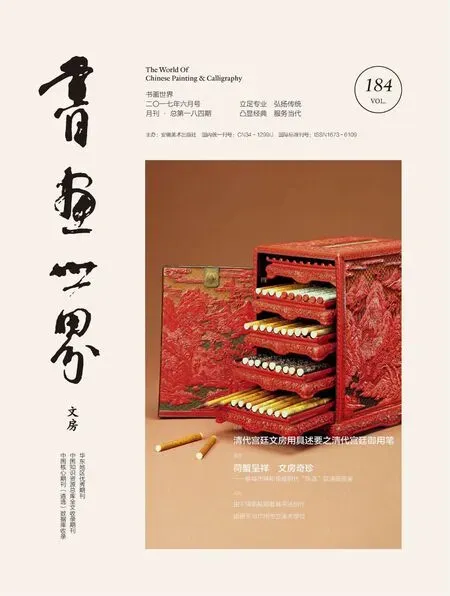淺談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
文_金鑫
淺談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
文_金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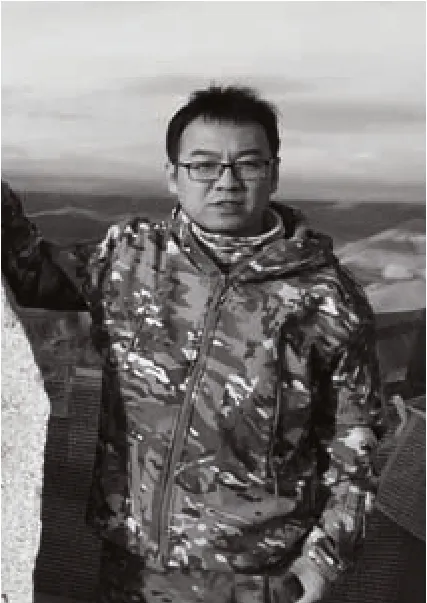
金 鑫Jin Xin
談到藏族聚居區,一般都會認為是西藏,但從嚴格意義來講,藏族聚居區分為三個部分,即安多藏族聚居區、康巴藏族聚居區和衛藏。安多藏族聚居區位于羌塘高原,介于四川、甘肅、青海三省與西藏自治區接壤的高原地帶,其包括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亦包括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和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康巴藏族聚居區位于橫斷山脈的山河夾峙之中,其包括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地區、木里藏族自治縣,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衛藏是以雅魯藏布江流域為中心,主要以岡底斯山脈和念青唐古拉山脈大斷裂帶為劃分,衛藏包括拉薩市、那曲地區、阿里地區、山南地區、林芝地區及日喀則地區,其中日喀則地區被稱為后藏。
藏族聚居區題材水墨風景寫生,是一個較為新穎的中國畫寫生題材。自20世紀以來,出現過一大批以藏族聚居區題材為表現內容的繪畫作品。如李鐵夫《拉卜楞寺街市圖》,孫宗慰《塔爾寺宗喀巴塔》《蒙藏人民民俗》,張大千《番女醉舞圖》《西康紀游》,關山月《源流頌》,吳作人《藏女負水》《藏原放牧》,葉淺予《西藏高原舞姿》《夏河浪山節》《高原牧笛》《拉薩長袖》,李煥民《高原峽谷》《草原牧歌》,馬振生《江孜青年》,方增先《帳篷里的笑聲》《母親》,吳冠中《羅布林卡》《扎什倫布寺》,李伯安《走出巴顏喀拉》,劉萬年《神山圣水圖》等,大多數畫家都以人物、宗教題材為表現對象。就水墨風景而言,當下所見到的代表性作品甚少。
內地畫家在進入藏族聚居區之前,對這一地區地貌特征僅限于意識中的認知,這種認知多來源影像資料、圖片、文字等。真正深入藏族聚居區之后,經過社會文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地域風貌等諸多方面體驗與感受之后,才會逐一認知。畫家對藏族聚居區的生活進行體驗,尤其是在藏族聚居區對景色、人文等觀察和思考,才會逐漸形成相對的認知,從而為寫生及創作藝術作品打造基礎和創造前提。石濤云:“筆墨當隨時代。”當深入藏族聚居區,面對自然之景,遠處的雪山、白云及近處的草地、牦牛、樹林、湖泊、房屋、寺廟等融為一體時,這種“神山圣水”的構圖及山水畫表現似乎在中國歷代山水畫圖式和技法中未曾出現過,亦沒有繪畫技法和經驗的總結,勾皴擦點染的山水法則面對如此般圣境,更多的是在畫面中體現對景色的感受性表現,這種感受無法用以往繪畫的經驗去表現,這即是畫家對藏族聚居區客觀世界的主觀印象。畫家方增先曾言:“最初去西藏的創作的目的是為了找尋形式感。西藏風土人情、自然景觀的夸張性,符合我對藝術創作的要求。寬大的藏袍、風吹日曬的臉龐,加上當地獨特的自然條件的惡劣,這些形式感上的變形都非常適合藝術創作的要求。”方增先對藏族聚居區的這些感受和認知是其藝術創作的前提條件。
唐代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把感性的認知轉化為理性的認識。元末明初的畫家王履在登臨華山時 “以紙筆相隨,遇勝則貌”,隨身攜帶繪畫工具,在自然中吸取繪畫素材,從而體悟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的藝術創作總結。同樣,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對于一個畫家來說,感受性的認知往往可以決定畫面是否不被程式化所束縛。經過近三年的藏族聚居區寫生和體驗,筆者認為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表現。

1.金鑫 岡仁波齊寫生40cm×70cm 2016
首先,藏族聚居區的山水樹木、人文景觀、文化習慣與內地有異,且藏族聚居區的風貌也有所不同。由于藏族聚居區處于高原地帶,自古以來交通不便,大多數畫家均未有直接來藏族聚居區交游或寫生的機會,故古代山水畫理論體系中亦無藏族聚居區山水畫寫生的理論依據。一種或多種技法、經驗無法適用于千變萬化的藏族聚居區地貌特征,這就必須因地制宜地進行寫生。正如宗炳《畫山水序》云:“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親身所到的地方,用具體的筆墨去描寫自然,依照實物寫生即可。例如在康巴藏族聚居區,由于海拔落差大,常可以看到樹木、河流與雪山同時出現在景色當中,當我們以中國古代山水畫體系中的樹石基礎來表現這種場景時,會覺得有種生搬硬套之嫌,也無法體現地貌特征。這就使我們在繪畫技法運用方面必須尊重景色的客觀性和對繪畫的筆墨感受性。而安多藏族聚居區則與康巴藏族聚居區有所不同。安多藏族聚居區有廣闊無垠的草原,山勢起伏多變,與歷代中國山水畫中的山石區別很大,部分山脈綿延數百公里,且氣勢磅礴,非古人畫法所能概括,亦不能以古人總結的皴法進行表現。衛藏山南地區、林芝地區植被又屬亞熱帶闊葉林,因而要對樹木的畫法進行選擇性提煉,否則運用古人的點葉之法概括會略顯呆滯。日喀則地區處于喜馬拉雅山脈北坡,跌宕起伏的山脈變化豐富,涉及中國山水畫的多種皴法,亦有古人不曾表現過的山石勢形態。這就必須對山形、石態進行歸納和總結,并根據客觀感受在筆墨中來表現。

2.金鑫 珠穆朗瑪峰寫生40cm×70cm 2016

3.金鑫 定日孜布日神山寫生40cm×70cm 2016
其次,以現實主義手法表現藏族聚居區風景寫生,務必要在具體客觀物象的寫生中對繪畫技法進行改造和創新。傳統中國畫山水體系中的濃淡干濕、大小虛實、遠近關系等原則同樣適用于藏族聚居區風景寫生。宗炳云:“且夫昆侖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于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宗炳總結的這種透視學原理可以在藏族聚居區寫生中靈活運用。例如對藏族聚居區風景中草地的處理手法,即可從近、中、遠三個層次將草地細細勾出,逐漸推遠淡化,亦可以用整體染色的方式進行大塊面處理,以表現草地在畫面中的整體性。另外對于雪山的表現,由于藏族聚居區的雪山大多都覆蓋在堅硬的塊面山壁上,也有大量的冰川與雪同在一個或幾個山脈中,中國古代山水畫中幾乎沒有此類雪山的表現方法,故必須區分雪山的層次與塊面,以淡墨勾染,亦可留出空白或以白色染之,才能體現出高原山石的堅韌。藏族聚居區云水景色也有別于內地,藏族聚居區地處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上,空氣稀薄,天空中云朵較低,形成獨特的景象。而內地名山大川中因天氣原因常會出現云霧,但這種云霧與藏族聚居區的云區別很大,這就要求畫家在畫面中對云霧的表現務必遵循客觀現實,在筆墨線條中應盡量表現云的沉著和厚重感。另外則是水的表現,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既是黃河、長江、雅魯藏布江的發源地,也是佛教四大河流的發源地。這里的水有平鏡的湖泊,亦有湍急的江水,且色彩豐富,故在畫面中表現方式要活,但不能呆板。

4.金鑫 甘孜寫生45cm×70cm 2015
最后,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靠單純的水墨線條不足以表達,藏族聚居區是一塊很吸引人的地域,因其人和自然的關系,包含著最初的一種珍貴的原始景色,在形象上保存了很多原始的、優美的東西。中國山水畫歷來以墨色表現為主,墨色如果適中,則不須著色,如畫面層次不夠深入,則以色補充。而在藏族聚居區風景中,呈現在畫面中更多的是神秘的色彩。這些色彩既有山體、樹木、草地、湖泊的顏色,也包含寺廟、房屋、人物、經幡的顏色,在藏族聚居區寫生作品中要合理地表現畫面效果,就必須通過一定的染色來制造意境或抒發畫家的情感。但染色的前提是尊重客觀自然,在繪畫過程中如果畫面的層次不夠,則可以用色彩來補充,且染不可平涂或反復積色,而是和“書寫”一樣,通過運筆速度、墨色的虛實來補充,使畫面中的藏族聚居區景色增添幾分高雅和空靈之氣。
綜上所述,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自古以來沒有成熟的理論體系與寫生技法的總結。隨著國家的日益強盛,交通的便利可以為更多的繪畫工作者提供前往藏族聚居區的便利,畫家應不斷地去探索與創新,走出畫室,走進藏族聚居區,去發現和總結更多的有關藏族聚居區水墨風景寫生及創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為發揚藏族聚居區文化和美術做出更大的貢獻。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