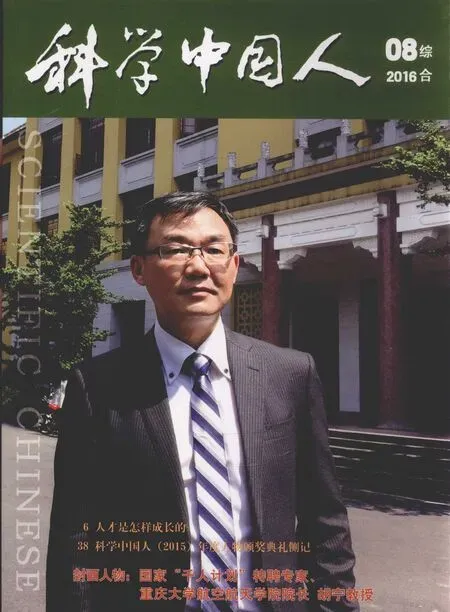跨越抽象數(shù)學(xué)到生物醫(yī)學(xué)的鴻溝
汲曉奇
從古代科學(xué)時(shí)期,人類直觀地認(rèn)識自然界,并將所獲得的知識包羅在統(tǒng)一的古代哲學(xué)之中;到近代科學(xué)時(shí)期,人類開始對自然界進(jìn)行系統(tǒng)地觀察、設(shè)計(jì)精確的實(shí)驗(yàn),并初步建立起嚴(yán)密的邏輯體系;再到現(xiàn)代科學(xué)時(shí)期,科學(xué)的發(fā)展把人為分解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重新整合起來。在這100多年時(shí)間里,始終勃興的交叉科學(xué)面對消除各學(xué)科之間的壁壘的挑戰(zhàn),有望填補(bǔ)它們之間邊緣地帶的空白。特別是從抽象的數(shù)學(xué)到實(shí)際的生物醫(yī)學(xué),需要跨越一道道鴻溝。
為實(shí)現(xiàn)這一跨越,眾多學(xué)者在生物信息學(xué)、系統(tǒng)生物學(xué)交叉研究這片廣袤的沃土上耕耘并收獲著創(chuàng)新性成果,而中國科學(xué)院數(shù)學(xué)與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院的研究員王勇是其中一員。一直以來,他致力于用手中的數(shù)學(xué)工具為看似遙遠(yuǎn)的抽象數(shù)學(xué)和實(shí)際的生物醫(yī)學(xué)“牽線搭橋”,將“天塹”變成通途。
在生物醫(yī)學(xué)的后花園“玩耍”
1995年,王勇作為國家首屆數(shù)理基地班的學(xué)生得以免試推薦到內(nèi)蒙古大學(xué)。一開始他身肩繁重的課業(yè)壓力,既要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又要學(xué)習(xí)物理。到大三專業(yè)分流時(shí),他最終選擇興趣更為濃厚的數(shù)學(xué),從此踏入數(shù)學(xué)研究的大門。之后,他又經(jīng)免試被推薦到大連理工大學(xué)攻讀碩士。一路走來,王勇刻苦拼搏,勇往直前。2005年,他從中國科學(xué)院數(shù)學(xué)與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院獲得運(yùn)籌學(xué)與控制論博士學(xué)位,博士論文研究內(nèi)容為基于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的蛋白質(zhì)結(jié)構(gòu)預(yù)測與分類研究。
對于攻讀博士階段轉(zhuǎn)向生物醫(yī)學(xué)研究,王勇給出了解釋:“生物醫(yī)學(xué)是一個龐雜的大學(xué)科,近年來在測序等新技術(shù)的推動下產(chǎn)生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需要在數(shù)學(xué)上找出產(chǎn)生數(shù)據(jù)的最佳的模型,揭示生物學(xué)家關(guān)心的因果關(guān)系;需要研究生物數(shù)據(jù)的基本數(shù)學(xué)結(jié)構(gòu),最優(yōu)的分離信號與噪聲;需要研究如何最優(yōu)地集成生物醫(yī)學(xué)數(shù)據(jù)。這些都離不開最優(yōu)化建模。”而他數(shù)學(xué)研究的背景,恰好就是“最優(yōu)化”。就像是一座橋梁,“最優(yōu)化”將數(shù)學(xué)與生物醫(yī)學(xué)連接起來,也將王勇和生物醫(yī)學(xué)的緣分連接了起來。
但“牽線搭橋”并不是那么容易,如何將其與最優(yōu)化進(jìn)行交叉研究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王勇漸漸摸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從一些前人已經(jīng)研究透徹、數(shù)學(xué)意義比較清楚的問題入手,采用計(jì)算的方法從數(shù)學(xué)角度來研究生物醫(yī)學(xué)問題,慢慢對生物的積累和理解就多了。”如今的王勇越來越了解生物醫(yī)學(xué)的研究方式,他可以站在生物學(xué)家的角度思考,提出一些他們所關(guān)心的問題,再尋找一些“有趣的數(shù)據(jù)”來進(jìn)行數(shù)值試驗(yàn)。對此,他戲稱自己“這是在生物醫(yī)學(xué)的后花園玩耍。”
2005年10月,王勇遠(yuǎn)赴日本從事系統(tǒng)生物學(xué)方面的研究。在日本,他第一次接觸到“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就是以基因?yàn)楣?jié)點(diǎn)、基因之間調(diào)控作用為邊建立的生物分子網(wǎng)絡(luò)。王勇強(qiáng)調(diào),這里的調(diào)控作用指的并不是兩段基因之間的物理相互聯(lián)系,而是一種間接通過mRNA、蛋白質(zhì)、代謝物或者非編碼RNA實(shí)現(xiàn)的調(diào)控作用。
每個細(xì)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調(diào)控系統(tǒng),用來保持體內(nèi)代謝過程的正常狀態(tài)、適應(yīng)多變的環(huán)境、防止生命活動中的有害后果、產(chǎn)生細(xì)胞周期特異性和外界信號的響應(yīng)特異性。因此,研究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應(yīng)用價(jià)值。它是系統(tǒng)生物學(xué)里的研究熱點(diǎn),一改傳統(tǒng)“集郵式”的研究方法,強(qiáng)調(diào)以網(wǎng)絡(luò)、相互作用、動態(tài)行為等整體論觀點(diǎn),并結(jié)合數(shù)據(jù)整合的觀點(diǎn)對復(fù)雜生命現(xiàn)象進(jìn)行理解和詮釋。
然而,如何推斷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成為擺在眾多研究者面前的難題。由于生物實(shí)驗(yàn)條件的限制,每個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集只能在相對很少的時(shí)間點(diǎn)上取得觀測數(shù)據(jù)(一般少于20點(diǎn)),相比之下基因數(shù)量是非常龐大的,比如模式生物酵母菌中有6000多基因,兩兩基因間可能的調(diào)控關(guān)系有3600萬,需要找出和數(shù)據(jù)最匹配的調(diào)控關(guān)系的集合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這種模型復(fù)雜性和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嚴(yán)重不足之間的矛盾,就是通常講的“維度災(zāi)難”。在希爾伯特提出著名的23個數(shù)學(xué)問題的整100年后,美國數(shù)學(xué)會召開了題為“21世紀(jì)的數(shù)學(xué)挑戰(zhàn)研討會”。會議上美國科學(xué)院院士、壓縮感知的提出者之一——Donoho教授發(fā)表了題為“高維數(shù)據(jù)分析中的維數(shù)災(zāi)難”的主題演講,特別指出,維數(shù)災(zāi)難是個核心的問題,在科學(xué)各領(lǐng)域中無處不在。王勇與合作者針對這個困難,提出了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重建的最優(yōu)化模型與算法,系列結(jié)果發(fā)表在生物信息學(xué)頂級雜志Bioinformatics上,目前被引用300多次。基于該方法,他們用計(jì)算方法重建了小鼠24小時(shí)節(jié)律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識別出一些新的重要基因,受到美國科學(xué)院院士、美國加州大學(xué)圣地亞哥分校Steve Key教授的高度評價(jià),生物領(lǐng)域頂尖綜述期刊Annu. Rev. Genet.的綜述認(rèn)為王勇等通過卓越的努力,成功地整合多樣和不完整的數(shù)據(jù)集,用數(shù)學(xué)建模彌補(bǔ)了數(shù)據(jù)的稀缺。
馳騁于廣闊原野
回憶起在國外的求學(xué)經(jīng)歷,王勇坦言,收獲很多,能在交叉研究領(lǐng)域一直堅(jiān)持下來,得益于很多好老師——博士生導(dǎo)師章祥蓀研究員、大阪產(chǎn)業(yè)大學(xué)陳洛南研究員、波士頓大學(xué)夏煜教授、斯坦福大學(xué)王永雄院士等。通過和這些老師合作,王勇在研究方法和方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和幫助。
訪問波士頓大學(xué)生物信息學(xué)中心和斯坦福大學(xué)Bio-X中心,給王勇最深的感受就是“國外做交叉學(xué)科的條條框框很少”,習(xí)慣于成立“program”,往往是跨院系、跨研究組、將興趣相投的一群優(yōu)秀人才聚集在一起開展自由探索研究。這樣相較于傳統(tǒng)學(xué)科的研究方式,他們擁有更廣闊的天地和更加自由的發(fā)揮空間。王勇喜歡把他們這些做交叉研究的學(xué)者比作“曠野上的牛仔”,他們的獵物就是有趣的課題。而他所要做的就是選擇合適的工具伺機(jī)展開獵捕。這或許就是交叉學(xué)科的魅力所在。
2017年,王勇提升為中科院數(shù)學(xué)與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院研究員,他的研究水平也更是上了一個階梯。他開始探尋更加前沿的全新領(lǐng)域。
半個世紀(jì)以來,基因調(diào)控的DNA編碼和轉(zhuǎn)錄因子編碼從物理、生化角度得到廣泛關(guān)注,但在基因調(diào)控與環(huán)境等外部因素交互等研究方面遇到了困難。因此,近年來位于中間層面的表觀編碼特別是染色質(zhì)開放、被修飾和甲基化狀態(tài)得到密切關(guān)注,并形成遺傳學(xué)中一個前沿領(lǐng)域:表觀遺傳學(xué),其重點(diǎn)研究基因的DNA序列在沒有發(fā)生改變的情況下,基因功能發(fā)生了可遺傳的變化,并最終導(dǎo)致表型的變化。有越來越多研究表明,染色體狀態(tài)從表觀遺傳學(xué)層面為基因調(diào)控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同時(shí)也開辟出新途徑。
針對基于染色質(zhì)狀態(tài)的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研究中高通量數(shù)據(jù)的快速積累問題,已有的單層次數(shù)據(jù)方法還存在很多局限。“這需要對來自染色體和轉(zhuǎn)錄組兩個層次數(shù)據(jù)的集成方法進(jìn)行深入研究,建立一系列可以應(yīng)用于這些數(shù)據(jù)分析、整合的,且有嚴(yán)格數(shù)學(xué)與信息學(xué)理論支持的模型與算法,并應(yīng)用到具體問題對生物機(jī)理進(jìn)行探索,”王勇道出了問題的關(guān)鍵。
以染色質(zhì)上基因的調(diào)控元件的開放狀態(tài)為核心,王勇梳理出了幾個核心問題,即染色質(zhì)調(diào)控元件開放狀態(tài)參與基因表達(dá)調(diào)控的機(jī)理;調(diào)控元件的上游調(diào)控因子是什么?受這些功能區(qū)域調(diào)控的下游基因是什么?如何集成調(diào)控元件上下游的定量信息揭示基因調(diào)控機(jī)理? 他與美國斯坦福大學(xué)王永雄教授、清華大學(xué)自動化系江瑞副教授開展合作,針對調(diào)控元件的開放狀態(tài)和基因表達(dá)相互作用機(jī)理和多層次數(shù)據(jù)特點(diǎn),構(gòu)建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來探索表觀遺傳與遺傳因素互作機(jī)理,極大地?cái)U(kuò)展了傳統(tǒng)基因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的概念。發(fā)表于《國家科學(xué)評論》的綜述文章“集成染色質(zhì)開放狀態(tài)和轉(zhuǎn)錄組數(shù)據(jù)的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建模”中,介紹了這一方面的最新進(jìn)展。他們合作開發(fā)的利用匹配的染色體開放狀態(tài)和轉(zhuǎn)錄組兩層次數(shù)據(jù)推斷調(diào)控網(wǎng)絡(luò)的研究工作近期發(fā)表在《美國科學(xué)院院刊》上。
最近,參與中科院先導(dǎo)專項(xiàng)研究“動物復(fù)雜性狀的進(jìn)化解析與調(diào)控”,讓王勇感到尤為興奮。各個研究所,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員被集中在一起,針對“進(jìn)化的基因型、表型的系統(tǒng)生物學(xué)eGPS”進(jìn)行研究。項(xiàng)目由昆明動物所牽頭,基因組所、上海生科院、遺傳發(fā)育所、北京動物所以及數(shù)學(xué)與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院共同參與,王勇參與的是模型和算法部分的課題。
展望未來,王勇表現(xiàn)得尤為專注和踏實(shí),他表示會按照興趣繼續(xù)探索下去。慶幸的是,中科院數(shù)學(xué)與系統(tǒng)科研學(xué)院為他提供了寬松的平臺,也給予他充分的時(shí)間來專注基礎(chǔ)研究,對此,王勇十分珍惜機(jī)會。未來,他期望以數(shù)學(xué)為器,在醫(yī)學(xué)的后花園種植出更多的豐碩果實(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