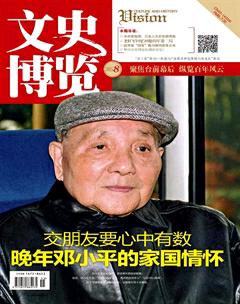從絲綢之路走到大唐的外商
李曉巧
盛唐時(shí)期,京城長(zhǎng)安人口上百萬(wàn),而同時(shí)代的東羅馬帝國(guó)的君士坦丁堡雖號(hào)稱繁華,但人口卻只有80萬(wàn),長(zhǎng)安作為當(dāng)時(shí)國(guó)際大都市的地位無(wú)可動(dòng)搖。《唐六典》記載唐王朝曾與300多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有交往,而從陸上絲綢之路到大唐的商人占了很大比率,“唐興,(西域諸國(guó))以次修貢,蓋百余,皆冒萬(wàn)里而至”。
來(lái)自絲綢之路的商人在長(zhǎng)安開(kāi)了很多商鋪,從中亞運(yùn)來(lái)的金銀器具和玉石制作的器皿成了宮廷和朝廷貴族的喜愛(ài)之物,他們不惜花大價(jià)錢購(gòu)買,上行下效,乃至于民間富人也對(duì)西域貨很熱衷。市場(chǎng)一大,更加刺激了西域商人到富庶的大唐來(lái)賺取高額利潤(rùn)的熱情。
在唐代鼎盛的開(kāi)元年間,在長(zhǎng)安定居的外國(guó)人(實(shí)際上多數(shù)是商人)有突厥人、回鶻人、吐火羅人、粟特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此外流動(dòng)外商更是無(wú)法統(tǒng)計(jì)。當(dāng)時(shí)政府為了有效管理這些外商,專設(shè)了一個(gè)政府機(jī)構(gòu)叫做“薩寶府”,其字面意思是“商隊(duì)首領(lǐng)”,系外來(lái)語(yǔ)的英譯。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長(zhǎng)安的外商之多。
唐朝大詩(shī)人李白有首描寫(xiě)當(dāng)時(shí)長(zhǎng)安市面的詩(shī):“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fēng)。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這位富二代先是逛了奢侈品市場(chǎng),逛膩了后,又去了有異國(guó)情調(diào)的胡姬酒店喝酒劃拳、尋歡取樂(lè),這兩處在當(dāng)時(shí)長(zhǎng)安都是外商做生意的地方,是富貴公子必去的銷金窟。
眾多史料顯示,在大唐諸多西域外商中,波斯商人的影響力不小,長(zhǎng)安城開(kāi)有波斯邸、波斯酒店、波斯金店等,波斯商人也遍布長(zhǎng)安、洛陽(yáng)、廣州、揚(yáng)州等地。
而且波斯商人與華夏民族也有了融合,他們長(zhǎng)期定居唐帝國(guó),甚至娶了中國(guó)妻子。最著名的如晚唐詩(shī)人李珣和他的妹妹李舜弦就是販賣香藥的波斯商人的后代。
其實(shí),從絲綢之路走向大唐的外商中,粟特商人的勢(shì)力也是相當(dāng)之強(qiáng)。
“從公元前2世紀(jì)到唐朝末期(公元10世紀(jì)),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貿(mào)易中占支配地位。”“他們的家鄉(xiāng)馬拉坎達(dá),即現(xiàn)在的撒馬爾罕(今屬烏茲別克斯坦),位于絲綢之路的西北方。中國(guó)人因張騫去西域探險(xiǎn)而知道了粟特人(索格底亞那人)”。
公元前327年,粟特人被亞歷山大的軍隊(duì)攻打之后,從此軍事力量再也沒(méi)有得到恢復(fù),但是,他們很快以商人的身份在中亞聞名遐邇,活躍于絲綢之路,并且走向了繁盛的大唐。我國(guó)古代和田人稱呼這些粟特商人為“蘇利”,久而久之,他們把所有的商人都稱為“蘇利”,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粟特商人的影響之大和程度之深。
粟特人的長(zhǎng)相是“瘦長(zhǎng)臉、高鼻梁、深眼窩和長(zhǎng)著濃密胡須”。唐朝僧人玄奘在公元7世紀(jì)到達(dá)粟特人的都城馬拉坎達(dá)時(shí),發(fā)現(xiàn)他們居住得十分狹窄,但是市場(chǎng)上的商品琳瑯滿目,“異方寶貨,多聚此國(guó)”。粟特人的小孩在5歲起就讀書(shū)寫(xiě)字學(xué)做生意,到了12歲就被送到鄰近的國(guó)家做生意。據(jù)說(shuō),葡萄和苜蓿就是粟特人輸入到中國(guó)的,他們還將西方的奢侈品如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器和玻璃器皿、波羅的海地區(qū)的琥珀、地中海的珊瑚、羅馬的紫色羊毛布等運(yùn)進(jìn)中國(guó)銷售,再將中國(guó)的絲綢運(yùn)銷至中亞地區(qū),乃至于羅馬,粟特商人還以善于鑒寶著稱,他們還仿制中國(guó)銅錢,使用中國(guó)紙張。
在7世紀(jì)時(shí),有很多粟特商人在中國(guó)經(jīng)商,并且取了中國(guó)名字,據(jù)說(shuō)當(dāng)時(shí)的很多粟特人改姓“安”。8世紀(jì)中期,粟特人在我國(guó)敦煌附近站穩(wěn)了腳跟,因其擅長(zhǎng)做生意而積聚了大量財(cái)富,成為當(dāng)?shù)睾苡杏绊懥Φ娜后w。
唐代的涼州和洛陽(yáng),有粟特人建的瑣羅亞斯德教寺廟。在敦煌佛寺藏經(jīng)洞和吐魯番的摩尼教經(jīng)書(shū)中就有粟特語(yǔ)的,據(jù)考證,大部分成書(shū)的時(shí)間大概在公元8世紀(jì)或9世紀(jì)的唐朝。
還有西方史料考證,唐玄宗的楊貴妃不僅青睞中亞地區(qū)的時(shí)尚,而且還鐘情于中亞地區(qū)的男子,其證據(jù)之一,就是她對(duì)肥碩的安祿山的垂青。安祿山體重300多斤,比她這位歷史上有名的“環(huán)肥”美人不知要肥到哪里去了。或許是“惺惺相惜”,或許真是楊美女為安祿山身上的粗獷風(fēng)格著迷,總之,兩人茍且之“好”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并且還左右了歷史的走向。而這個(gè)安祿山就是絲綢之路上有名的粟特商人的后代。
據(jù)《新唐書(shū)》介紹:“安祿山,營(yíng)州柳城胡也,本姓康。”而西域之人姓康的,幾乎都是來(lái)自當(dāng)時(shí)西域“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是中國(guó)南北朝、隋、唐時(shí)期對(duì)從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操中古東伊朗語(yǔ)的古老民族人來(lái)到中原或其后裔10多個(gè)小國(guó)的泛稱。他們善商賈,和中國(guó)通商很早,唐代在中國(guó)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國(guó)人、石國(guó)人為主。
史書(shū)還明確記載,康國(guó)粟特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guó),利所在無(wú)不至”。
據(jù)《新唐書(shū)》記載,安祿山的媽媽阿史德,在絲綢之路沿線商路上以行巫術(shù)為職業(yè),接觸的來(lái)往商人當(dāng)不可計(jì)數(shù),她也弄不清到底是跟哪一位匆匆過(guò)客構(gòu)造了個(gè)孩子(或者是她弄不清,或者是她不想公布孩子他爹的真名實(shí)姓),于是就自己編了個(gè)神話,說(shuō)是她祈禱“軋犖山”感動(dòng)了山神,讓她懷孕了,這個(gè)孩子后來(lái)輾轉(zhuǎn)改名為“安祿山”。安祿山在歷史上雖然算是位武人,但他身上的商業(yè)色彩卻很濃:首先,他的祖先是真心喜歡并善于經(jīng)商的粟特人;其次,從其出生地來(lái)看,他的“隱形爸爸”是商人身份的可能性很大;再者,安祿山“通六蕃語(yǔ)”,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互市郎”——外商與唐朝人做生意的中間介紹人,實(shí)際上也可算是商人;更重要的是,安祿山的“做大做強(qiáng)”,得到過(guò)“外商”朋友們的鼎立支持和巨額資金,史上說(shuō)“(安祿山)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cái)百萬(wàn)”。可見(jiàn),歷史上的安祿山與西域胡商關(guān)系密切。
總之,唐朝時(shí)粟特商人、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等西域外商來(lái)華做生意,為自身賺取財(cái)富的同時(shí),也將中國(guó)的絲綢、陶瓷、茶葉等特產(chǎn)購(gòu)銷到了中亞,以至更遠(yuǎn)的歐洲,對(duì)唐朝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shí)也促進(jìn)了中亞文化和唐朝文化的交流。并且,在“開(kāi)元盛世,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zhèn),出北道者納賦輪臺(tái)”——唐朝政府在絲綢之路上收商業(yè)稅作為駐軍的軍費(fèi),以此鞏固邊防。
從陸上絲綢之路走來(lái)的西域“外商”在民間也赫赫有名,如《太平廣記》等唐人小說(shuō)中也多有體現(xiàn),歷來(lái)為世人所津津樂(l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