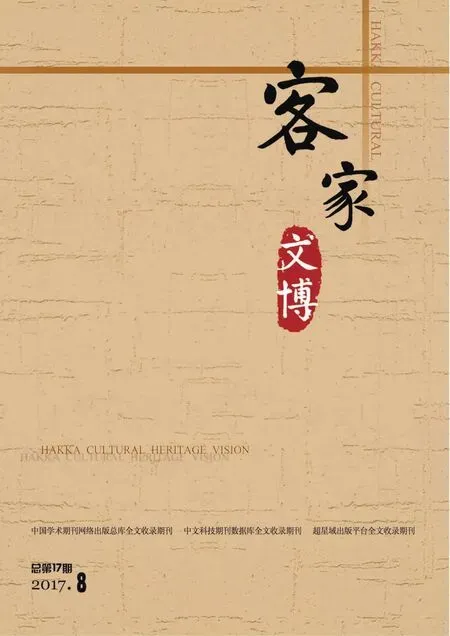雷州窯與長沙窯、吉州窯、磁州窯陶瓷的比較研究
田蔚恩
雷州窯與長沙窯、吉州窯、磁州窯陶瓷的比較研究
田蔚恩
本文以館內所藏的雷州窯和長沙窯、吉州窯、磁州窯藏品為研究對象,從最直觀的器物的裝飾工藝著手比較異同,進而探究其各自形成背景的異同,再探討其各自的流通方向,盡可能全面對比這些褐彩瓷的共同點和不同點,繼而挖掘南北褐彩窯址之間的影響關系。
雷州窯 長沙窯 吉州窯 磁州窯 比較
廣東雷州窯制燒于宋元時期,多為釉下褐、赭色彩繪瓷,其范圍大,窯址多,有公益圩、調乃家、舊洋、符宅等10余處古窯址1。雷州窯釉下褐彩清新秀麗,常用詩詞雅句、吉祥話語做裝飾,獨創一格,遠銷海外。
唐宋元時期,在以釉為美的主流審美之下,長沙窯、磁州窯、吉州窯、雷州窯在瓷器上以褐彩裝飾,別具一格,自成一派。唐代,長沙窯首創釉下褐彩,對宋代廣東興起的雷州窯的影響很大,探究雷州窯和長沙窯的關系,有利于了解雷州窯的起源。雷州窯、吉州窯和磁州窯,三者同一時期興起,其相似的器型,相似的裝飾風格,使得在六七十年代雷州窯產品曾一度被認為是吉州窯或磁州窯產品。因而,對雷州窯、磁州窯、吉州窯三者進行較為細致的比較研究,找出不同點,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區分三者。找出相似點,有利于更深程度地研究三個窯址之間的相互關系。
一、雷州窯
1957年,一件青釉褐彩鳳鳥紋荷葉蓋罐(圖1)出土于海康縣(今雷州市)西湖墓葬。蓋罐高31厘米,罐口9.8厘米,底徑13.4厘米。蓋沿呈荷葉波浪形,半圓形蓋鈕,釉下褐彩繪弦紋、蓮瓣紋。罐直口、豐肩、餅足,釉下褐彩繪纏枝菊花紋等。肩部繪纏枝菊花紋,鳳凰、喜鵲穿插其間。腹部四個菱花形開光,內繪折枝菊花,繪以錢幣紋為界,下接一圈卷草紋。近足部四個橢圓形小開光,內繪折枝花卉。蓋罐釉色清亮,褐彩發色清晰,彩繪線條優美,紋飾豐富,別具特色,與磁州窯和吉州窯相似,也有些不同,引人注目。隨后,類似的釉下褐彩常見于墓葬發掘中,常被認為屬于磁州窯系。

圖1 青釉褐彩鳳鳥紋荷葉蓋罐
1986年10月,雷州紀家鎮公益墟,清理出一座龍窯,殘長18.7米,并在附近發現深約3.36米的窯址廢棄陶瓷片堆積2。其中,出土的瓷器與雷州市宋元時期墓葬所出的同類瓷器十分相似,多以釉下褐彩繪裝飾,線條流暢而柔美。器身多見卷草紋、菊花紋、蓮瓣紋、錢幣紋等,并題有吉祥語。從龍窯發現的窯具可知其所出的瓷器是用匣缽疊燒而成的。對比胎質和燒造痕跡,雷州宋元時期墓葬所出瓷器亦采用同樣的燒造工藝。通過這些幾近相同的特征推測,公益墟龍窯出土的瓷器與墓葬出土的瓷器應為同一時期,并屬于相同的窯系,證實這種釉下褐彩瓷器為本土窯系所燒,而并不是之前誤認為的磁州窯或是吉州窯。
雷州窯,以窯址所在地命名,此處的雷州指廣義范圍上的雷州,涵蓋整個雷州半島,包括雷州市、廉江市、徐聞縣、遂溪縣和湛江市部分地區。由于雷州窯并不像其他大型窯系一樣常見于古籍文獻記載,關于雷州窯的研究資料大部分來自于考古發掘。
目前,就考古發掘情況而言3,最早的窯址年代為唐貞觀時期,發現于茂膽村和余下村,窯址均為龍窯形制,周圍發現瓷器施青黃釉,多為碗、豆、盤、罐等日用器,形式較為簡單。中唐時期雷州窯,除青黃釉瓷外,還燒制大量褐釉罐,胎質厚重。晚唐時期,雷州窯瓷器燒制工藝相對比較粗糙。唐代的雷州窯器形簡單,不具備獨特的燒制工藝、裝飾特色等,瓷器的質量總體不高。且所發現的唐代窯址較少,分布較為分散。因此,唐代時期的雷州窯還處于萌芽時期。
雷州窯最為顯著的青釉褐彩裝飾始于南宋早期,興盛于元代。1986年,發掘于雷州市紀家鎮的公益墟窯址,年代為宋至元,發現龍窯一座,出土有釉下褐彩裝飾的青瓷。宋代雷州窯器型開始多樣化,有碗、杯、碟、缽、盞、壺、瓶、罐、枕等,多為青釉瓷,但最具特色的是以釉下褐彩做裝飾。宋代雷州窯的青釉褐彩多見四系罐、瓷枕,還有一些釉下點褐彩碗,與磁州窯釉下褐彩瓷相似,多施青黃釉。褐彩紋飾不斷豐富,早期點彩、弦紋或是繪制纏枝花卉,后期常見開光內繪折枝花卉或題字,開光外飾纏枝花卉或以短直線相隔。但是,南宋雷州窯釉下褐彩的燒造技藝還有待提高,釉質稀薄易脫落,褐彩較為黯淡。元代,雷州窯釉下褐彩工藝成熟,制作更加精良,器形也有所創新。青釉明亮潤澤,褐彩艷麗醒目,紋飾精細繁縟,層次分明,開光裝飾更加多變。元代雷州窯荷葉蓋罐、雷州釉下褐彩瓷棺獨具特色,亦研燒出梅瓶、盆等器型。
元明之際,青花瓷以其明艷的色彩、細白的胎質,博得了更多的青睞,鮮艷多彩的釉上彩瓷也漸漸吸引陶瓷市場的注意,相較之下,色調單一的釉下褐彩則黯然失色。再加上,明朝政府禁止民間“通番”貿易,實行“海禁”,雷州半島海外貿易受到很大的限制,面向外銷的雷州窯釉下彩瓷逐步走向衰落。
二、同本異末的裝飾工藝
釉下褐彩,是以氧化鐵為呈色劑,在素胎上繪制圖案,外施淺色釉或透明釉,入窯高溫一次燒成。早在東晉時期,越窯的雞首壺上常見釉下點褐彩,但是這里的釉下褐彩還只是以點彩出現,沒有采用褐彩繪制圖形、圖案,裝飾意味并不強烈。直至唐長沙窯,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釉下褐彩裝飾,以氧化鐵、氧化銅為呈色劑,在素坯上繪出裝飾圖案,或是題寫文字、詩句,然后外施青釉經高溫燒制而成。長沙窯釉下褐彩,充滿古樸趣味的詩情畫意,別具匠心,引起眾多窯場紛紛效仿,釉下褐彩也逐漸在陶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磁州窯、吉州窯都是燒制釉下褐彩的著名窯口,各自具有鮮明的特征。
(一)雷州窯與長沙窯裝飾工藝比較
長沙窯興起于隋唐時期,繼承了岳州窯青瓷的燒造方法,又吸收了當時外來的文化因素,風格多變。長沙窯主要燒制青瓷,胎色灰白色、米黃色、青灰色,胎質疏松,還有少量瓦缸胎。由于胎質不大好,長沙窯的瓷器多施用化妝土。長沙窯瓷器釉色豐富,以青色偏黃釉為主,還有白釉、醬釉、綠釉、藍釉等。器形多是日常生活用具,而且種類齊全,其造型具有濃厚的民間生活氣息。除了常見的壺、瓶、杯、盤、碗之外,還有動物造型的勺子,小巧的油盒,儲放錢幣的撲滿等等。
由于時間的跨度,雷州窯與長沙窯相比,無論是器型,還是紋飾圖案都存在著不小的差別。但是,在釉下褐彩的燒制方面,裝飾工藝的手法上還是存著一定的聯系。

圖2 長沙窯青釉詩文執壺
在燒造工藝上,二者最大的共同點便是均采用龍窯燒制而成。從長沙窯的窯爐遺址可知,窯爐為依山而建的龍窯結構。而關于雷州窯窯爐結構,目前僅限于公益窯址和土塘窯址發表的考古報告4,可知雷州窯亦采用龍窯結構的窯爐燒制瓷器。公益窯和土塘窯的窯爐窯頭坡度較大窯尾平緩,說明窯爐設計已經考慮到窯頭坡度大易上火,窯尾坡度減緩以便存火保溫。窯址周圍發現的窯具,表明雷州窯以匣缽裝燒為主。這種匣缽裝燒方法,興盛于唐代的長沙窯已經采用了這種方法,常采用筒形匣缽裝燒。相比而言,雷州窯采用南朝末出現的直壁匣缽,直壁匣缽可以靈活結合多種窯具,充分利用空間,提高燒造效率。
長沙窯的裝飾手法多樣,釉下褐彩則是其最光彩奪目的裝飾手法。紋飾常見有幾何紋(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圓形等)、云帶紋、山峰紋之類,這種紋飾多點彩而成。也有些紋飾,類似中國寫意畫,繪畫各種飛鳥、游龍、走獸、魚紋、花卉、人物等。用筆簡練流暢,自然生動,頗有水墨畫的意味。在胚胎上書寫詩文、諺語等作為釉下彩裝飾圖案,書法藝術和陶瓷工藝的融合,擴寬了陶瓷裝飾藝術的空間。在褐彩裝飾上,雷州窯無疑受到長沙窯深遠的影響,褐彩繪花卉、飛鳥等,也題寫詩句、諺語做裝飾。區別在于,雷州窯的褐彩裝飾開光加邊飾,繁縟復雜,題寫的文字也多以諺語為主。而長沙窯則更為灑脫隨性,只以主體圖案為裝飾,文字則常見一些詩句,體現了唐代詩歌的興盛。圖2為長沙窯常見的青釉詩文執壺,執壺上,只以釉下褐彩題詩文為裝飾,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字體隨意灑脫,寫著“日日思前路,朝朝別主人。行行山水上,處處鳥啼新。”雖然對仗并不是十分工整,但是也頗有唐朝詩歌浪漫主義色彩。圖3是雷州窯的褐彩四系罐,滿飾褐彩紋飾,文字題寫在腹部的兩個開光內,開光兩兩相對,其中兩個開光內題寫著“桃花”和“洞里”。“桃花洞里”意指世外桃源,典故出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5。這件雷州窯褐彩四系罐,字體隨性灑脫,仿若身在世外桃源般愜意,充滿濃厚的民俗意味。

圖3 雷州窯“桃花洞里”四系罐
(二)雷州窯與磁州窯裝飾工藝比較
磁州窯,“出土古邯鄲地磁州”“好者同定窯相似,但無淚痕”6。自明代曹明仲的《格古要論》起,就有關于磁州窯的記載。磁州窯為北宋年間興起的北方窯系。馮先銘先生基于磁州窯考古資料的論證,從磁州窯瓷器同層發掘的錢幣等,推理出磁州窯燒造的年代范圍7。磁州窯歷經南宋、遼、金、元、明、清,燒造歷史悠久。磁州窯器型注重實用與美觀相結合,雖多為日用器皿,但裝飾風格新穎多變, 創新出“白地刻劃”“鐵銹花”“珍珠地”“白地褐彩”“白剔花”“黑釉剔花”“芘紋刻劃”等裝飾方法。其中,磁州窯釉下褐彩,黑白對比強烈鮮明,將世俗所見作為裝飾題材,花鳥魚蟲、龍鳳鹿馬、市儈景物、童叟仕宦、詩歌詞賦、兒歌詞曲等無所不繪,具有濃郁的民間生活氣息。
雷州窯與磁州窯都以釉下褐彩裝飾為顯著的特征,都以民俗題材裝飾為主,因而早年間發掘的雷州窯瓷器常常被誤認為是磁州窯瓷器。但是,雷州窯和磁州窯,在燒造、器型、裝飾上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別。
磁州窯以當地原料“大青土”制成器胎,由于土質粗糙,遠不如同時期定窯、邢窯的白瓷細白。于是,磁州窯的工匠便在胎體上施白色的化妝土遮蓋瓷胎的不足。而雷州窯則是直接在胎體上繪以褐彩,并不使用化妝土。在燒造方法上雖然雷州窯和磁州窯都是采用匣缽燒造,雷州窯常使用筒形匣缽和直壁匣缽;而磁州窯使用筒形匣缽和缽形匣缽,精細產品使用漏斗形匣缽單燒。并且,根據觀臺磁州窯的發掘報告8可知,磁州窯多采用馬蹄形饅頭窯構造的窯爐燒造,而雷州窯則是采用較為傳統的龍窯構造的窯爐燒造。
磁州窯的器型品種較為豐富,涉及到日常生活多方面的用品,而根據目前出土的雷州窯器型較為簡單,多見罐、瓷枕等。磁州窯將裝飾手法與器型相結合創新,如常使用嬰戲題材與瓷枕結合成“孩兒枕”。圖4便為磁州窯典型的“孩兒枕”,孩童手持荷葉憨態可掬,以躺臥的孩童造型為瓷枕的底座,孩童手持的荷葉為枕面,極具生活氣息。磁州窯亦常常以走獸為飾,圖5將瓷枕塑造為猛虎形象,虎紋筆觸豪放有力,猛虎栩栩如生。雷州窯常使用花草、人物紋飾,并且人物極具南越少數民族特色,人物的發式、服飾與漢族人大為不同。圖6為一對雷州窯褐彩人物鳳鳥紋梅瓶的局部,梅瓶開光內描繪的人物形象與中原人物形象大相徑庭。其中一位男子面容粗獷,身穿交領長袍,赤足。女子雖也是挽髻,但皆挽雙髻。其中一位女子還赤足,與中原女子的矜持不同。這對雷州釉下褐彩罐上描繪的人物,無論是服裝和發式,都反映了當地俚族的習俗,椎髻跣足,鄉土氣息濃郁。

圖4 磁州窯孩兒持鏈瓷枕

圖5 磁州窯虎形枕

圖6 雷州窯褐彩人物鳳鳥紋梅瓶局部
(三)雷州窯與吉州窯裝飾工藝比較
宋元時期的著名民窯,北有磁州窯,南方便以吉州窯最富盛名。《景德鎮陶錄》給予吉州窯極高的評價:“江西窯器,唐在洪州,宋時出吉州”9。吉州窯位于江西吉安市永和鎮,又稱永和窯,始于晚唐,盛于宋,終于元。常見器物有碗、盤、碟、缽、瓶、壺、杯、高足杯、鼎爐、罐、器蓋和玩具等。吉州窯雖以黑釉瓷最為著名,但釉下褐彩瓷也別具風彩。吉州窯釉下褐彩,筆觸秀美,精粗并存,裝飾題材豐富。荷間鴛鴦、鯉魚戲水、瑞鳳祥鹿、峽蝶、蜜蜂等喜慶吉祥圖案,日常生活中習見的蘆雁、月梅、竹枝、石榴、山茶、波濤等景物,都是吉州窯彩繪的內容;再以錦紋、回紋、八卦、如意云紋、纏枝卷草等紋飾組合。
吉州窯的燒制與雷州窯有很多相似點。兩者都采用龍窯結構的窯爐燒造。在窯具使用上,吉州窯也采用匣缽裝燒法燒造瓷器。在褐彩的繪制上,吉州窯同雷州窯一樣,直接在胎體上繪褐彩,并不使用化妝土。吉州窯褐彩的顏料采集于褐色赭石,經過反復擂碾,加工成細膩的顏料。因而,褐彩的發色為醬褐色或紅褐色,色彩更加鮮艷明快。
吉州窯以植物花草、飛禽走獸為主,再輔以回紋、如意云紋、纏枝卷草紋,與雷州窯不同的是人物紋極少。吉州窯和雷州窯都常見花卉,但還是有些細微的不同。吉州窯的花卉常見富貴牡丹、梅蘭竹菊,描繪細膩,頗具文人畫韻味;而雷州窯的花卉描繪比較寫意,常見菊花紋。如菊花紋雖然都見于雷州窯和吉州窯瓷器上,但是吉州窯并不是特別常用;菊花紋的描繪上,雷州窯菊花的花頭俱有圓形及扁圓形,而吉州窯只見圓形花頭。再如蓮花紋,吉州窯的蓮花紋較為精細并且還搭配其它圖案,常見折枝荷花紋、一把蓮、纏枝蓮花紋及蓮池鴛鴦紋(圖7)等形式,而雷州窯則只見單獨蓮花紋(圖8)。在邊飾方面,雷州窯最常見的錢幣紋,反而很少見于吉州窯。

圖7 吉州窯褐彩蓮池鴛鴦瓶

圖8 雷州窯釉下褐彩荷花紋如意形枕
三、南北窯系的成因比較
長沙窯、磁州窯、吉州窯、雷州窯瓷器的不同,究其根源在于窯系成因的差別。自然地理、社會經濟、人文風俗等的差別造就了這些窯系的差別,而這些窯系差別中有亦有著關聯,相互之間的聯系,昭示著釉下褐彩的流傳的過程。
興起時間最早的長沙窯,對之后的磁州窯、吉州窯、雷州窯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自然地理條件,長沙窯窯址位于長沙市望城區銅官鎮至石諸湖一帶,北端依山臨江,南端沿江面湖,且靠近原料產地。周世榮先生曾在《淺談長沙窯釉下彩瓷科技鑒定》中談到,“長沙窯陶瓷器的胎色主要呈灰白色和青灰色,陶瓷原料主要來源于當地的瓦渣坪和藍岸嘴”。10再者,社會背景方面,安史之亂后,北方絲綢之路受阻,而南方海上陶瓷之路則逐步興旺發達。長沙窯的瓷器在海運未通前,主要靠陸路,沿絲綢之路,由西安經新疆、中亞、西亞至波斯等地。廣州至波斯灣航線開通以后,長沙窯則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銷往國外。長沙窯的出海線路主要分兩支:東線從湘江、洞庭湖、長江到揚州或者寧波等地出港,銷往東亞地區的朝鮮半島及日本群島;南線、西線從揚州、寧波出海,經轉廣州,或直接從廣州出海,銷往東南亞、南亞、西亞及非洲諸國。2000 年,在印度尼西亞海域打撈出沉船“黑石號”,發現大量長沙窯唐代瓷器,證實了長沙窯外銷的出海路線長沙窯為適應海外陶瓷貿易的需要,在岳州窯制瓷基礎上,吸取北方模印貼花和多彩工藝的特點,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釉下彩瓷。最后,唐代興起的詩歌和書法,啟發了長沙窯的大膽創新,將書法、詩歌與釉下彩裝飾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長沙窯最奪目的一點。
(一)窯系差異成因
磁州窯、吉州窯和雷州窯窯場所在地天南地北,所處的文化氛圍相差甚大,所以其釉下彩繪瓷器多少都帶有各自的風格,表現不出同的形態特征。三個窯址所受的不同的人文風俗是造成三個窯場瓷器不同的最大因素。兩宋時期,磁州窯窯場的所在地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游牧文化對當時北方地區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受北方游牧民族粗獷豪邁性格的影響,磁州窯釉下彩瓷也呈現出瀟灑豪放面貌,常飾以走獸飛禽紋樣。唐以后的古吉州地區文化氛圍非常活躍,形成了以歐陽修、周必大、楊萬里歷史文化名人構成的廬陵文化11。吉州窯所在地區文化氛圍如此濃厚,消費者的欣賞水平較高,促使制瓷工匠不斷提高藝術修養,進而提高吉州窯的藝術水平,無論是造型還是裝飾相對高雅,具有濃郁的文化氣息。器物上多繪制宋代文人士大夫所喜愛的圖案,如梅花(圖9)、萱草等紋飾,并偶有題詩,整個瓷器頗具詩情畫意。雷州窯所在的雷州地區漢、越和俚族雜處,漢文化、越文化與土著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相互交融,形成了獨特的雷州文化。雷州窯釉下彩繪紋飾中的人物椎髻跣足,是當地赤腳俚族的生活寫照,充分反映了當時雷州的風俗習慣。

圖9 吉州窯黑釉剔花膽瓶
(二)窯系聯系成因
磁州窯、吉州窯和雷州窯都興起于宋代。磁州窯和雷州窯的年代比較接近,而雷州窯最晚。三個窯系的瓷器在器形與裝飾題材具有的共同點比較多,源于三個窯址的形成原因的諸多共同點,及其互相影響因素。
在自然地理方面,雖然三個窯址地理位置不同,但是都具備交通便利的地理優勢。瓷器作為大宗交易商品,本身具有易碎、沉重、耐腐蝕、無時效性等特點,因而窯址位置交通的便利性尤為重要。磁州地處晉、冀、魯、豫四省交界處,漳、滏兩河流域,這兩條天然水道為磁州窯產品的外銷運輸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條件。磁州窯的瓷器可以漳河、滏陽河水系網絡到達沿海及內地的港口和碼頭,再通過這些轉運點分散到內地和出海運輸到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及非洲等地。吉州窯所在的永和鎮倚靠贛江,贛江當時貫穿中國南北水運的南段,是連接中原與嶺南沿海的要道。雷州窯所在的雷州半島,三面臨海,海岸線長,港灣多,沿北部出海來往南洋諸國,以瓷器貿易為對外貿易的大宗12。同時,雷州半島也緊密聯系內陸,東可達珠江口,西可達容州連接中原、荊按照內陸向沿海的路線,北方的瓷器南下必然途徑贛江,使得吉州窯的窯工們能接觸到不同的瓷器產品,包括磁州窯的釉下彩繪。之后,吉州窯釉下彩繪瓷器通過贛江,運送到廣州地區,進而影響了雷州窯。
在社會經濟方面,促使三個窯場發展的顯著原因,莫過于陶瓷外貿的繁榮。宋代,政府為了規范對外貿易,在重要港口設立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先后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等處設立了“市舶司”,并專門派內使到海外招徠貢市貿易。《宋史·食貨下七·香》:“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泄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瓷、漆之屬博易”。這項“博易”政策擴大了陶瓷外貿的市場,也使得三個窯場的瓷器匯集在沿海港口,銷往海外。
工匠是瓷器的創造者,對于窯場瓷器的工藝風格影響無可比擬。兩宋時期,人口遷徙對三個窯場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將三個窯場聯系到了一起。從北宋中期開始一直到南宋滅亡,北方動蕩不已,造成了大批北方人口南遷,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瓷匠,客觀上促成了制瓷技術的傳播和交流,促進了南方吉州窯和其他瓷窯的發展。雷州地區自唐末五代起,外來移民逐漸增多。據吳松弟統計,宋代自元豐元年到至元二十七年的212年間,位于廣西路南部的雷州的戶數增長了550%。14再加上,雷州自古以來都為朝廷官員流放之地,流放的臣子、文士及遷徙過來的百姓給雷州帶來了制瓷技術。
四、結語
長沙窯開辟釉下褐彩裝飾的先河,在釉下褐彩的燒制、裝飾方式,都對后世興起的磁州窯、吉州窯、雷州窯影響深遠。磁州窯、吉州窯和雷州窯都興起于宋代。磁州窯和雷州窯的年代比較接近,而雷州窯最晚。三個窯系的瓷器在器形與裝飾題材具有的共同點比較多。而磁州窯、吉州窯和雷州窯窯場所在地天南地北,所處的文化氛圍相差甚大,所以其釉下彩繪瓷器多少都帶有各自的風格,表現不出同的形態特征。三個窯場所受的不同的人文風俗是造成其瓷器不同的最大因素。
本文從最直觀的器物的裝飾工藝比較異同,進而探究其各自形成背景的異同,再探討其各自的流通方向,盡可能全面對比這些褐彩瓷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但是,由于資料不足,相關的考證還不夠充分。尤其是在窯系產品流通方面,缺乏更多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證實。關于長沙窯、磁州窯、吉州窯、雷州窯的關系,有待更深一步地研究。
注釋:
1 馮先銘.中國古陶瓷圖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79.
2 湛江市博物館、雷州市文化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州窯瓷器[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18.
3 湛江市博物館、雷州市文化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州窯瓷器[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195-205.
4 楊少祥.海康縣公益村、土塘村宋元遺址[A].1987年中國考古學年鑒[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5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165-169.
6 【清】梁同書.古窯器考[A].中國陶瓷經典名著選讀[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190.
7 馮先銘.宋磁州窯宗論[J].人文雜志,1980(1):72-78.
8 秦大樹、馬忠理.河北省磁縣觀臺磁州窯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1990(4):1-22.
9 【清】藍浦.景德鎮陶錄[A].中國陶瓷經典名著選讀[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256.
10 周世榮.淺談長沙窯釉下彩瓷科技鑒定[A].The Methodology, Prospect and Significance on Nondestroyed Scientific Determination for Chinese Ancient Ceramics--Proceedings of CCAST (World Laboratory) Workshop[C].2002.
11 高立人.江西永和窯[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4.
12 阮應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湛江港口[J].湛江文史,第19輯;143.
13 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J].學術研究,1987(1):53-58.
14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566-568.
[1] 馮先銘.中國古陶瓷圖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 湛江市博物館、雷州市文化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州窯瓷器[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
[3] 高立人.江西永和窯[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4]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2017-6-5
田蔚恩,女,安徽阜陽人,任職于廣東省博物館,研究方向為文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