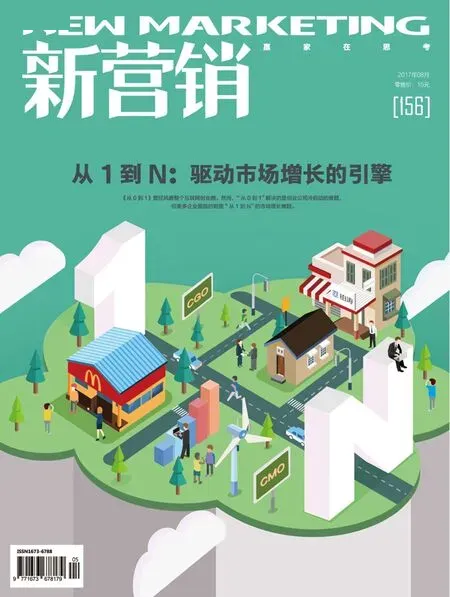營銷攻心術:存在感與安全感的博弈融合
■文/周再宇
營銷攻心術:存在感與安全感的博弈融合
■文/周再宇

《新營銷》雜志副主編,《藝術商業》雜志特約撰稿人,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碩士。曾采訪過阿迪達斯、寶潔、碧生源、嘉士伯、可口可樂、諾基亞、佳能、沃爾沃、奧迪等企業。
雖然,幾乎每十年就會出現一次針對年輕一代的研究風潮,比如80后獨生子女一代、90后網生一代、00后移動一代。每一代人在剛步入社會時都會被標上“叛逆”、“新奇”、“個性”等標簽。但事實上,每一代人都大同小異,說到底是年輕人的共性。
年輕人期待用特立獨行標注自己在這個世界里的坐標,肯定自己的存在感,但是一旦發生什么事,他們又是最快跑向群體,并通過群體一致性獲得安全感的社會性動物。
“我就這樣”與“我也這樣”
這種存在感與安全感的博弈,看起來矛盾卻真實存在的心理需求,卻正是營銷者可以利用之處。
當你對自身缺乏明確的認知,就只能依賴外物認知自己。這時,營銷者隨便拋給你任何東西,都可能被你當作浮木,用以塑造理想中的自我形象;當你的存在感依托于外界認同,你就會急于融入任何一個群體,以獲得安全感。
前者是“我就這樣”,后者是“我也這樣”;前者靠廣而告之塑造形象,建立人與物的聯系;后者靠意見領袖(KOL)聚攏相似人群、強化說服力,建立人與人的關系。前者更像是廣告的功能,后者更偏向于公關范疇。
廣而告之失靈,意見領袖崛起
在移動互聯網打破時空界限的今天,也許廣告與公關的界限已不再明顯。如今很多廣告公司拓展了公關業務,而很多公關公司也在發布社交內容廣告。
其背后的邏輯是:在最大范圍內“一對多”的傳播模式已經失靈,更多碎片化的意見領袖崛起,他們同時擔當廣告與公關的重任,并且以小眾化和垂直化的社群同時滿足人們獲得存在感與安全感的需求。
種子用戶與流量磁場
如今,意見領袖的價值不僅應用在傳播階段,更被引入到早期聚攏用戶的破冰過程中。
對于任何產品和服務來說,最初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從0到1”打開局面。找到早期用戶或消費者,并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讓早期用戶具有“流量磁場”的效應——他們對產品的使用,將加速新用戶的進入和轉化。
這類早期用戶被稱為種子用戶。
比如知乎,在內測期邀請的都是媒體大咖、業界大牛,這樣的種子用戶不僅為知乎品牌定下了基調,還可以吸引更多新人成為用戶,因為他們“也想成為這樣的人”。
為什么有些意見領袖轉化率高
去年,內容電商特別火,因為大號們也在尋找廣告之外的盈利模式,比如賣貨。在這方面羅振宇帶了個好頭,但是大家在跟進的過程中發現:不是所有人都叫羅振宇,不是所有大號都能成為羅輯思維。
人們對于意見領袖的追隨,有些是基于認同,有些則是基于消遣,而前者能帶來更高的轉化率。
那么,用戶更認同什么樣的意見領袖?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以前,人們更容易被權威性、專業性的意見領袖引導。如今,人們通過內容篩選符合自身價值觀和期待的意見領袖,同一個意見領袖的粉絲會形成一個特別的社群,所有用戶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歸屬感和安全感。
這種“我們很特別”的感受,避免了“我很特別”帶來的孤獨感,也避免了融入群體失去自我的恐懼。用戶正在圍繞一個個被認同的意見領袖,形成不同的小圈層。
個人期待與自我驅動之間的聯系
傳統的用戶畫像只能了解“TA是什么樣的人”,但是無法洞察“TA想成為什么樣的人”,而唯有后者,才能幫助營銷者預測TA下一步將如何行動。
在這方面,微博大號和微信大號的粉絲數據具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他們所關注的意見領袖代表著他們所向往的某種形象或生活方式。但問題是,以往對于大號的標簽和分類過于簡單粗暴,不足以為營銷提供精準有效的指引。從這個角度說,微博和微信大號簡直是懷抱寶山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