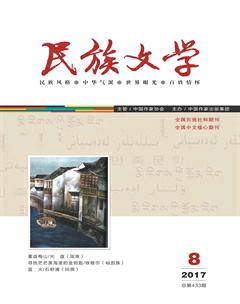遼沈走筆
凌春杰
5月4日,遼沈天空浸潤著一場毛毛細雨。此刻的大地,已然褪去厚重的雪衣,柳絮猶在輕盈飄飛。遼沈大地,吹著江南的軟風,滿眼盡是鵝黃翠綠。這樣慵懶的時光,適合獨自在庭院散步,或者在窗前駐足眺望,或者邀上好友煮茶論詩。卻有一個多民族作家代表團,直奔沈陽老工業基地而去。對于長期生活在南方的我,或許興奮中又格外滲入了一層好奇,即將真實步入的沈陽飛機廠、機床廠和鼓風機廠,一直是心中的一個沉睡的傳奇。更多的日常,我們陶醉于高樓與時尚、紛繁和美食,偶爾還陶醉于一些可有可無的雞湯,享受著衣食住行給予官感的所有舒適,就像一只溫水中的青蛙,漸漸遺忘了還有重工業這一龐大的身影。
我想,對于很多人而言,生活中輕工產品觸手可及,大至家電,小至從不離身的手機,我們時時刻刻浸身于輕工產品帶來的愜意,以至于常常熟視無睹,仿佛它們就是身體的某個部分,手,肌膚,舌頭,眼睛,或者是毛細血管中兀自流動的血,一直都與身體同在,極少認真地打量過。我在深圳,長時間耳濡目染的是新興產業,互聯網,海洋生物,生命科學,新能源……它們多半還沒有完成對傳統產業的轉型和替代,也不是今天經濟體中的中流砥柱,形成的成果要么如華大基因般的軟資產,要么像大疆這樣細小的無人機。當然它們的身影是俊逸的,綻放著光彩迷人和創新激情,天生就代表著科技和未來。這些新興產業的興起,讓我們奮斗,讓我們追逐,讓我們欣喜,讓我們向往,成為流行的日常話語。于是,我們常常就在豐富的輕工品和新興產業的隔離中迷離眩暈,以為生活只有這些物品和消遣,以為世界只有這些夢想和奮斗,只有在閑得百無聊賴時,才一本正經地談談詩和遠方。
在我生活的城市周圍,惠州,東莞,中山,佛山,珠海,這些城市擠滿了民營經濟群體,千千萬萬標注Made in China的產品,可能都是這些城市的手筆。在這些城市的廠房或樓宇,布滿了千奇百怪的輕工生產線,眾多青春的身影被打結在流水線,在傳輸帶的流轉中日日重復同一個動作。從這些車間,流出智能面板手機,光鮮亮麗的服裝,曲型面板的電視,冷暖變頻的空調,以及小小的電子管、薄如羽翼的貼片、細小如蚊的電動機……哦,似乎,一切人體感官的需求,這里都能轉化成為某個產品。這個世界,似乎就沒有什么東西他們不可以生產,直到讓生活被它們填得滿滿當當,也不曾停歇下來。這些形形色色的輕工品,在占領了一個時代后,成為引導世界物性化的潮流,主導世俗生活的基本范式。
當我走進遼沈大地,生活切換出新的頻道。眼前的大沈陽,承載過侵略者鐵蹄的肆意踐踏。風云際會的歷史,今天看似已然風輕云淡,卻深藏著某種成長的不懈沖動。現代工業文明,正是從這片大地萌芽,在苦難中緩緩洇出一條鐵路,長嘯著一路馳行到今天。也許,過長的冬天讓這片大地格外厚實舒軟,讓人對具有沉穩特質的鋼鐵情有獨鐘。金屬和鋼鐵,在他們眼里,不僅是鍛打,是鑄造,也是雕刻,是打磨,直到光滑如鏡,或者穩重拙樸。這里的工業品,并不以無堅不摧介入家庭生活或個體生命,而是以國營國有方式,對公共和重大葆有一份母性般的熱忱。它們是飛機,裝載車,智能機床,以及眾多重大裝備的零部件,等等。這些重工業產品,無一直接關涉到哪一個具體的人或家庭,卻又與每一個人的生活絲絲相連,成為生活的一個居于宏大敘事的背景。
我跨入沈陽數控機床集團的車間,那種大工業的厚重頓時震撼了我。我從沒有想象過機床有著如此恢弘的陣容,像秦皇氣象萬千的兵馬俑,橫著成排豎著成列,透著莊重肅穆。數百臺智能機床的開啟,組合成一部渾沉的奏鳴曲,我從喧囂中聽到了其間的沉穩和寧靜。在一臺數控銑床前,我透過玻璃觀察門,看到一把銑刀正高速運轉,半透明的降溫液如注沖洗。這張銑床,刀是固定的,臺床像泊在水面的船般浮動搖晃。而另一張銑床,刀正輕盈游走,銑床一直紋絲不動,金屬的屑末隨著降溫液流入回收渠。在過道展示臺,我端詳著剛剛銑出來的葉輪、軸承,如果不將它們裝備組合到一臺機器之上,也可以作為一個工藝擺件收藏。但是注定,它們將隱藏在某部機器的軀殼內,融為機器的五臟六腑,令世人忽略了它的存在。摩挲著這些剛剛銑出來的部件,我感到一種從未觸碰過的質感,仿佛握在手里的,是一列靜臥的高鐵之輪,是一架大飛機的引擎葉輪,那么精致,那么沉穩。這些近乎工藝品的金屬部件,兀自閃耀著迷人的光芒,有的銀白,有的金黃,精巧中透著神采,著實讓人好生歡喜。
我想起了小時候見過的一家農機廠。那家農機廠,主要生產農具,鋤頭,鐮刀,鐵壺、犁鏵,大都是鄉下農村日常要用的物什。我看到,鐵在那里以高溫加熱的方式,被人一步一步鍛打成型。那時令我有些驚訝的是鍛打時不像鐵匠鋪里需要鐵匠輪起八磅大錘,而是在一臺電動機和曲軸的牽引下,那個鐵錘一上一下地自動錘擊,金屬之音初而沉渾,繼而清脆,余音婉轉,復又混入沉渾。或者,這也該算得上一個簡單的機床了。幸而的是,農具粗糙一些并不影響田間耕作,哪怕長相各異也不要緊,照樣可以割草、松土,照樣可以燒水做飯。所幸的是,這些農具,一旦進入到千家萬戶,就漸漸有了靈魂,變得靈動而锃亮,成為農人的心肝寶貝。我記得家里曾有一張犁鏵,就是在那個農機廠買回來的,晚上收工時倒插在田中。第二天再去扶牛耕耘,那張犁鏵依然閃著月白的光華,一犁犁松開翻轉出濕潤的泥香。那時的這種小工業,往往要從這種農耕文明的轉換中得到呈現。現在,這個傳統似乎不那么涇渭分明了,傳統農業在弱化中,不得不向產業化轉型。眼前的這家機床廠,似乎也是從手工和電動開始,數十年之間,頓然成為智能制造的典范,飛月捉蛟莫不有著其身影,他們凝聚起浸透過的心血,使得人和物,格外飽滿,格外厚重,格外沉穩。
在一遍遍打量過一張藍線條看不懂的圖紙之后,我和一個穿藍衣的工人攀談。我想確認自己的猜想,整個車間里人,是不是都屬于高級技工,都是所謂的大國工匠吧?他卻沒有正面回答,告訴我說,師傅是工匠,帶著徒弟,一個師傅,帶三個徒弟。他就是師傅的徒弟。他正值守著兩張車床,師傅此時并不在現場,看來徒弟已經得道了。我想,眼前所看到的,或許依靠的是信息和電子所構成的機電力量,人在此時成為一種旁觀的存在,僅僅監測或陪伴機器的運轉,應付可能的意外。然而,這個徒弟馬上糾正了我。他說,師傅帶徒弟,首先帶的是手上的活兒,這些上到銑床的部件,大多是批量的工業品,而這個部件起初的設計和打造,就是師傅帶著徒弟借助各種車床一點一點打造的,直到完全符合要求后,才形成產業化的工藝數據流程。令我瞠目結舌的是,居然有老師傅手工制作的部件,比這些精密的數控車床做得還更加精確。對于飛機和潛艇而言,任何一個部件,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這個徒弟莊重地告訴我。我頓然感到,師傅是一個有著絕活的工匠,徒弟正在歲月的洗禮中,身上卻彌漫著一代工匠的精神,他們有著知識分子的底蘊,隨心掌控的數控智能機床,將最為沉重笨拙的金屬,精心鏤刻成鐵的藝術。在他們的內心,一定有著父本的執著,母性的寧靜,和近乎死心眼般的追求。看看,那些銑出來的大大小小的鐵花,已全然不顧金屬的沉穩,競相展現曲線之美,舞蹈著,扭轉著,飄逸著,相聚,復又循環為鋼鐵,只為那化為鐵花美的幸運。我確信,他們就是我們當代的新型工匠。
一行來到沈陽鼓風機集團。看著行程中的介紹,我一直不明白鼓風機究竟有何看頭。在我的印象中,鼓風機無非就是用在工地,用在煤礦的掘進巷,燒鍋爐的爐子旁。生活中有時會看到商家開業慶典,扎一個半圓的充氣門,旁邊也用一個小小的鼓風機,鼓動起一片喜慶之氣。鼓風機之小,其不起眼,實在只覺得有用處而無妙處。走進沈鼓大門,方知原來鼓風機也可另有一番天地,倘是僅僅將鼓風機只做到燒爐子慶典這個份上,那真也離淪為原始機械不會太遠了。讓中國裝備與世界同步,這是沈鼓車間極為顯眼的標語。偌大的液晶屏,使我對眼前的沈鼓有了大致印象,原來沈鼓已從鼓風機涵蓋到石油化工、煤化工、天然氣、空分、冶金、電力、環保、國防等領域,已從一個小小的鼓風機廠,成長為我國重大裝備的支柱型、戰略型領軍企業。一家老工業企業,在時間的嬗變中依然保持著充沛活力,將觸須延展到周邊的方方面面,其大,足可代表中國重裝工業;其新,可與世界同類產品媲美;其尖,擁有若干全球領先第一。行走在車間,我想也許是得“風”相助,從那片鼓風的葉輪旋轉開始,風所到之處,亦是對氣的壓縮,是對液的分離,眾機器的旋轉,是泵的搏動。鼓風,隨風的吹拂,張揚而至世界,又以離心壓縮,聚起風的力道,凝集新的能量。當我站在那臺乙烯離心壓縮機前,端詳靜臥其旁的多葉轉子,我仿佛聽到了風在遠方的獵獵作響,如同進軍的號角,那里面滿是振奮與激情,讓我也跟著蕩氣回腸。是呢,沉浸于這樣的大工業,在個性極度張揚的今天,除了這些堅守者,世間曾有幾人想到過他們?在這座車間,和我看到的機床車間一樣,都有著一群默默無聞的守護者和創造者,他們甘于生活的幕后,甚至與當下節奏已然有些遙遠,卻始終有著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格調,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遠方。他們聚起風的力量,撞擊著我的心靈,使我不愿聽從解說員程序化的講解和走馬觀花式的引導,我想多看看每一臺機器,伸手再摸摸它的溫冷,感受它們內心的激情,以致我在參觀中一再掉隊,一再獨行。
回到旅行車上,我沒有和同行者急于分享自己的見聞觀感,我想理理自己的思緒,想整理出它們的前世今生。瞑目回想中,思緒不由回放到首先走進的沈飛博覽園。這其實是一個沈飛集團的博物館,沈飛集團所有的殲擊機模型都陳列在這里。沈飛集團,正是中國殲擊機的搖籃,擔負著航天國防的使命。現今除了研發生產飛機,沈飛已形成了汽車、輕金屬結構、倉儲物流設備、大中型機械設備、機電產品、民機零部件等六大系列三百多種產品。走進這個博物園時,雨下得有些大了,淋濕了好些人的衣服,卻不能阻隔我們好奇的步伐。廳堂的那架殲擊機模型,腹部和機翼上都掛著導彈,以飛天之姿挺立在聚光燈下。我愿意與這架戰斗機模型合影,在我的心中,它不僅僅是一種戰略威懾,也是空天中矯健的精靈,在藍天中吟唱和平之歌,它的威嚴不語,正是我此刻的安寧。在一個透明的空氣動力模型裝置前,我對一股氣流如何營造加速推舉起數噸數十噸的重量有了一知半解,進而對飛機懸掛的引擎由衷地充滿敬意。在展館中,我貪婪地拍下各型飛機,教練機,殲擊機,而在那架真正的戰斗機上,我們逐一登入駕駛艙,揮手寄寓飛天的夢想。我拍攝下了很多留影者,他們收不住心底笑容,內心充滿自豪。也許,人類最初的夢想,就是像鳥兒一樣飛天了。當萊福兄弟首次橫空飛起來時,這個夢想就不再是樹與樹之間的距離,而是像一條無盡的射線,一直延展到浩渺的星空。今天,這些飛機還在防備著人類自己,我相信總有一天,世界可以放下更多的戒備,齊心向著浩瀚的太空進發。那時,它們越是飛得高遠,越是不發一槍一彈,越是意味著和平安寧。我突然意識到,這種大工業,并不像我們日常使用的手機、穿的衣服、吃的美食那樣與人熟絡,它本就天然地滲透在生命的血液,樸實到時常被人遺忘,卻始終與隱秘的夢想緊密相連。
作為一個工作在經濟領域的書寫者,有時我會選擇一個更大的背景,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視野來觀察世界。我在這里所看到的飛機、機床和裝備,它們極少進入到世俗的日常經驗,但卻仍有那么一批人,默默堅守在這份事業,追求著高,追求著精,追求著尖,比起我這個習慣了輕工產品的享用者,他們的堅守和秉持,成為我享用生活的巨大背景,讓我不由生出由衷的崇敬,使我從輕快中一再回首,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厚重底蘊,看到了實體經濟的希望之光。我想起了,我們作為一名文學的書寫者,這些年來卻少有抒寫這種大工業題材的作品,是不是我們也像一個世俗的生活者,漸漸在舒適中淡忘了重工業在一個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坐標,在虛擬經濟的高韜中模糊了實體經濟的基礎地位,在個體舒適中習慣了沉湎于個體精神世界的追問;我們是不是忘記了,這些基礎工業和他們的工匠,他們的夢想,他們的世界,他們的愛恨情仇?作為無用之用的文學,豈可毅然決絕地將目光轉向錦衣玉食,僅僅關注作者自己的功名利祿和個體生命的悲歡離合?
5月7日,我離開遼沈大地。但那里的厚重與堅守,像風像雨,始終浸潤在心里,閃現于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