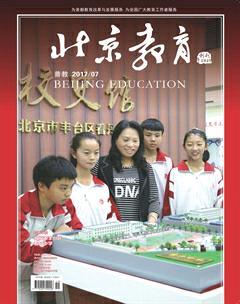唯有觸及生活方式的課改才能取得最終成功
朱傳世
自上世紀末開始,我們一直在搞課改,但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就是:改革的效果還沒有達到預期。國家的態度是明確的,省市區各級也不同程度地跟進了,問題就在學校和老師這個通道還沒打通。
為什么不通?板子還不能打在學校和老師那兒!
第一方面,學校和教師沒有得到課改紅利,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用兩個字表達就是“忙”“累”。第二方面,對學校和教師的評價體系沒有改變,教育行政部門評價學校仍然以考試成績為主,自然,學校評價教師也會以考試成績為主。這就必然帶來“學校之間圍繞成績的惡性競爭”和“教師之間教學成績的橫向比較”兩個“惡果”。同時,學校和教師要兩頭忙:一頭忙應試,一頭忙課改。第三方面,社會輿論評價也主要還是以考試成績論英雄。老百姓關注的切身利益是自己的孩子,如果老百姓不能實現“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希望,對學校的評價也好不到哪兒去。也就是說,從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角度看,學校和教師也不敢放松對成績的追求。
學校和教師的通道打不通,問題還在于學校和教師陷入了應試的怪圈,沒有時間、精力、能力研究出既能保證課改方向又能出好成績的辦法,而通過犧牲學生的休息時間以及重復機械的學習方式卻能得到高分,也就是說,不搞課改,學校和教師仍然不吃虧,也能拿到獎勵,因此能不改就不改了。
由此觀之,一場加重負擔的課改,一場沒有觸動評價的課改,一場不改還能得利的課改,很難吸引學校和教師,因此改革的動力嚴重不足。一言以蔽之,在基層,很多條道路不是通向改革的,而是不利于改革甚至是阻止改革的。而那些為數不多的取得較好改革效果的學校,主要是靠領導者的個人魅力、情感維系、有限的獎勵調整、局部體制機制改變等獲得成功的,這種成功很難復制,有的本身就很脆弱。
課改中不少學校的生活面貌照舊,教師的生活方式照舊,這樣的課改更多的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課改。有的老師聽完課改專家的講座后,會很不屑地遞上一句:“別聽專家瞎咧咧!”甚至有的老師有一種“專家恐懼癥”,認為“專家一進校,準沒好事了”。
歷史上有過無數的改革,其中不少改革都以失敗告終。為什么呢?改革沒有改善被改對象的生活方式!此次課改沒有如預期順利,原因也在于此。
首先,此次課改是以下放部分課程權力作為標志的,可很多學校和教師不知道自己手頭有沒有權,有哪些權,怎樣合理使用這些權力,這些權力能否帶來紅利,有哪些紅利。有些教師認為,權力是與責任對等的,權力就是“燙手的山芋”,要了是麻煩,還不如不要。這說明課改帶來的教師職業生活內容的變化在教師那兒不被確知。
其次,現今處在教育“深綜改”時期,要實現考試評價與課改的同步共振,但如何同步共振是很專業的事情,無論是培訓機構,還是教研系統,自身都沒有接受系統的培訓,更別說指導學校和教師了,因此出現了生硬對接的硬著陸案例,也不足為怪。
再次,課改導向的整體育人觀、學科融合觀要求教師在課程規劃、開發與實施中,調動學科前認知、跨學科前認知、生活前認知,而此前教師只是習慣調動學科前認知,如何調動后兩種前認知還無所適從。這說明課改帶來的教師職業生活方式的變化在教師那兒也不被確知。
此外,增加校外實踐課程的比例、改變教育教學時空格局等方面的變革,還沒有全方位地實施起來,教師仍然處在以教室為圓心、以學校為半徑的生活圈、工作圈、學習圈中,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單調乏味。教師角色中,“傳授者”的角色仍在主導地位,他們還沒有嘗到作為“組織者、指導者”的甜頭,更別說作為“課程規劃者、設計者、開發者”“課程環境布置者、課程文化的影響者”“學生學涯規劃師、學生生涯指導師”,體驗更富有意義和價值的生活了。
要打通學校和教師的渠道也并非不可能。長期固化的教師生活方式容易帶來職業倦怠感和單一刺激造成的壓迫感,改變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注入新鮮感,調整教師的心智模式,另一方面容易激發教師的創造潛能,引導他們感受教育創造的快樂。為此,教育行政層面一方面要通過自上而下的體制機制貫通式調整,讓改革者獲得紅利,讓不改革者接受輿論的監督;另一方面要組織力量,加強對教師新生活方式的指導,明確學校組織變革的重點和教師新的專業發展方向,并從考核評價、獎勵晉級、榜樣引領、定點幫扶等方面賦予新的專業發展以動能。
當學校的生活面貌和教師的生活方式真正變革后,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增強,學生的學習方式、生活方式、學習品質、生活品質也會隨之變化,這種變化如果被家長捕捉到,家長就會成為正向輿論的引導者。這是一種良性循環機制,而不是像以前,家庭教育否定學校教育,學校教育否定社會教育,最終把各自應付的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總而言之,課改的發動者和參與者都要從生活方式角度,俯下身去發現問題,找準對策,讓改革不忘末端,改在痛點,輕裝上陣,人人受益。
編輯 _ 付江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