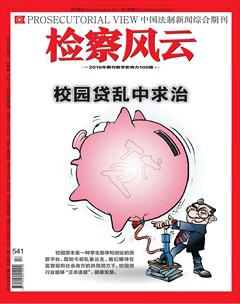建設法治國家需要提升全民“法商”
殷嘯虎
有些人為什么會“知法犯法”
從目前來看,知法犯法現(xiàn)象依然大量存在,法律還沒有真正成為大眾的信仰。可以說,絕大多數(shù)的違法者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是很清楚的,但為什么還要明知故犯呢?泰勒教授認為: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工具主義和規(guī)范主義兩種觀點。工具主義的觀點認為,人們在行動前,對自己遵守法律是否會受到直接的、明確的激勵,會受到什么樣的獎勵,或者對自己觸犯法律是否會受到直接的、明確的懲罰,他們會作出自己的估計,然后再據(jù)此決定自己應當如何行為——也就是說,對于各種不同的行為是可能給自己帶來收益,還是會給自己造成損失,他們會作出自己的判斷;規(guī)范主義的觀點則認為,人們之所以遵守法律,是以他們對當局的信任為基礎的。只有人們能夠信任當局,能夠信任當局制定的有關規(guī)則,能夠信任有關的執(zhí)法機構,他們才能相信自己忠誠于這個組織會給自己帶來長期的收益。
人們遵守法律是如此,同樣,人們違反法律也是如此。對違法行為而言,人們在選擇是否違法的時候,實際上同樣也是基于工具主義與規(guī)范主義的雙重選擇。就工具主義的角度而言,人們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會有一個價值估量:自己不遵守法律的行為受到懲罰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遵守法律與違反法律所獲得的收益哪個更大。如果不會受到懲罰的可能性很大,或者違法所帶來的收益要遠遠大于守法所帶來的收益,那他就有可能會選擇違法;反之則否。正是根據(jù)這種價值估量,來決定自己是否進行違法;就規(guī)范主義的角度而言,人們選擇不違法,是基于個人遵守規(guī)則的信念和對法律的信任,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因素。如果現(xiàn)實背離了人們的這種期望,大多數(shù)人有可能最終還是會選擇違法。
因此,我們在對如何才能有效地預防違法行為的發(fā)生進行考量時,就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些方面的因素。其實,從違法行為發(fā)生的階段而言,一開始往往只是少數(shù)人會選擇違法,大多數(shù)人可能會選擇觀望。如果這時候違法者立即受到制裁,大多數(shù)人必然會選擇守法;但如果違法者沒有受到制裁,大多數(shù)人就會跟著違法;當大多數(shù)人都選擇了違法、個別違法者卻因違法而受到制裁時,這個別違法者必然會對制裁不服,認為這是對他的不公正,因為其他違法者并沒有同樣也受到制裁,抗拒執(zhí)法的行為便由此發(fā)生;而當大多數(shù)人都在違法時,個別守法的人更會面臨痛苦的抉擇。
事實上,除了極個別的人以外,絕大多數(shù)的人在骨子里都知道不能違法。那些選擇了違法的人,固然有出于功利方面的選擇,但如果對違法行為不能及時公正執(zhí)法、嚴格執(zhí)法,客觀上可能會縱容違法行為的發(fā)生。有學者就曾指出: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國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國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國的法治出了問題,有法不依、違法不究,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善的法治國家。如果外國跟中國一樣,扔垃圾、吐痰、闖紅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估計比中國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敢,時間長了,就成了生活習慣。中國人之所以這么干,簡而言之,就是沒人管嘛!
所以,對于違法行為,在強調說服教育的同時,必須強化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只有通過規(guī)則的強制,才能形成執(zhí)法與自覺守法的良性互動,以嚴厲的處罰使人不敢違法,以嚴密的制度使人不能違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違法,以素質的提升使人不愿違法。
智商和情商替代不了法商
社會所面臨的一些法律困境,比如依法辦事、遵守秩序、崇尚規(guī)則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缺失等需要通過提高全民的“法商”來解決。按照一般的理解,法商(Law Quotient ,簡稱LQ)是一個人對法的內心體認和自覺踐行,體現(xiàn)的是人們法律素質的高低,法治意識的強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辦事、遵守秩序、崇尚規(guī)則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法商”的提出雖然已有十余年,但與情商和智商相比較,仍可謂是一個新詞。2006年9月到12月《檢察日報》推出“法商”新概念系列報道,使法商成為2006年的年度法治熱詞。2007年8月教育部在其官方網(wǎng)站發(fā)布了《2006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法商成為教育部認可的漢語新詞語。
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法商的認同度并不高,對提高全民的法商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習慣并沒有真正養(yǎng)成,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現(xiàn)象依然存在。雖然經過了30年的“六五普法”,公民的法律知識、法律意識有了普遍的提高,但公民的守法意識以及依法辦事的能力卻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下降了。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在于我們的“法商”并沒有真正得到提高。
一般來說,智商和情商的高低,個人先天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法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后天的學習和培養(yǎng)。有不少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不低,他們無論是在待人接物、為人處世還是協(xié)調關系、處理問題等方面都有很強的能力、很好的辦法,但結果卻在法律方面出了問題,犯了錯誤,原因就是忽視了法商的培養(yǎng)與提高,甚至以智商和情商替代了法商,認為只要智商和情商高就可以了,法商的提高不僅不利于事,還很有可能“誤事”。這從官場上流行的一些“段子”也可以看出: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wěn)定,低調就是腔調,大氣就是人氣,妥協(xié)就是和諧……這里面折射出的是人情和世故,缺少的是原則和法律。
因此,提升“法商”,首先表現(xiàn)為對法律的正確理解與認識,并通過這種對法律的正確理解與認識支配自我的行為。在此基礎上,形成健全的法制意識與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辦事、遵守秩序、崇尚規(guī)則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提升法商,僅有法律知識還不夠
與智商不同,法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的學習與培養(yǎng)獲得的。法律知識的學習無疑是法商的重要內涵,但法律知識扎實并不一定就代表法商高。據(jù)說當年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的法律就考了95分,但他最終卻因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副省級官員。因此,法商的高低不僅在于法律知識掌握的多少,更在于對法律精神的認識與理解,在于對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這種對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是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逐步養(yǎng)成的,具體表現(xiàn)為一種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行為習慣和工作能力。
首先,要敬畏法律,這是提高法商的基礎。一些人的法商不高,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對法律缺乏敬畏感。在他們眼里,根本就沒有法律的存在,有的只是對金錢、權力的貪婪與渴求;為了金錢、權力,可以肆無忌憚,什么法律、規(guī)則,統(tǒng)統(tǒng)拋在了腦后。過去一些領導干部犯了罪,在懺悔時還不會忘記說自己忽視了對法律的學習,現(xiàn)在一些干部連這句話都不說了。近年來的公開報道中落馬官員進行的公開懺悔中,不少人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時最常見的一句話,就是“我是農民的兒子”,連遮羞布都不要了。
其次,要尊重法律,這是提高法商的關鍵。不論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百姓,在平時的工作和生活中能用法律約束和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養(yǎng)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習慣。要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決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現(xiàn)象蔓延開來。要使大家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訴求,通過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
其三,要信仰法律,這是提高法商的核心。法商的高低,核心就是看一個人對法的信仰和崇尚程度。法律不僅僅是一種規(guī)范,更是一種信仰。古希臘的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說中,對此做過很好的詮釋:“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而寬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悅誠服。”只有內心對法律的信仰、對法律的心悅誠服,才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用法律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法商。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求提高全體公民的法商,但首先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法商。孔子說過:“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要求執(zhí)政者首先以身作則;孟子也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執(zhí)法者能夠帶頭用法和守法。我們一些領導干部常常抱怨群眾法律素質低,總是因為“不明真相”而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但他們是否想過,自己如果能夠依法做到政務公開,群眾又怎會“不明真相”?自己如果能夠真正依法辦事,群眾又怎會輕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反之,如果領導干部自己是“信權而不信法”,那么群眾也只能是“信訪而不信法”了。因此,提高法商,首先要從作為“關鍵少數(shù)”的領導干部做起。
采寫:聞濤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endprint